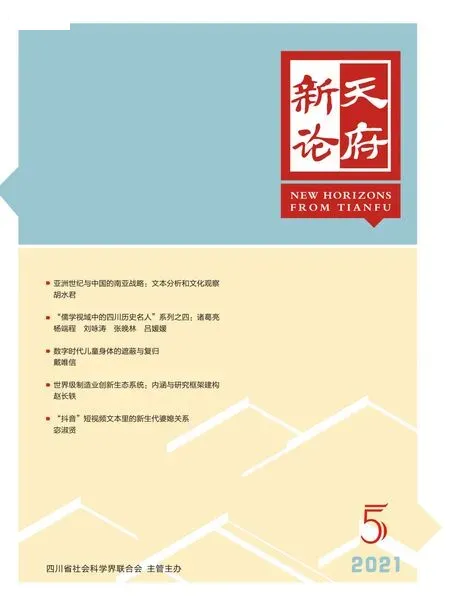諸葛亮治蜀與蜀漢的國家建構
楊端程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余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東漢中期以后,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加劇,國家建構的核心支柱——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1)安德烈亞斯·威默(Andreas Wimmer)認為“政治整合”和“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是國家建構的一體兩面。而譚凱(Nicolas Tackett)指出,到了宋代,中國的士人(知識階層)才逐漸有了近代意義的國族認同。因此在筆者看來,對沒有興起國家認同的前現代國家而言,國家建構的主要任務就是形成政治整合。參見Andreas Wimmer, Nation Building: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Others Fall Apar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4; Nicolas Tackett,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ng China and the Forging of an East Asian World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逐漸坍塌。至東漢末年時,原本大一統的政治秩序在接二連三的起義、叛亂和內戰中徹底崩解。在各大政治軍事勢力相互競爭的過程中,曹操、劉備和孫權三家逐漸脫穎而出,最終形成魏統中原、漢據巴蜀、吳領江東的三足鼎立之勢。以重建統一國家為目標(2)《三國志》對三國各方的統治者以統一為目的的表態都有詳細記載。的魏、蜀、吳三國在展開軍事競爭的同時,也開啟了在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領域中的不同實踐。與魏、吳相比,諸葛亮治蜀一改東漢中期以來的政治流弊,一方面形成了“宮府一體”的有效政治整合,實現了桓靈以來士人政治的追求;另一方面充分發揮了國家專制性權力(despotic power)與基礎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3)有關國家的專制性權力與基礎性權力的定義可參考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5, No.2,1984, pp.185-213.,從而增強了國家力量(state strength),一時間塑造了中國古代王朝國家治理的理想類型。
一、研究的緣起
諸葛亮治蜀,不僅在中國西南地區歷史發展和文化傳承事業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且對后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對于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歷朝歷代的史家、政治精英乃至統治者都給予了高度褒揚(4)如一代明君唐太宗在召集群臣時曾言:“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嘗表廢廖立、李嚴于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故陳壽稱:‘亮之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參見吳兢:《貞觀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5頁。再如在歷經安史之亂、面臨藩鎮割據的中晚唐,以諸葛亮為榜樣的宰相裴度協助唐憲宗開創了“元和中興”的局面。參見裴度:《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并序)》,載諸葛亮著,段熙仲、聞旭初編校:《諸葛亮集》,中華書局,2014年,第129-131頁;王曉喬:《論諸葛亮精神與裴度開創元和中興局面》,《文史雜志》2020年第5期。而在喪亂的東晉一朝,朝中的士族領袖王坦之也力勸簡文帝修改遺詔“家國事一稟之于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來試圖感化、勸解已有篡位之心的桓溫。參見房玄齡等:《晉書·桓溫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2579頁;房玄齡等:《晉書·簡文帝紀》,中華書局,1974年,第223頁;房玄齡等:《晉書·王坦之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966頁。,彰顯了深刻的政治教化意蘊。而從學術意義上加以省察,當代歷史學界對此也著墨甚多,特別是從諸葛亮本人的政治思想(5)如陳寅恪指出,諸葛亮的政治思想源于法家;朱大渭則指出,諸葛亮是儒法合流的代表;還有學者對宋代理學對諸葛亮的評價做了較為完善的梳理。參見陳寅恪:《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附論吳、蜀)》,載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24頁;朱大渭:《論諸葛亮治蜀——兼論諸葛亮是儒法合流的典型人物》,《魏晉隋唐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91-124頁;許家星、王少芳:《“儒者氣象”——宋代理學視野下的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軍事戰略(6)陳金鳳認為諸葛亮北伐不僅出于政治目的,還具有經濟目的;時殷弘則批評諸葛亮北伐是國家戰略讓位于意識形態的錯誤決策。參見陳金鳳:《諸葛亮軍事經濟思想與戰略論析》,《社會科學輯刊》2004年第2期;時殷弘:《從徒勞北伐到蜀漢覆亡:戰略的蛻化、復興和湮滅》,《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2輯。和選人用人(7)參見霍雨佳:《諸葛亮與曹操、孫權用人異同優劣論》,《海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3期;黃劍華:《論諸葛亮的人才觀和人才政策》,《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張思恩:《諸葛亮的人才思想和用人實踐》,《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4期。等多個角度出發加以求證,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從諸葛亮的個人政治身份出發,亦可從國家建構者(state builder)的角度理解其治蜀的方針策略和政治意義。換言之,在漢晉之際,因君主幼沖,由宰輔行使國家最高權力的現象屢見不鮮。但與兩漢霍光、董卓以及同時代稍后時段主政東吳的孫峻、孫綝兄弟相比,諸葛亮的角色更接近于魏國的奠基者曹操,他不僅是當時的“王佐之才”(8)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2526頁。,更是真正的國家建構者(9)可以印證的是,《諸葛亮傳》在《三國志》“蜀書”中所占的篇幅最大,超過了《先主傳》對蜀漢開國皇帝劉備的記述,足見諸葛亮個人在蜀漢國家興衰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在政治整合方面的建設、對東漢政治流弊的革新以及對士人政治的追求直接決定了蜀漢中期之前的國家發展。
從更廣闊的視域來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前現代帝國、王朝國家乃至近代民族國家等不同類型的國家相比,中國在國家建構領域是名副其實的先行者,早在2000年前就建成了韋伯(Max Weber)意義上的現代官僚制(10)Edgar Kiser, Yong Cai,“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 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 No.4, 2003.,在后來的發展進程中也經歷了不同波次的“波峰”與“波谷”,不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在歷史長河中更是涌現出了眾多聞名遐邇的國家建構者。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下政治學研究中的國家建構理論多源自西方學術界對歐洲特別是西歐早期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經驗的概括,而忽視了古代中國在這一領域豐富的實踐經驗。作為中國國家建構史中典范的諸葛亮治蜀自然也非例外,其長期以來只被視為一種歷史現象,只被固定在歷史學領域加以討論,其政治學意義則遭到了完全忽視。
有鑒于此,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本文嘗試將歷史學與政治學的敘事結合起來,立足于關鍵行動者(actor)諸葛亮,從結構/能動的角度討論諸葛亮治蜀與蜀漢的國家建構這一歷史事實的緣起、過程與影響。(11)本文并不是挑戰歷史學的已有研究,而是借助歷史學已有的豐碩成果,從國家建構的角度重新理解諸葛亮治蜀。本文接下來將從以下幾個部分展開論述:首先是介紹諸葛亮在執政前后蜀漢面臨的困境,其次是介紹諸葛亮進行橫向政治整合的舉措——確立“宮府一體”制度,再次是討論諸葛亮如何發揮國家專制性權力和基礎性權力從而實現對社會的縱向整合、提升國家力量,最后是對諸葛亮治蜀之于國家建構的意義進行總結與討論。
二、執政的困境:“此誠危急存亡之秋”
東漢中期以后,皇帝相繼早亡,嗣后即位的君主又多幼沖,由此導致大權旁落。在中央,最高權柄在外戚、宦官之間來回易手,政治斗爭變得空前白熱化;而在地方,惡政導致干戈四起、烽火連天。由此,原本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經歷了桓靈二帝的昏聵統治,終于在黃巾起義和董卓亂政的打擊下演變為全面內戰,進而土崩瓦解。隨后,在各大勢力之間展開的軍事競爭中,曹操、劉備和孫權三強從逐鹿的群雄中脫穎而出。
建安二十五年(220),吳大都督呂蒙偷襲荊州,俘殺蜀將關羽。次年先主劉備以為關羽報仇為名,不顧蜀漢政權新立、根基不穩之虞,興兵伐吳,不料在夷陵猇亭之戰中大敗,國力遭受重創。章武二年(222),劉備退至永安,次年病篤,臨終之前將國務大事托付給丞相諸葛亮,令其輔佐太子劉禪,又令劉禪以父事之。
當時后主年少,不能親政,而此時的蜀漢又處于內憂外患之中,正如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所言“此誠危急存亡之秋”(12)從某種程度上說,《出師表》代表了諸葛亮治蜀的方略和理想。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收錄了該表。參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919-920頁。本文接下來將多次引用該文,不再單獨標注出處,只用引號表示。。特別是當先主兵敗夷陵的消息傳回時,蜀中人心震動,漢嘉太守黃元聞知舉兵反叛,而牂牁太守朱褒、大姓雍闿、越雋夷王高定等勢力也相繼叛亂,甫立不久的蜀漢政權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因此,在內有叛亂、外有強敵的危險情況下,如何改革東漢中期以來的政治積弊、維護政治整合、完成先主劉備未竟的國家建構事業就成為擺在諸葛亮面前的頭等大事。
從永安受托執政算起,到北伐病卒五丈原,諸葛亮單獨執掌蜀漢國家大權共計十二載,時間雖然不算長,但其竭力鞏固內政外交,不僅使蜀漢獲得了難得的安定環境,而且大大增強了蜀漢的國家力量,使得蜀漢一度憑借一州之力同北方強敵曹魏抗衡,創造了三國乃至中國歷史上的一段佳話,影響極其深遠。
有鑒于此,我們不禁要問:蜀漢自立國以來,盡管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13)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中華書局,1982年,第923頁。為正統,以“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為志業,然而重建大一統國家并非能坐享其成。因此,在激烈的軍事競爭中,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在面臨重重困境時,諸葛亮又是采取了何種措施,不僅完成了國家建構的任務,而且增強了國家力量呢?
對此,本文指出,諸葛亮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夯實了政治整合這一之于國家建構的重要支柱。在橫向政治整合層面,諸葛亮以丞相府統領全國政事,建立了“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制度,通過選賢舉能來推動“宮府一體”制度的有效運轉,從而改革了東漢中期以來政出多門、政治腐化的積弊,維護了中央精英間的團結和政權的穩定,實現了東漢中期以降士人所追求的政治理想;而在國家-社會關系層面,諸葛亮充分發揮了國家的專制性權力與基礎性權力,從而完成了國家對社會的整合。他一方面抑制豪強,懷柔少數民族,另一方面厚植民生,重視教化,從而提升了國家對社會資源的汲取,增強了國家力量。
三、推動政治整合,確立“宮府一體”
作為國家建構的支柱,政治整合在空間上具有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所謂橫向維度的政治整合即統治者/執政促進中央層面政治精英的團結,防止精英之間陷入內斗,進而維護政治穩定,形成具有向心力的精英網絡。
諸葛亮在國家建構方面的舉措首先見于其通過制度設計推動橫向層面的政治整合,即以丞相開府統領全國軍政大權,實現其在《出師表》(14)這里之所以又引《出師表》,不僅因其是一篇樹立良臣典范的優秀文學作品,更因其提綱挈領地闡述了諸葛亮治國理政的方針政策。中所提“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目標。在此,“宮”指的是內廷、禁中,用來指代以君主為核心的中朝/內朝,而“府”則為三公之府,即兩漢以來三公領導的外朝/中央政府,在蜀漢語境之中特指諸葛亮領導的丞相府。諸葛亮為何要推動“宮府一體”的制度建設?(15)張仲胤、張旭華從“宮府一體”制度的確立到破壞的歷史演變入手探討了蜀漢的國家興亡。參見張仲胤、張旭華:《“諸葛之成規”與蜀漢興亡》,《中州學刊》2020年第5期。這就要從西漢中期以降形成的政治現象說起。
西漢中期以來,在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即位后,君主一方面出于對開國以來外朝以丞相為首的三公權力過重的忌憚,另一方面又不便直接統領外朝事務,便愈發倚重內廷的尚書、中常侍等職,中朝官由此坐大,開始分割外朝三公的宰相權力(16)有關對兩漢三公皆為宰相的詳細論述,參見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二章、第三章。,以致“雖置三公,事歸臺閣”(17)范曄撰、李賢等注:《后漢書·仲長統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1657頁。,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王莽篡漢。其后,東漢光武帝雖然實現了漢朝中興,但對西漢形成的這種政治安排因之不改,“內廷權重、外朝權輕”(18)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31頁。的制度也由此定型。(19)關于從西漢中后期到東漢三公制度演變的詳細論述,參見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7-85頁。
然而自漢安帝以來,因君主相繼早亡,而即位的新君又多年幼,大權開始在太后(外戚)和宦官之間來回易手,這就導致了外戚、宦官與士人等不同群體之間相互傾軋,加深了內廷和外朝之間的矛盾,以致一時間朝廷內外黨派林立,政出多門,光武中興塑造的政治秩序就此腐化,而這種政治衰敗的亂象到了桓帝、靈帝在位期間更是愈演愈烈。宦官不僅掌控了內朝/宮中事務,腐化政治,更是干涉地方用人選舉,禍害一方,致使舉國上下“正直廢放,邪枉熾結”(20)范曄撰、李賢等注:《后漢書·黨錮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2187頁。。而士人等清流群體對此則憤懣不平,于是聯合外戚反對宦官執政。桓帝一朝,尚書朱穆上疏切陳宦官禍國,指出“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并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御。兇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21)范曄撰、李賢等注:《后漢書·朱穆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1472頁。。由此可見,當時以朱穆為代表的朝中正直官員已經深刻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希望統治者加以遏制。然而這種流弊非但沒有被遏止,反而將宦官與外戚、士人之間的斗爭推向了白熱化,以致先后引起了兩次黨錮之禍(22)漢桓帝在位時期,宦官為非作歹,朝廷內外的士人聯合外戚共同反對宦官,于是反對者皆治罪下獄,后來雖獲釋放,但皆禁錮終身,永不錄用。漢靈帝即位后,士人領袖陳蕃升任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外戚竇武共同謀劃誅除宦官,事泄被殺,并牽連多人,引發了第二次黨錮之禍。,最終這種激烈的權力斗爭以涼州軍閥董卓入主洛陽而告終,東漢的國家權威也由此走向崩解。因此,在亂世中如何建立權威、推動政治整合進而形成政治秩序成為各大政治勢力亟須解決的首要難題。
作為蜀漢政權的創立者,劉備雖然在即位后即“置百官,立宗廟,袷祭高皇帝以下”(23)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先主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890頁。,但是己身長年戎馬倥傯,立國甫定又興兵伐吳,于夷陵大敗后不久即“中道崩殂”,在政治制度的改革與建設上并沒有取得多少突破性的進展,因此在巴蜀之地建立乃至鞏固一個有效的政治權威仍然是尚待解決的難題。劉備率軍出征時,蜀中政務全由諸葛亮處置。劉備殂后,“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24)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918頁。。諸葛亮充分吸取了前朝因政治分裂而覆亡的教訓,強化政治整合,一改前朝宮府分離的二元體制,重新建立了“宮府一體”的制度。
制度在建立后,其自身并不會自動運作,若要推動制度的有效運作則離不開人為。在這層意義上,如何推動“宮府一體”制度的有效運轉,完成政治整合,實現士人的政治追求,選人用人的重要性就凸顯了出來,正所謂“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25)安小蘭譯注:《荀子》,中華書局,2012年,第72頁。。諸葛亮以丞相府總理全國政務,在人才選拔上格外重視從儒家推崇的士人政治的追求予以考察,他強調“治國猶于治身,治身之道,務在養神,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是以養神求生,舉賢求安”(26)諸葛亮:《便宜十六策·舉措第七》,載諸葛亮著,段熙仲、聞旭初編校:《諸葛亮集》,中華書局,2014年,第67頁。。在這一原則指導下,諸葛亮舉賢不避親仇,所選拔重用之人皆為“貞良死節之臣”,這就與東漢中后期宦官專權,腐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選舉形成了鮮明對比,因而西土人士無不服諸葛亮“能盡人之器用也”(27)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楊洪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1014頁。。陳震、楊洪、向朗、張裔、蔣琬、費祎、董允、郭攸之等忠良之士雖在劉備創業之時已被挑選任職,但得到重用均是在諸葛亮執政時期。諸葛亮在率軍出征時,就經常以向朗、張裔、蔣琬等主管相府事務,治理益州,使得“足食足兵以相供給”(28)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蔣琬費祎姜維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1057頁。。同時,以郭攸之、董允為侍中,取代自東漢以來由宦官出任的中常侍(29)西漢開國后,沿襲秦制設中常侍一官,以士人任職。然而自東漢建武以來,中常侍皆由宦官出任,所以才會出現前文中所述宦官權傾內廷以致專權擅政的局面。參見范曄撰、李賢等注:《后漢書·宦者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2508-2509頁。、小黃門(30)東漢小黃門由宦者充任,其“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眾事”。參見范曄撰、李賢等注:《后漢書·百官志》,中華書局,1965年,第3593頁。等職,以負責宮中事務。后來,諸葛亮又使董允兼虎賁中郎將,以向朗為中部督,統領宿衛親兵。董允等人“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31)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董允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986頁。,在匡正后主的同時抑制后主身邊的小人禍亂朝綱,故其在世時,在后主親政時期操弄權柄的宦官黃皓,其職位只是黃門丞。正是如此,諸葛亮領兵在外,朝廷內外相安無事,“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32)尚馳:《諸葛武侯廟碑銘》,載諸葛亮著,段熙仲、聞旭初編校:《諸葛亮集》,中華書局,2014年,第128頁。。
如果說選拔士人推動“宮府一體”制度有效運轉的本意當為實現政治整合,那么諸葛亮對政治整合的維護還可從對彭羕、李嚴的打擊中窺見一斑。作為在劉備領益州牧時即辟任為治中從事的人物,彭羕恃才傲物,在遭到貶斥后試圖暗中勾結馬超另立權力中心(33)彭羕曾經對馬超說“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參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彭羕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995頁。;而李嚴與諸葛亮同受托孤大任,以尚書令副丞相,位高權重,但其也試圖另立權力中心,先是欲“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34)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李嚴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1000頁。,不果后又在諸葛亮率軍北伐時掣肘后勤。彭羕、李嚴的做法不僅是破壞“宮府一體”制度的行為,也是對士人政治的倒退,為諸葛亮所不能容忍,因而受到了嚴厲打擊。(35)彭羕被下獄處死,李嚴被廢為庶人。但需要強調的是,諸葛亮采取的這些措施并非出自個人對權力的野心與覬覦(36)諸葛亮廢李嚴為庶人后,啟用李嚴子李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可見其公心無私。參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李嚴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1000頁。,而是打擊政治分裂、維護政治整合的舉措。
諸葛亮創制的“宮府一體”制度完成了劉備未竟的國家建構事業,在一時間內維系了蜀漢內部的政治穩定,在此基礎上選用貞良之士,使得君臣和睦,優劣得所。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東漢中期以后形成的政治流弊,部分實現了當時士人在政治上的追求。盡管諸葛亮后來病逝,但嗣后輔政的蔣琬、費祎二人延續了諸葛亮制定的政策方針不改,因而也創造了“邊境無虞,邦家和一”(37)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蔣琬費祎姜維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1069頁。的安定局面。然而到后主親政時,其開始任用東宮舊臣,破壞了維系蜀漢立國的“宮府一體”制度,侍中陳袛與宦官黃皓由是“互相表里”(38)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陳袛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987頁。。陳袛死后,黃皓更是升任中常侍、奉車都尉,專權擅政,甚至和右大將軍閻宇密謀廢姜維大將軍一職取而代之,導致領兵在外的姜維飽受猜忌,最終不得已請求出鎮沓中自保。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蜀漢的覆亡離不開后主親政后對“諸葛之成規”(“宮府一體”制度)的破壞。(39)參見張仲胤、張旭華:《“諸葛之成規”與蜀漢興亡》,《中州學刊》2020年第5期。此外,筆者與黃晨正在進行的研究通過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發現在劉禪親政之后,蜀漢朝廷的精英網絡開始分化,逐漸形成了以君主為中心的權力網絡和以輔政大臣(他們依次是蔣琬、費祎、姜維)為中心的權力網絡,不僅在戰略和政策上逐漸陷入分裂,更是在后期陷入權力斗爭。參見黃晨、楊端程:《國家興衰的精英基礎——精英吸納、精英網絡與魏蜀吳三國國家構建的不同命運》,待刊論文,2021年。
四、國家整合社會,以民為本,教化為先
如前所述,諸葛亮建立“宮府一體”是為了改革東漢中期以降不同精英群體之間互相惡斗的亂象,實現橫向層面的政治整合,其目的最終落腳于維護政治穩定,但是這并不能直接推動國家力量的提升。換言之,如果要增強國家力量,就必須推動縱向政治整合,即國家整合社會。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權力,汲取社會資源以展開軍事競爭。諸葛亮執政時將國家權力下滲到社會正是推動縱向政治整合的具體表現。
巴蜀地區雖然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譽,但本為“蠻夷”之地,在三代之時與中原政權的聯系與后來不可同日而語。直到秦滅六國,廣泛推行郡縣之治,國家權力的觸角逐漸向全國伸展開來,巴蜀之地進一步被納入中央王朝統一的行政管理之下。(40)秦始皇統一全國后,設三十六郡,其中在蜀地設巴郡、蜀郡。司馬遷著、裴骃集解:《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82年,第239頁。秦朝雖二世而亡,然而在蜀地設行郡縣之制不廢,兩漢因之,這種做法也一直持續到西晉末年氐族首領李雄據蜀稱帝自立(41)從秦朝建立到西晉滅亡期間,巴蜀地區的行政區劃多有變動,但以郡縣進行治理的方式不變。當地行政區劃的具體變遷歷史可參見房玄齡等:《晉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82年,第438-439頁。。在此500年間,歷屆中央政府陸續委任地方官員,在當地進行行政管理和發展生產的同時,也對民眾展開教化,使得“漢家制度”地方化,一度涌現出以文翁治蜀為代表的循吏典范(42)在西漢景帝、武帝時有文翁治蜀之故事,該事由東漢班固在《漢書》中追記,雖然其具體史實還存在爭議,但反映了兩漢時期的政治社會現象。參見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循吏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3625-3626頁。從國家建構的角度評析此事者,可參考任劍濤:《文翁治蜀、“漢家制度”與國家重建》,《天府新論》2021年第3期。,為戰亂后的國家重建做出了重要貢獻。自此之后,蜀地社會因被整合到國家當中而得到了長足發展。
然而到了東漢末年,政治權威的崩解導致天下大亂,豪強四起,由是地方脫嵌于中央,社會脫嵌于國家。巴蜀地區同樣不能置身事外,也陷入軍閥豪強專政的狀態。一方面,巴蜀地區因其“民殷國富”,豪強之間彌漫著奢靡腐敗之風,由是“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43)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董和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979頁。。另一方面,則是當地人民為了生存不得不依存豪強,在其盤剝下苦不堪言。劉焉在主政益州之初也試圖抑制豪強,但旋即遭到豪強的反叛(44)劉焉曾以他事為借口殺益州當地豪強王咸、李權等立威,犍為太守任岐、益州從事賈龍隨即以此為借口進行反叛。參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劉二牧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867頁。。劉焉死后,益州豪強見其子劉璋溫仁,便推舉其為州牧。既然由豪強推舉,劉璋任州牧后自然不得不向豪強妥協,加上自身暗弱,又不能制止從三輔、南陽一帶流竄而來的東州兵侵暴蜀地人民。由此,劉焉、劉璋父子兩代主政益州二十余年而無恩德施于百姓(45)對于劉璋牧益州,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給出了“不知存恤”的批評。參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913頁。,致使當地“政令多闕,益州頗怨”(46)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劉二牧傳》注引《英雄記》,中華書局,1982年,第869頁。。
因此,對于作為外來政權的蜀漢而言,如果要在當地立足,就必須對脫嵌的勢力重新進行整合,只有重新將國家權力嵌入社會當中,才能在碎片化的權力結構中重新建立權威。對此,曹操曾言“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47)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高柔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683-684頁。。這表明,在治平之世當用禮樂教化民眾,而在亂世時則應以法治國,才能恢復政治秩序。在漢末天下大亂、禮崩樂壞的情況下,如果要重建政治秩序,必須行法治以立威,再行德治教化人心。這一做法倒并非源自曹操唯獨信奉法家的政治理念,而是在東漢一朝,儒生與文吏兩種原本不同身份的群體已經愈發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同聚焦禮樂的西漢儒生與新莽儒生不同,東漢愈來愈多的儒生在進入帝國官僚體系內任職后,變得以實務為導向,逐漸在身份上完成了文吏化與官僚化的轉型。(48)關于東漢時期儒生與文吏的合流歷程,可參見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十章。因此,他們在施政時就不能只追求復古而不繼承發揚帝國從前的“法治”和“吏化”傳統,因而在“漢家制度”下的士人政治也就具備了“霸王道雜之”(49)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元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第277頁。的特征。
諸葛亮治蜀正是秉承了東漢士人這樣的政治傳統。諸葛亮輔佐劉備建立蜀漢政權后,一改之前劉焉、劉璋兩代州牧主政時“德政不舉,威刑不肅”(50)這句話出自《諸葛亮答法正書》,參見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蜀記》,中華書局,1982年,第917頁。的政治流弊,與法正、劉巴、李嚴和伊籍五人共造《蜀科》(51)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伊籍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971頁。,以法治蜀,并且在打擊豪強專政的同時以上率下,以身作則,以“內圣”實現“外王”,將國家的專制性權力重新嵌入社會當中。
當然,如果說以法治國是發揮國家專制性權力的表現,彰顯出的是國家權力中“硬的一面”,那么其推行教化則是國家發揮基礎性權力的體現,表現出的則是“軟的一面”。諸葛亮雖然秉承了東漢士人的政治實踐傳統,以法治蜀,但與蜀漢另外一位開國功臣法正“擅殺”有著本質不同。換言之,如果治國只用嚴刑峻法,則施行的只是讓民眾感到恐怖、同時為士人所詬病的申、韓之術。然而與法家以威刑震懾民眾不同,諸葛亮頗重視教化的作用,其強調“以教令為先,誅罰為后”(52)諸葛亮:《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載諸葛亮著,段熙仲、聞旭初編校:《諸葛亮集》,中華書局,2014年,第74頁。來贏得人心。這種以教化為主、以刑罰為輔的德政不僅深入漢地人心,也遠邁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由是“刑政達于荒外,道化行乎域中”(53)裴度:《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并序)》,載諸葛亮著,段熙仲、聞旭初編校:《諸葛亮集》,中華書局,2014年,第130頁。。對于這一做法,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記載的諸葛亮平南中的故事可以作為佐證。以諸葛亮對孟獲七擒七縱為代表,最終使得當地豪強心服口服。而孟獲口中的“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54)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中華書局,1982年,第921頁。亦成為諸葛亮教化有成的最好反映。

五、總結與討論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總結:諸葛亮治蜀,是在蜀漢開國不久、國力因夷陵兵敗遭受重創、面對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以執政身份完成國家建構、推動國家發展以期實現士人政治理想的實踐。諸葛亮在外交上與孫吳重新修好,與之恢復聯盟,為鞏固內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在此基礎上,諸葛亮改革自東漢中期以來形成的政治積弊,一方面創建“宮府一體”制度,選用“貞良死節之臣”,促進了中央層面的政治整合;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國家的專制性權力與基礎性權力,在以法治國、以上率下的同時以民為本、重視教化、安定民心、懷柔邊境,進而成功地將社會整合到國家當中。由此,蜀漢在諸葛亮治下成功地完成了國家建構,造就了政治清明、秩序井然的局面,成為古代王朝國家治理的典范。因此,即便以精簡審慎而揚名后世的良史陳壽在評論諸葛亮時也絲毫不吝惜筆墨,給出了十分中允的稱贊: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61)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934頁,第934頁。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62)方勇譯注:《孟子》,中華書局,2010年,第262頁。意指統治者執政贏得民心的重要性。換言之,如果統治者為了民眾能安逸地生活而驅使人民,那么民眾即便受到驅使,雖然辛苦勞作也不會有怨言。同樣,統治者為了天下蒼生而采取刑殺的手段,那么遭到刑殺的人也不會有什么怨言。諸葛亮治蜀,正是踐行了孟子所言,所以才會“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63)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82年,第934頁,第934頁。。也正是如此,諸葛亮治蜀的政治影響才超越了時空的限制,在其死后多年仍被“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64)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袁子》,中華書局,1982年,第934頁。。
后來,在短暫的三國歸晉、天下重新一統后,曇花一現的西晉帝國又迅速在內戰和蠻族入侵中坍塌。在中原陸沉、南遷的晉室又處于一片風雨飄搖時,國家建構的失敗又讓士人們對諸葛亮治下的蜀漢有了重新認識。南朝梁時的文士殷蕓在其小說中記敘了東晉中期權臣桓溫西征成漢時的一則故事:
桓宣武征蜀,猶見諸葛亮時小吏,年百余歲。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后,正不見其比。”(65)殷蕓編纂、周楞伽輯注:《殷蕓小說·吳蜀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6頁。
上述《殷蕓小說》中所載故事內容雖然不一定全是真實的,但它卻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一種社會心態。諸葛亮治蜀展現出來的正是東漢中期以來士人所追求的國家一統、政治清明的理想。正如錢穆所言,東漢士人群體身上“有一種共遵的道德,有一種足令后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雖傾,天下雖亂,而他們到底做了中流砥柱”(66)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91頁。。正是這種士人精神,在東漢末年經歷三百年的消沉后,終于在隋唐之際重新煥發,將中國國家建構的歷史推向了新的“波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