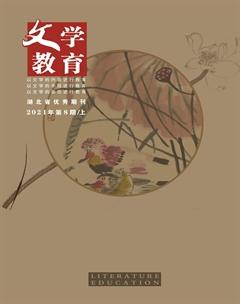“安于語言的智慧”

在詩歌的“風箱”中,臧棣游刃有余地調動風力,鼓冶出許多“能激活偉大的暗示”的作品。這些作品之所以能夠激活“偉大的暗示”,主要在于他對語言神秘性力量的調度。臧棣對于語言有一種特殊的好感,比如他會認為“詩的幸福的核心是人們可以安于語言的智慧”,有時他對語言是依賴的,比如他會認為“對于詩的境界而言,最根本的還是,讓語言來決定想象。”但是語言的這種所謂“神秘性力量”,對于臧棣而言也許并不神秘。雖然他將詩的語言看作是“對應于神秘的召喚”,但實質上詩的語言的本質不過是“實驗性的”。正因為是“實驗性的”,所以這其中可以挖掘的“可能性”便是無限大的。
臧棣曾經對瓦雷里的“純詩主義”感興趣。瓦雷里后來頗為關注物本身的象征性和詞語本身之間的關系,曾聲稱“一個詞的激發功能是無窮無盡的”,而這與臧棣在詩歌實踐中注重語言的繁復以及語義的再生成有著重要關聯。舉他的《藍鹽簡史》一詩的前三節為例來看:“不同于那些常見的/白色結晶,以及奢侈的貧窮中/你有一個關于人類的偏見/只能靠它來糾正;//首先,你得學會面對/你的傷口是藍色的——/非常深,深到傍晚的空氣/仿佛被神秘的疼痛狠狠稀釋過;//清洗必須及時,以及最關鍵的,/抓一把,撒到傷口上,/你會聽到一只親愛的獅子/從你身體里發出過震天的吼叫”。讀這首詩,我有兩點最直觀的感受,一是對詩歌語言的“好奇”,二是詩歌似乎帶著“面具”。其實,臧棣本人對于詩歌語言就帶有好奇心,他曾說:“我們最需要的詩,是從語言的好奇心開始的詩。”而詩歌也“只能深刻于語言的好奇”。從《授粉師》來體會一下:“剛剛翻越過四十不惑,/流大汗流得像黑熊并不滿足于/用芭蕾的腳尖踮起/一個碩大但卻優美的身軀;/中年男性,可疑的魅力/定型于再無恥辱可供洗刷;/而驕傲并未過時,但溫和作為/一種生命的效果,會自動阻止/他過度反省:這所謂的不惑/像不像專為中年男性設下的/一個分寸感十足的局。//……而迷人的香氣/則來自陽光的撫摸。過濾在/微風中,兩性花多么捷徑。/譬如,黃瓜花就很善于雌雄同株。/輪到人能否經得住人心的考驗時,/你必須和他一樣確切地知道:/在莖稈的低位上開放的,/通常是雄花,而那些晶瑩的花粉/只有借助細細的毛刷,才會完成/一個小小的秘密。沒錯,不太起眼,/卻關鍵得近乎宇宙還有懸念”。我覺得這種“好奇”,一方面來自于語言本身所帶有的美感和“寓意”特性,另一方面則主要來自于詩人對語言和句子的“心凝”與“形釋”,以及如何將語詞與外在的物理事象加以“冥合”。對于詩人而言,處理好語言與思想的關系絕對是一項本領。
在詩歌語言上,臧棣也是一個有“野心”的人。從他所主張的“詩人成熟于語言的傲慢”可以窺見一些端倪。臧棣認可詩歌的“面具性”,認為“面具,是詩歌送給語言的最好禮物。”20世紀30年代,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歷史語境的轉換,西方學者對詩歌在功能上的變換曾有非常敏銳的分析:“詩在技巧上達到了空前的高水準;他越來越脫離現實世界;越來越成功地堅持個人對生活的感知與個人的感覺,以致完全脫離社會,直至先是感知然后是感覺都全然不在了。”“詩人為生活所迫——即為個人經驗所迫——集中注意力于某些詞匯和起組織作用的價值。”(考德威爾著《幻想與現實》)這段話明顯指出詩歌在功能上有從社會層面到個人層面轉化的一面,詩歌寫作越來越“堅持個人對生活的感知與個人的感覺”,甚至開始“集中注意力于某些詞匯和起組織作用的價值”。但“危機”有時就意味著“出路”,因為這恰恰暗示了詩歌的另一種重要功能——話語功能。“詩歌話語一直力圖保持的就是語言創始活動中對意義的敏感性,對感受自身的敏感性。……對詩歌話語而言,話語活動是一個永無終結的啟蒙過程,是對人類敏感性與感受性的持久的啟蒙,也是語言的自我啟蒙,即對意義感知領域的無限拓展。這是詩歌話語的雙重功能,既參與建構社會的象征視閾,也消除那些已經固化的社會強制儀式或墮落為儀式形態的象征主義。詩歌話語忠實于感受性、敏感性,不斷開啟對意義新的感知方式,同時忠誠于隱秘的象征秩序,致力于未完成的象征主義視域的建構。”(耿占春著《失去象征的世界》)詩歌話語是一種非常強大的“話語”!讀臧棣的詩歌,可以很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臧棣的詩歌“安于語言的智慧”,致力于對語言的揮斥與重構,為詩歌在“話語功能”的開拓上留下了巨大可能性。
趙目珍,青年詩人,批評家。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