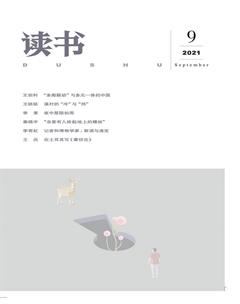墻壁和距離
黃紀蘇
接觸臺灣的文藝要早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當時我家那臺牡丹8402半導體收音機(后來又升級為牡丹941)的拉桿天線代我踮起腳、伸長脖窺望墻外的世界。當時聽過美國之音、英國BBC、日本NHK,漢語說得七拱八翹。只有忘了是叫“中央社”還是叫“自由中國”的海峽對岸在說地道的中國話,雖然聽著跟這邊也不大一樣。不時插播的歌曲戲曲就是臺灣文藝了,但干擾聲太強,不是斬首就是截肢,全須全尾的極少。再后來,七十年代末,大家長夜排大隊領救濟糧似的買盒式錄音機,沒多久,鄧麗君珠圓玉潤的歌聲竟如百萬雄師攻城略地,迅即占領了億萬耳朵。再后來的事就無須贅言了。
接觸臺灣的左翼文藝比較晚,好像是九十年代末。國民黨四十年代末敗走臺灣后,對共產黨幾乎見一個殺一個,造成了一代“無人區”,使得后來左翼的生長少見父子師徒的傳承,基本是靠“自學”“旁聽”——陳映真好像也是偷聽了海峽這邊的廣播開始的左翼人生。八十年代末臺灣解嚴,左翼有了生存的環境,于是發掘臺共黨人的史跡、為赴死就義的烈士樹碑立傳,便成為這撥兒革命遺腹子持之以恒的工作。他們愿力之篤、作風之實,讓人聯想到古代的摩崖造像,仿佛隱隱聽到深山里不停的斫石聲。以我有限的閱讀,鐘喬兄的《戲中壁》正是這項志業的最新成果。
《戲中壁》的“壁”是臺灣“光復”后三位左翼青年創作的一出戲,戲的名字就叫《壁》,講的是將社會隔為貧富的那堵墻。國民黨剛剛由于這堵墻丟了大陸,雖然打算在最后的棲身之地把土改進行到底,別讓墻太高了,但對于推墻黨不是殺就是抓,才不管什么自由世界不自由世界。結果,三個青年中編劇A喪命,導演S逃往大陸,編劇的愛人L冒死保藏了劇本。舞臺上的A和S在現實中均有真身(L是否虛構不清楚),或者說,作者的目的就是要還原真實的歷史。但以屠殺造成的斷層以及數十年的滄海桑田,犧牲者的事跡尤其是心跡只怕要比蛛絲馬跡更難尋覓,不像這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寫回憶,除了秘書部下,還有專門的班子負責查核檔案、整理錄音。這樣的客觀條件再加上鐘喬的詩人氣質,或許就決定了《戲中壁》的寫作過程會是一次反求諸己的心靈探索。鐘喬的探索著實艱難,他化身為臺上作家X在藥罐間輾轉反側,甚至在榻榻米上做瑜伽、翻倒立,為全劇濃重的悲情平添一抹輕松的自嘲。基于這種自我叩問的敘事結構不算別致但很極致:作家X完全是在人我、今昔交錯恍惚的心理時空中,與三位青年述往事、思來者。來自社會理想而不徒修辭美學的詩意,洋溢在字里行間,使舞臺在溫情中透著正氣。就這樣,一段冰凍的歷史像被春風解開,從深山中潺灄而動、蜿蜒而出。
雖然猶豫但還是想說,我讀臺灣左翼文藝包括鐘喬這部戲會感到某種距離。這距離肯定不是表達習慣上的,“阮”(咱)、“代志”(事情)那些很容易逾越;原因還在社會歷史變遷那邊。大陸改革開放后,社會大眾重建的世俗化、個人化情感,跟鄧麗君、羅大佑、侯孝賢詠嘆的家鄉故人、親情愛情可謂一拍即合、親密無間。跟臺灣左翼的心事,卻有著不小的時間差或歷史錯位,就好像時針都指六點,可一個am(上午)、一個pm(下午)。臺灣左翼與大陸左翼都出身于二十世紀上半葉那場革命,那場革命的基本目標是推倒那堵墻。革命者在俄國、在中國先后大獲成功,但那堵墻一直都在。關于這個問題,如果讀者嫌德日拉斯太境外了,可以參考毛主席的相關論述。總之是,親歷了革命之后種種的大陸左翼讀書人,如果沒什么特殊原因,是不會讀了沃勒斯坦的中心/邊緣學說或薩米爾·阿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理論,便忘了身邊的鴻溝大墻;也不會一見當年陳延年、陳喬年清澈的目光、壯烈的犧牲便對當今的“牛鬼蛇神”反倒看不見了。而東亞地區,尤其臺灣的革命者從未大獲成功,他們對革命的感受還在等著看日出的階段,自然沒有我們的矛盾和糾結。他們對某些字詞的熱愛、對某些顏色的迷戀,我能理解但實難茍同。這個意思,前些年評介藍博洲的《臺共黨人的悲歌》時我曾講過,當時曾引起藍君及一些臺灣朋友的不快。寫到這里心懷忐忑,也不知鐘兄見了會是什么反應?
其實,壁也好墻也好均為壓迫,砌筑也罷夯筑也罷都是不公。就反抗墻壁的本義或初衷而論,我們彼此的認同一定大于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