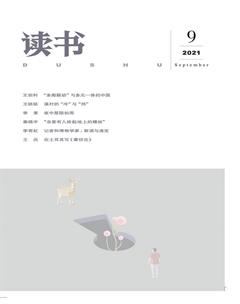魏瑪共和國的雅努斯面孔
方旭
一月(January)是兩幅面孔的雅努斯(Janus)。按照拉丁語的詞義,Iinus指的是“拱形走廊、門”之義,這道“門”既是時序的開端,又是時序的終結,它一面回顧過去,一面眺望未來。無論共和制,抑或帝制下的羅馬人,新年的第一天都會帶著上好的蜂蜜和無花果向其獻祭,祈求一年平安,善始善終。對于今日的魏瑪研究者而言,“魏瑪共和國”似“雅努斯”神般的存在,她既見證戰爭廢墟上自由民主的新生,又目睹了極權主義的游魂如約而至。二0二一年一月出版的埃里克·韋茨的《魏瑪德國》正是這樣一本書,其“雅努斯神”特性正如其副標題“希望與悲劇”所示。
本書二00七年首次出版,在魏瑪百年之際(二0一九年)再版。在韋茨看來,魏瑪精神“長存不滅”,如今依然要歌頌魏瑪的偉大成就:民主制度、文化創新、性解放、社會改革等。它以細膩的筆法全景描繪了共和國的重要主題:從海德格爾到希特勒,從托馬斯·曼到弗利茨·朗,從波茨坦廣場周圍精致閃亮的咖啡館,到伊合伍德陛下的卡巴萊歌舞廳和烏煙瘴氣的酒吧……韋茨的著作透露出立場:魏瑪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標桿,納粹的第三帝國是人類至暗時刻,魏瑪就是魏瑪,第三帝國就是第三帝國,不能因為第三帝國的“瘋狂”而污蔑魏瑪的輝煌成就。
今日與魏瑪對話依然有時代意義。年初,特朗普支持者“攻陷”白宮后,有美國學者撰文稱,“美國已經正走向魏瑪時代”。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九日革命的浪潮席卷柏林,德國共產黨人卡爾·李卜克內西與其追隨者攻占柏林皇宮,在皇宮陽臺宣布“社會主義共和國”誕生。兩個小時前,社會民主黨佩利普·謝德曼在帝國議會陽臺上搶先宣告“議會民主制政府”成立。這幅畫面像極了二0二0年美國大選尚未結束時,現任總統與總統候選人紛紛匆忙宣稱獲勝的情形——歷史不會放過任何重演的機會。
韋茨發現,十一月九日這一天成為二十世紀德國四次重要歷史節點。雅努斯神再次降臨:一面是革命和民主的偉大成就,除了一九一九年革命浪潮外,還有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墻倒塌”事件。另一面則是魏瑪夢魘時刻。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希特勒和魯登道夫等人在慕尼黑啤酒館自封“國家總理”,宣布臨時革命政府成立,并帶領三千沖鋒隊員向柏林進軍。希特勒的這一舉動實際上是仿效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因不滿意大利法西斯黨在意大利國會選舉中的失敗,一九二一年十月號召三萬名支持者進軍羅馬。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納粹政府策劃希特勒青年團、蓋世太保和黨衛軍襲擊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由于許多猶太人的窗戶在當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般發光,德國人諷刺地稱之為“水晶之夜”。據說,這一夜僅砸毀的玻璃相當于比利時全國半年生產玻璃的總量。
有人說,魏瑪是打著共和國招牌的“換湯不換藥帝國”。但作者強調,魏瑪共和國通過革命實現了國家的民主化——畢竟廢除了皇帝,制定了代表當時自由民主憲法標桿的“魏瑪憲法”。作者也承認,魏瑪原封不動地保留了許多舊的社會秩序,以致魏瑪封建統治階級穿戴華麗的制服、勛章和綬帶在波茨坦現代都市廣場上招搖過市時,具有那么強烈的違和感。
什么是魏瑪?從視覺上看,它是歐美現代主義建筑的圭臬,是現代設計包豪斯的發源地。至今在柏林仍有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柏林現代建筑群落。陶特(Bruno Taut)代表作“布里茨”和“馬蹄鐵”公寓,盡顯魏瑪“自由”“民主”之氣質:每個住戶享受同樣的陽光、綠地,以及社區歸屬感。韋茨坦言,這類烏托邦現代建筑設計將使居住者失去隱私自由,畢竟現代主義設計具有其“高傲一面”:其設計的是人們應該居住的方式,而并不管人們是否喜歡。
魏瑪普遍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它縮短了不人道的工作日長度。市民開始有了走進豪華影院、戲院、有歌舞表演的餐廳、酒吧消磨時光的閑暇。魏瑪標志性的“三大件”——收音機、電話機和汽車成為“新人標配”。不管美國文化曾被普魯士精英階層如何視為“粗俗低劣”,如今魏瑪流行文化彌漫著美利堅氣息:人們到現代化百貨公司購物,欣賞美國爵士樂曲,跳著美國的狐步舞和查爾斯頓舞。看上去——魏瑪共和國政治穩定、文化繁榮,儼然是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那隱藏在繁華背后的德意志工人黨(納粹黨前身),一九一九年不過只是個七十多人反民主主義、反猶太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小黨。這時——誰需要納粹?
魏瑪擁有的冠冕堂皇符號背后遮蔽了戰爭后血腥、黑暗、野蠻的創傷。德意志第二帝國有超過一千三百萬德國男性在軍隊中服役,他們“走向戰場,保衛德意志帝國”,抵御覬覦他們領土的“異邦人”。最糟糕的是他們輸掉了一場他們壓根兒不認為自己會戰敗的戰爭。直到魏瑪共和國成立,右翼圈子內還流傳著“刀刺在背”(Dolchsto legende)的傳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之所以戰敗,是因猶太人在國內煽動革命和輿論,使政府不得不向敵國投降,這為今后納粹大規模反猶行動埋下伏筆。
一九二0年榮格爾(Ernst Junger)的《鋼鐵風暴》為在炮火中重生的德意志軍魂極盡贊美之能事。文中“死了的人通過死亡從不完美的現實走向完美的現實,從目前這種形態的德意志走向永恒的德意志”這句尼采語錄體激勵了無數走向戰場的德國青年。而一九二九年德裔美籍作家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則表現出戰爭的恐怖、殘酷、骯臟,猶如手術刀割開“一戰”創傷的膿包,膿液順著皮膚流下……這支失敗的軍隊從前線歸來,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失去了眼睛,無數軍人因為疼痛接受嗎啡、可卡因的治療,戰士們無法從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宏偉承諾中脫離出來。他們精神感到幻滅,逐步走向“異化”,不再適應和平年代的生活。
“自由”是最好的撫慰劑,柏林成為世界同性戀表達和性解放的文化之都。毒品與性麻痹戰爭中難以愈合的黑暗創傷,事情的另一面則是,在“自由”孕育下的魏瑪——一九二八年的納粹黨反激增至十萬黨員。即便如此,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的第五屆國會選舉中,納粹黨依然只獲得2.6%的選票。僅隔了四年,希特勒的政黨成為國會中最為強大的政黨。這段時間發生了什么呢?
韋茨將“中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化”描述為納粹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德國馬克呈螺旋式的惡性通貨膨脹,德國的中產階級遭受重創。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來襲,嚴重破壞了德國經濟的穩定,掏空了中產階級私人口袋,導致大規模的失業。柏林大街上排滿了長長的隊伍領取救濟,人們厭煩了國內無休止的黨爭,對威爾遜的承諾不抱有任何希望,他們需要一個強力而富有魅力的領袖結束無盡苦難。
納粹的文宣機器開始高效運轉,它不斷重復“刀刺在背”和“凡爾賽陰謀”等類似陰謀論,承諾要一洗“國家恥辱”,解決民眾現實困境。它們許諾向偉大的帝國幻景策馬揚鞭,直至建立屬于德意志人的永恒之國。
帝國需要制造“真正的人民”。根據本書記載,在一九三0年的塔爾堡(屬漢諾威的小鎮),納粹黨幾乎每隔一周就召開居民會議,會議的主題不限于“淪為國際資本家利息奴隸的德國工人”,“在民族社會主義國家挽救中產階級”等。在塔爾堡納粹黨每天為兩百人提供食物,青年人能夠在非宗教環境享受聚會娛樂活動。希特勒明白,納粹黨如同一臺引擎,必須不斷加速,文宣系統必須使其支持者處于高度煽動和瘋狂動員狀態。當他到訪塔爾堡,當地納粹黨人要花上幾周時間準備排場,各處張貼海報,使用高分貝的麥克風和揚聲器,采用電影和戲劇等新手段宣傳。他們征召周邊地區的納粹黨人烘托熱烈的氣氛——鋪天蓋地的卍字旗高高舉起,希特勒的飛機從云端降落,人們群情激昂、山呼海嘯,發出同仇敵愾的呼喊。
韋茨不由得感嘆道:“魏瑪的覆滅,如同長鳴的警示,始終提醒我們民主的脆弱。”可魏瑪國父們創造魏瑪時,并未預計到它會如此脆弱。普羅伊斯、馬克斯·韋伯等精英們努力打造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周全憲法”,他們仔細研究瑞士、美國、英國和法國等國的憲法,吸取世界上最先進的立憲經驗,并將自美國、法國和拉美革命以來所有奉入建國憲法的政治權利都寫入其中……魏瑪憲法是世界憲法之楷模,韋茨更是稱道:《魏瑪憲法》堪稱舉世無雙!
我們進一步追問:“完美憲法”何以培育出激進極權主義?韋茨的著作關注到了魏瑪著名緊急狀態條款:第四十八條。從第四十八條的法理內涵上看,這個緊急條款終究是一種臨時性的權力,“緊急狀態”的法律界限晦暗不明。
從憲法文本上看,魏瑪國父們的總統緊急權力是用來克服議會功能弱點而設置,但從實踐操作來看,總統很難在緊急權力面前保持中立,議會在危機來臨之時往往被懸置,甚至拋棄一邊。無論后世將《魏瑪憲法》稱為何等精致完美的存在,第四十八條始終是這部憲法無法修補的Bug(漏洞),憲法的敵人從憲法內部攻破憲法本身。“專制保存自由”——這是魏瑪共和國又一雅努斯面孔。
從布呂寧開始,第四十八條成為頻繁使用的統治手段。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興登堡總統動用第四十八條,任命希特勒為政府總理。不到兩個月德國國會修憲通過《解救人民和帝國苦難法》(后稱《授權法》),容許德國總理及他的內閣可以繞過議會通過法案,雖然《授權法》違反自由民主、權力分立等《魏瑪憲法》設立的初衷,但審查機構無力認定其憲法程序“違法”,“極權主義”已經偽裝成“自由主義”侵入共和國。在韋茨看來,即便希特勒沒有上臺,魏瑪憲制已遭傾覆。
《魏瑪德國:希望與悲劇》的雅努斯面孔依然喃喃向我們訴說。它一方面揭示魏瑪文藝、建筑、哲學的輝煌創造力,另一方面則是描述魏瑪共和國如何走向萬劫不復的毀滅。韋茨的判斷可能是精準的:第三帝國的誕生并非是自由民主之標桿的魏瑪共和國之精神怪胎,而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事件。可如果過分強調“偶然性”,會讓我們忽略:魏瑪的敵人并不在于左右翼政黨造成的意識形態撕裂,而在于“自身”。這不是“民主,還是專制”的簡單判斷題,而需要在無比復雜的現代政治迷宮中找尋到救贖的阿里亞德涅線團。我們憧憬一個“有序的自由狀態”,這不僅需要“完美憲制”,更重要的是勇氣、德性、智慧與愛……當看清了政治的本相,我們才可能在魏瑪的教訓中發現問題,在魏瑪的悲劇中看到希望。
(《魏瑪德國:希望與悲劇》,[美]埃里克·韋茨著,姚峰譯,聶品格校譯,北京大學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