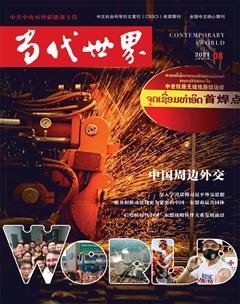來自奧地利的中國記憶和政治評論
【奧地利】海因茨·菲舍爾

對中國及其歷史、文化和發展的濃厚興趣貫穿我在維也納大學的求學生涯并持續至今,驅使我在1974年至2019年間十余次訪華。
我第一次訪華是在1974年夏末,當時中國處于毛澤東時代和“文化大革命”的末期。作為一名在1971年中奧建交之年當選的年輕國民議會議員,我和夫人在沒有陪同的情況下踏上了旅途。我至今都難忘首次訪華的經歷,此后更是見證了中國在過去近50年里翻天覆地的變化。天安門附近十幾層高的北京飯店是當時全北京最現代的建筑,與我們會談的多為各單位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在乘坐飛機和火車時,我們是唯一的外國旅客。大約幾千輛自行車里才有一輛汽車,大多還是公務用車。而如今去長城參觀,可以在不堵車的情況下經由高速公路快速到達,抵達后能看到長城上熙熙攘攘的游客和停車場上密密麻麻的車輛,還可以乘坐舒適的纜車俯瞰美景。在1974年,參觀長城需要一整天的時間。當年我們乘坐的是奧地利駐華使館的公務車,車上帶著一個折疊桌、三個折疊椅和一個野餐籃。車輛行駛在狹窄的鄉間小路,艱難地穿梭在若干牲畜拉車、少數破舊卡車和大量自行車之間,司機需不時鳴笛提醒。車開了幾個小時,臨近中午到達長城后我才明白,為什么奧地利駐華大使萊特納讓我們帶著野餐裝備。長城上游客寥寥,也沒有飯店。我們就在長城腳下支起桌椅,愜意地享用午餐和熱茶,順便觀察長城上孤獨巡邏的軍人和警察。飯后登上長城,在秋日暖陽中盡情欣賞壯麗景觀,感嘆長城是名副其實的世界文化遺產。返程途中還去了明十三陵,那里也幾乎沒有游人。參觀結束后,我們趕在晚餐前回到了酒店。
訪華的第二站是上海,同樣令人印象深刻。老城小路綠樹成蔭,兩側多為一兩層高的房子,探出木質的陽臺。當時的上海還留有德國和奧地利猶太人的印跡,他們曾在希特勒暴行和二戰期間來到上海避難。后來,上海成立了猶太難民紀念館,我在2019年訪華時參觀過。在訪華的第三站廣州,我穿街走巷尋訪周恩來的足跡。周恩來曾于20世紀20年代主管中國共產黨在廣東的事務,并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與時任校長蔣介石共事。國共兩黨合作開辦軍校,對于如今的歐洲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離開廣州后,我們趕往香港。出人意料的是,火車開到深圳河界就返回了,我們不得不拖著本次三周行(俄羅斯-朝鮮-中國-日本)的全部行李步行過橋,到達香港一側后才坐上另一輛火車。
兩年后的1976年,我原本要隨奧地利司法部長布羅達率領的奧中友協代表團再次訪華。但就在代表團啟程前,中國發生唐山大地震,傷亡慘重。訪問不得不推遲數月至1976年和1977年之交。那是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天,我們雖然帶了冬衣,但還是凍得瑟瑟發抖。中方邀請單位貼心地送了我們每人一件合身的軍大衣和一頂暖和的皮帽。除了寒冷,中國在兩年間發生的許多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周恩來和毛澤東在幾個月內相繼離世,中國人民十分悲痛,這也給中國帶來了深遠影響。此外,我還驚嘆于中國外交官的博學廣聞。中方為人數眾多的代表團安排了多名陪同人員,其中一位名為潘海峰的年輕外交官負責陪同我和夫人。他是一位德語講得很好的滿族人,十分熟悉奧地利的情況。幾年后,潘海峰就被派往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工作。自此,我對中國外交官始終充滿崇高的敬意。
我最近一次訪華是在2019年9月,在中國駐奧地利大使李曉駟和奧地利駐華大使石迪福陪同下訪問了西藏。我們從中國西北乘火車出發,經過24小時抵達海拔高達3600米的拉薩,旅途十分舒適。離開拉薩,我們又訪問了上海和合肥。當年,有800萬人口的合肥舉辦了世界制造業大會,邀請了法國前總統奧朗德、德國前總統武爾夫、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和我參加開幕式。各國嘉賓致辭后,共同參觀了重點展區和高新技術產品,包括一個外形優雅的智能機器人女士,它能在短時間內回答嘉賓提出的各種復雜問題。輪到我時,我決定換個測試方式,問了一個相當簡單的問題:“不好意思,請問可否告知您的年齡?”機器人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是位女士,女士的年齡可不能問。”在場賓客都驚奇得說不出話。我至今也沒弄明白,設計人員在給機器人編程時是如何兼顧人際關系的禮儀和感性的。

1994年1月26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抵達維也納,開始對奧地利進行為期4天的正式友好訪問。圖為喬石與時任奧地利國民議會議長海因茨·菲舍爾交談。(中聯部圖片)

1979年5月,時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左二)率代表團訪問奧地利,時任奧地利國民議會社民黨黨團主席的海因茨·菲舍爾(右三)會見代表團成員。(中聯部圖片)
同歷次中國之行一樣,在奧地利接待中國領導人的經歷也總是令人難忘。在接待中國國家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等領導人時,奧方始終熱情好客,力爭展現最好的一面,同時尋求開放坦誠的對話。江澤民主席曾接受建議,在維也納跳了一曲華爾茲。我曾邀請喬石委員長到家中喝茶,但不巧電梯壞了,只得安排人協助年事已高、不便爬樓梯的喬委員長來到我在5樓的家中。胡錦濤主席曾于2011年考察奧地利薩爾茨卡默古特地區的一個農莊,看到節省人力、干凈衛生的自動擠奶設備,對奧地利現代農業贊賞有加。
我第一次與習近平主席會面既不是在中國,也不是在奧地利,而是在意大利首都羅馬。2011年6月2日,意大利舉行全國統一150周年慶典活動,邀請了各國領導人出席,其中包括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和時任奧地利總統的我。慶典結束當晚,在嚴密的安保措施下,各國領導人按照禮賓順序依次乘車離場,過程十分漫長。在等待中,我認出一位中國代表團成員,從而得以與習近平副主席進行一番愉快的交談,直到我們不得不離場。2015年3月,我與已成為中國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再次會面,共同回憶起4年前在羅馬首次見面的場景。
一晃6年過去了,2021年我們迎來了雙慶年,一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二是奧中建交50周年。新中國成立后面臨十分艱難的處境。二戰結束后國際形勢依然動蕩,朝鮮戰爭爆發嚴重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同時斯大林的對華政策充斥著自私和傲慢。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國內經濟形勢不容樂觀,“大躍進”未能達到預期目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導致中國錯過了一些發展機遇。
但是,中國重新調整了路線方針,特別是在鄧小平領導下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使中國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其驚人的發展成就得到全世界的矚目和贊嘆。2000—2019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速為8.9%,社會保障事業實現巨大跨越,基礎設施得到全面現代化。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始終大力推進扶貧工作,帶領近億人口脫離了貧困的苦海,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領導下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偉大成就。2017年,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21年3月,中國通過的“十四五”規劃旨在維護社會穩定,提高綜合國力,并推動經濟增長模式更加綠色公正和可持續。根據該規劃,中國將在未來5年保持經濟年均增長5%—7%,并根據各年度實際形勢確定具體目標。同時加大力度推動科技自立自強,確保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7%以上,將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研發經費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2020年,習近平主席宣布了充滿雄心的環境保護目標,即二氧化碳排放力爭在2030年前達到峰值,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十四五”期間,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將分別降低13.5%和18%。今年,中國還計劃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將城鎮失業率控制在5.5%以內。

2021年3月1日,中歐地理標志協定正式生效。圖為3月2日在奧地利維也納商店內拍攝的施泰爾南瓜籽油,它是中歐地理標志協定中首批受保護的歐盟地理標志產品。(新華社圖片)

中國與奧地利的交流涉及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2019年10月9日,“文化中國、錦繡四川”四川文化旅游展示會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辦。圖為觀眾現場觀看“變臉”表演。(新華社圖片)
通往宏偉目標的道路總是崎嶇的。德國作家布萊希特曾說:“歷盡艱辛攀上高峰后,還要歷盡艱險跨越平原”,即攀高充滿困難和危險,而到達高處后,即使路途不再陡峭,繼續前行仍面臨巨大挑戰。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是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的差距不斷縮小。國際多家知名經濟研究機構預測,中國很可能在203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90周年之前,躍升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還需付出巨大努力,并應對更加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主要來自美國,在一定程度上也來自歐盟和歐洲國家。中美博弈不僅限于經濟,也延伸到了軍事領域。當前美國以絕對優勢保持全球第一軍事大國地位。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布的報告,美國2019年軍費支出約為7300億美元,中國僅為2600億美元,不足美國軍費的36%。盡管美國的領先優勢有可能縮小,但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其軍事實力幾乎難以被超越。放眼未來,中國將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美國仍穩坐軍事領域第一把交椅,歐洲也將以和平方式努力維護其在多極格局中的地位。拜登上臺后,歐美關系雖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領導人更替對中美博弈影響有限,因為兩國的政治經濟競爭涉及雙方核心利益,有其內在邏輯。同時應看到,鼓吹“戰爭必然性”的時代早已成為歷史。只要相關國家有良好意愿、付出巨大努力并認識到,一旦付諸軍事行動,競爭將大概率轉化為沖突,這樣戰爭便極有可能被避免。
歐盟和中國均愿維持良好的政治經濟關系,但歐中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競爭對手,公平和機會均等對雙方意義重大。在過去50年里,歐中關系總體發展良好,但出現的一些問題不容忽視。一是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給歐洲帶來與日俱增的壓力,中方或許也能感受到來自歐洲的壓力,雙方競爭日益激烈。二是百年來歐美經濟和政治利益緊密交織,中美博弈將不可避免地影響歐洲。三是歐中政治和價值理念不完全一致,雙方必須就此進行開放、坦誠和客觀的討論,這是尋求相互理解的重要路徑。
在擔任奧地利總統的12年間(2004—2016年),我曾見證聯合國大會莊重而一致地宣布諸多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其中2015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正式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一種“全球執政綱領”,希望包括歐盟在內的世界各國都能為之共同努力,并以此為基礎解決其他復雜敏感難題。
總之,多極秩序優于兩極格局,歐中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很高興看到在過去50年里,奧中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了富有成果的合作,希望兩國關系變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