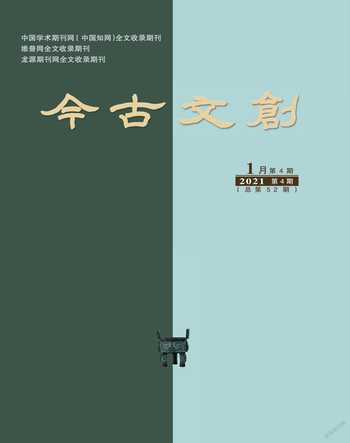淺析《莊子》創作中新穎獨特的題材選擇
魏寧 王永宏
【摘要】 莊子作為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對一個時代的人產生了巨大影響,其著作《莊子》也具有極大的研究價值。學界對其學術研究可謂多種多樣、百花齊放,本文通過廣泛翻閱國內外文獻內容,對比分析各大學者對莊子本人及其著作的評價,深入探究《莊子》文本的創作風格,探究其題材選擇的構思與奧妙。莊子崇尚自然的精神追求深刻體現在他的選材上,莊子運用了很多自然界中的動植物來表達對“道”的探索,通過奇人異事來體現“德”的真諦。
【關鍵詞】 莊子;創作風格;題材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04-0004-02
莊子與老子一起被后人尊為道家祖師,不論在哲學思想上,還是文化上,莊子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莊子的文章是先秦諸子的典范,具有豐富的想象力,構思新巧,筆走龍蛇,意境非凡。清代劉熙載說他“意出塵外,怪生筆端”,而魯迅則稱莊子文章“汪洋群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莊子》不僅在哲學領域影響深遠,還是一部具有獨特藝術魅力和很高研究價值的文學作品。莊子論述道義的方式不像老子一樣精微玄奧,更多是通過人物形象、故事等來闡述觀點,其文風、筆法、結構等等無一不值得人們仔細品味分析。
莊子的風格可以用恢詭譎怪來形容,他的創作題材新穎獨特,創作中題材主要分為人與物兩部分,新穎之處是以自然萬物為故事的主人公,以一些形體奇特的人物為主角,相反的那些看似品行端正身體健全的形象卻成為了反面形象。這是《莊子》的一大特點。他常以自然萬物為主人公,講述一段段離奇有趣的故事;他更是與儒家提倡的典型人物相反,文章創作中多次提及形體奇特的人物以及他們發生的古怪之事。
一、自然萬物
“寓言”是莊子的一種創作形式,通過虛構、擬人等手法塑造故事情節,通過象征、隱喻將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含蓄的表達故事中。在莊子的創作中的常以無人格的動植物作為預言故事的本體出現,并賦予動植物人性和意義,借此來闡發“道”的深遠含義。如《秋水》《至樂》《達生》等篇章都是通過多個寓言拼接而成,以此來表達思想內涵。
動物中有鯤鵬、蝴蝶、螳螂等,大體可以分為神話類的鯤鵬、鹓鶵,鳥類形象:《至樂》《達生》中的海鳥、《山木》中的異鵲、意怠鳥、《秋水》中的鹓鶵、鴟;魚類形象,魚這一形象在《莊子》中多次提到,在《大宗師》《秋水》《外物》《天運》等6篇文章中反復出現,還有一些其它寓言中的主人公也是動物,這些寓言被賦予了豐富的生命力。植物有椿樹、櫟社樹等,在《莊子》文章中植物的引入雖沒有動物多,但是也都不容小覷。可以將文中的植物按照“大與小”來區分,如內篇《逍遙游》中的大樗、冥靈、椿,《齊物論》中的大木、楹、梧等,加之外篇和雜篇中的大木意象約有20種。展現了莊子的無用和大美的審美主張,傳達了一種超越功利的人生態度和審美感受,使人的生命向著更積極的方向發展。《莊子》中的“樹”形象是對“無用之用”主題的進一步補充,戰國時期政治與哲學方面廣泛運用植物比喻來進行論述。文中的渺小植物有:草芥、焦、莛、柏、桑等,莊子舉了10多種,通過小的有用來反襯“無用即為大用”的觀點。
《莊子》中的動植物寓言寓意豐厚,闡述了莊子對于“道”的認識與理解,也借寓言讓世人明理。書中除了動植物以外還有很多自然景象,如“大海”“天空”“宇宙”等。從植物到動物再到大的景象都是莊子所追求向往的。莊子用詩化的語言闡發了自身不斷追求的超現實的人生理想與藝術境界,這種詩情畫意體現了莊子向往的自由,寓“道”于萬物也應了老子的“道,萬物之母”的言論。
二、奇人異事
在《莊子》一書中存在著大量的意向,比如鯤鵬、蝴蝶等一系列自然世界中的動植物,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人物意象,這些人物意象表現了莊子“立象以盡意”為主旨的創作實踐,獨立于大樹,鯤鵬等動植物意象之外。
(一)畸人意象。畸人意象是《莊子》中出現多的人物類意象,分為增殖型、殘缺型、極端型和精神型四大類,共12個人物形象。這類人的形成主要是因為社會動蕩不安、戰爭政權維護等原因使他們的身體受到傷害,進而成了不完整的人。他們也是最具現實意味的一類人群“道德社會”的受害者。莊子選擇這類人,主要是為了闡述這個社會的生存之道。在《人間世》中莊子借孔子之嘴說出“古之至人,先存儲己,而后存儲人”,“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義也。”這呼應了孔子所說的“為人臣子,固有所不得已。”相比這些欲“有為”之人,缺了身體部位的畸人是被忽視的集體,他們與普通人構成社會的基礎,在這個社會中,他們首要的目的就是生存。
面對畸人的生存狀態,莊子談到了他們精神與肉體上的需求,他們需要生活在世俗中,需要滿足吃、穿、住等基本需求。如甕大癭,支離疏等這些畸人的生存狀態可以說是在當時社會中達到了一種平衡。莊子對世俗的反抗主要體現在畸人意象縱向深入,從身體的畸形到心里的扭曲。接輿和盜跖,因為他們思想不符合所謂的道德標準,被看作異類;如叔山無趾,因觸犯法律而被砍去腳趾,從而被邊緣化。《人間世》中提到面對叔山無趾,仲尼說:“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因為“道德”而使自身變得不完整,又因為這種不完整而受到世人的歧視。通過一件件寓言表現莊子對當時社會的批評,更是借叔山無趾的口說出了“夫天無不覆,地無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儒家的欲有為于世,欲求名實,在莊子看來這種想法會造成社會道德的淪喪。
在《莊子》中畸人意象成為了“道”的實體形態。莊子對弟子說孫休是個見識短淺的人,不應該告訴他至人之德,因為那樣不會對他有啟迪,反而會嚇到他。很多身體健全的人,內心卻不完整,所以莊子借畸人意象,來體現什么是“道”。實際上作為“道”的體現,畸人形象是莊子對正常人所設立的一面鏡子,映射出正常的內心世界。莊子的題材新穎獨特,在當時的背景下他提出了一種與儒家思想相悖的觀點,他的作品中沒有君臣綱禮,蔑視仁義道德,追求自然大美,以奇人奇事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用這種奇特的題材來抒發自己內心的情感,給世人一條與綱常禮教不同的道路,讓人們理解“道”的意義。
(二)真人形象。“真人”是莊子理想人格,莊子認為老子、關尹子是真人,真人“不以人助天”,“以天待之,不以人如天”,真人是超越至人之一理念達到了超越“人”的境界。《大宗師》中對真人形象有詳細的描寫,古時候的真人看淡生死、不計較得失、無憂無慮追求自然之道。除了老子以外莊子還在書中塑造了一個真人形象——哀駘它,哀駝它的樣子十分丑陋,他坡腳、駝背、長相丑陋,但是卻受到男女老少所有人的愛戴,魯哀公也想與他一同分享這個國家,而他真正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德。《莊子》反復指出,只有內心的才智品德達到飽和狀態的時候,我們才是一個真實的“人”也就是真人。
借助真人形象的描寫莊子向我們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德性”,勸導世人少些計較,萬事萬物都要順應其身的發展,不去強加改變。那種原始的不加修飾的行為才體現真正的道德。
(三)追求的人格。“至人”在道家是指超越世俗、優于常人,達到無我境界的人,莊子言“至人無己”。在書中《逍遙游》《齊物論》《外物》《田子方》等篇中都有提到。文中說:至人是神仙,火燒身不怕熱,置于冰川不嫌冷,雷電把山劈裂、風把海水振起也都不能驚嚇到他。“唯至人乃能游於世而不辟,順人而不失己。”在莊子的筆下,“至”都是表示最好的、最高的、最尊敬的意象,“至”字本身就顯示莊子心目中崇高的地位。
《莊子》中關于“神人”的篇幅并不多,《逍遙游》中說姑射山有神仙居住,他們不吃五谷雜糧,可以靠風和露水來飽腹,還可以騰云駕霧、御龍飛行,暢游在天地人間,翱翔于四海八荒。“圣人”是道家理想的最高境界,他與世俗意義上的圣人不同,《齊物論》介紹圣人是不會趨利避害,不去主動求得什么東西,存在于塵世之外的。雖然整部《莊子》中沒有更多的話語介紹神人和圣人這種高境界,但是短小精悍的語言更讓我感悟到莊子的精神追求:回歸自然、抱樸歸真、逍遙無為、與道一體,表達了莊子超越人生困境的努力追求。
《莊子》的題材選擇不同于儒家著作規矩端正,更多的是一種隨心所欲,體現出一種自由,正是如此也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造就了很多經典篇章。向往自然的灑脫,畸人的生存之道,莊子留給后人的寶貴財富值得品味。
總而言之,《莊子》這本書,是源于莊子對于社會和人生的感悟,創作的目的也是為了幫助人們走出困境。莊子的作品如同他自己一樣,在當時的背景下可以說是恢恑憰怪、新穎獨特、顛覆了人們的認知,不論是創作方式還是思想內涵都為后者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莊子》獨特的創作風格也給后人留下了很大的啟發,他的文章結構、語言風格、寫作手法等都值得去學習借鑒,開辟中國文壇的新天地。
參考文獻:
[1]方勇.莊子學史第三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0.
[2]張松輝.莊子考辯[M].湖南:岳麓書社,1997:14-16.
[3]孫義凱,甄長松.莊子通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22.
[4]錢政.莊子生平考[J].大眾藝術,2015,(13):6.
[5]栗子涵.從莊子《逍遙游》出發[J].漢字文化,2018,(S2):11.
[6]林升文.“莊生夢蝶”:思想的精靈翩然起舞[N].福建日報,2020,(2):3.
[7]馮學成.無用之木的妙處[J].西部廣播電視,2009,(12):13
[8]謝曉莉.畸人意象與莊子創作[J].文學教育(下),2019.
[9]張巖,顧思晨.用意象來表情達意[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2(13):36.
[10]趙真朋.淺談《莊子·大宗師》中的真人形象[J].大眾商務,2019,8(4):8
[11]李宏達.《莊子》中“至人”“圣人”“神人”“真人”關系再探[J].湖北經濟學院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4.
作者簡介:
魏寧,女,黑龍江綏濱人,佳木斯大學研究生,學科教學(語文)專業。
王永宏,通訊作者,男,遼寧岫巖人,佳木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現代漢語詩歌、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