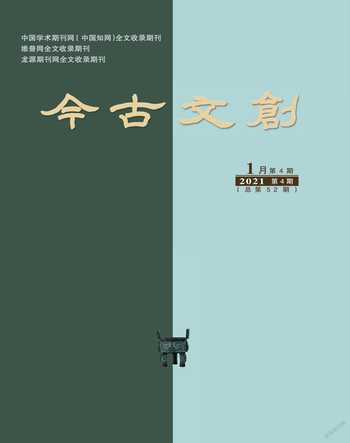“漂泊與成長”
【摘要】 兒童文學作家班馬以其強烈的個人風格,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兒童文學界掀起了一股“班馬風潮”,尤其是他筆下獨具一格的“漂泊式”少年形象令人記憶猶新。本文旨在以90年代盛行的“成長小說”中“少年出走”的傳統母題為切入點,來具體分析班馬作品中這一類母題的具體表現特征。其次,結合班馬對“漂泊少年”藝術形象的塑造,著力探討班馬兒童文學中“少年出走”這一類母題書寫中所存在的缺失,以期促進當下兒童文學中漂泊形象的全新建構。
【關鍵詞】 漂泊少年;出走母題;書寫局限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04-0014-02
一、漂泊與成長:班馬小說“少年出走”母題特點
班馬的兒童小說常涉及一個關鍵詞—— “漂泊與成長”,例如《上海街頭流浪記》中兩個少年歷經磨難最后乘長江輪向長江而去;《幽秘之旅》中主人公前往重慶協助破獲一個在川東地區的秘密流丐團伙;《野蠻的風》中主人公只身一人來到濱海小城;《沙漠老胡》中少年來到野蠻的沙漠冒險…… “漂泊與成長”已經成為班馬兒童小說中成長少年最鮮明的生存特征。本文將從以下四個角度來具體闡釋班馬小說中“少年出走”母題特點:
(一)少年形象設置
1.鬼頭鬼腦、行為頑劣的“壞學生”。班馬作品中的少年人物很直觀的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這類少年人物痛恨學校,常常把“我最恨學校”掛在嘴邊,不僅如此,還敢公然違逆老師父母,擾亂課堂紀律逃學,如《沒勁》中的“壞學生”李小喬就被老師稱之是“孫悟空”。少年天性的頑劣給予母題書寫成功的前提,同時“壞學生”也是班馬心中完美兒童的典型。因為班馬眼中的“壞學生”就意味著違反成人世界的預設,尊崇其生來自由的本性,極大保留了童年精神的本質性寶貴品質。
2.機智聰慧、操作能力強的行動派。班馬是兒童文學的鬼才,他筆下少年人物的性格也帶著“鬼”的影子。在《幽秘之旅》中鬼小子李小喬一人破獲秘密團伙,盤下“小喬火鍋店”,憑一己之力如數奉還三十萬元。班馬極其倡導“游戲精神”,因而少年主人公另一鮮明特點即慣于“做事”而非“言說”,例如李小喬最信奉的便是柳老師宣揚的“操作性思維”,即身體和大腦的及時聯動,他的“一切自動控制系統都不是靠‘想’而是靠‘動作’反應的”。
(二)出走地點設置
1.神秘滄桑——獲得生命厚重感。班馬兒童作品中少年出走地點大多選取遠離都市生活而具有特殊神秘感的地點,如湖底的古城、駭人的鬼碼頭、霧氣繚繞的鬼船等等,這些地方獨具歷史文化的厚重感。在少年主人公進一步觸摸歷史、貼近神秘、與遠古對話的過程中,逐漸喚起少年對生命的共同體驗,最終得以成長。例如,《魚幻》中都市中學生盯著湖底若隱若現的古城,內心深處涌起一股敬畏。
2.野性荒蠻——獲得生命力量感。班馬出生于上海,其作品中少年出走通常會以上海為出發點,而班馬通常選擇的落腳點卻與溫婉細膩的上海大相徑庭。他筆下的少年偏愛自由的曠野、野性的鄉村、荒蠻的西南腹地。比如《幽秘之旅》中,作者著重強調重慶的野性,“到處有一種大大咧咧、爽爽氣氣的味道,你講話吼兩聲,狠狠拍拍店鋪老板的肩胛,都沒有關系”。班馬期待的變化是在少年出走的經歷中把“城市小白臉”逐步弄野的過程,在與野性生活的過程中逐步擺脫桎梏,喚醒生命的野性力量。
(三)少年人物關系設置
1.盟友。班馬作品中的出走少年通常在學校是邊緣人物,好學生自然不與他們來往,而在校外的冒險奇事通常需要盟友的搭檔和支持,因而班馬善于設置盟友式的伙伴,來幫助主人公渡過難關獲得成長。在《上海街頭流浪記》中,李小喬與洪都拉斯聯手對付白蛇精,在過命的交情中酣暢淋漓地釋放了情緒并攜手逃亡;在《六年級大逃亡》中,在面對警察的盤問,陌生女孩安麗愿意為李小喬作保并相信他的不能言說的秘密,小喬第一次感受到了朋友的理解與信任,獲得了溫暖的關懷。
2.引路人。“童年時期,人的理性尚處于暫未發展的狀態 ,故而周圍環境、價值觀念、文化氛圍往往以一種無意識滲透的方式,滲透沉積于人的無意識之中。”少年的成長往往會受到成人的無意識引導,并逐漸培養少年正確的人生觀。在《六年級大逃亡》中,有勁的柳老師是李小喬的思想引路人,他帶給小喬動物園式的“玩耍課堂”,教會他極具操作性的“玩的思維”,在逃亡的五個月中,慈祥的班馬叔叔是李小喬的心靈引路人,他時時刻刻陪伴著他,傾聽他的流浪故事……他們都是少年兒童與“外面的世界”融合重新建構自身的重要引導者。
(四)少年出走模式設置
1.單一線性模式。少年出走母題在班馬作品中以單一線性情節模式出現,通常表現為以城市少年的出走歷程為主要線性框架,隨著少年的不斷移動,作者通過少年之口轉述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呈現出一個完整的外在世界。如《那個夜,迷失在深夏古鎮中》中,讀者跟隨著主人公的視線與行動腳步探秘陳園;《少年的野蠻航行》中,都市少年一人乘著輪船去遠房親戚家,一路上跟隨粗蠻的丁寶尋訪大魚,跟隨船長前往鬼碼頭、巧遇乘船的古代人……在人物行進的過程中串聯起一個個神奇的故事,向讀者呈現出一個精彩紛呈的出走之旅,有身臨其境之感。
2.一波三折曲折模式。少年的流浪歷程是在不斷地冒險中進行的,“情節模式可概括為受阻—破阻—受阻”的過程。幾乎誰都承認這樣一個現象,即孩子們特別喜歡看“歷險記”“奇遇記”一類的作品,班馬的兒童文學作品中也不乏奇幻冒險、坎坷曲折、柳暗花明的曲折情節。
如《幽秘之旅》中白頭翁叔叔突然失蹤,小喬情急之下買下火鍋店用于自保,一路上與匪徒斗智斗勇,與警察特工密謀脫身,全程屢遭險境,卻又最終化險為夷。使得讀者被曲折的故事情節所吸引,獲得情節急速變奏的快感。
二、班馬“少年出走”母題書寫局限
(一)性別固化
通過對班馬兒童作品的閱讀,不難發現“少年出走”母題的主人公通常為十至十五歲左右的少年,而缺少女性兒童作為主人公的母題書寫。班馬倡導“力的美學”,主張以野性的環境去滋養童年,于是他筆下的少年形象大多如李小喬一樣性格張揚、無所畏懼,敢于逆反冒險,象征著一種向外拓張、不斷追尋的生命上升狀態。而女性兒童在班馬母題書寫的過程中通常是以配角或者對立人物出現,如《六年級大逃亡》中總是裝模作樣令人討厭的班長孫琴,削弱了女性角色表現的多樣性。
在班馬的寫作中慣于給予人物性別化的類型特征,即男孩——自由張揚的原始生命形態;女孩——文靜乖巧的理性生命形態,這主要是因為在班馬的兒童觀念中認為女性兒童所代表的是一種平和內斂的生命形態,并不能有效地在兒童文學作品中傳達其“力的美學”思想。在性別固化的觀念下,成人話語再次顯現,作家按照成人對兒童性別的不同預設制定不同的人物性格。雖然班馬受到現代兒童文學觀念的影響,但仍舊無法跳脫出文化語境的限制。
(二)人物形象臉譜化
班馬“少年出走”母題的書寫中人物形象缺少變化呈現臉譜化趨勢,如李小喬為代表的壞學生形象,在重復書寫的過程中缺少新質。同時,班馬過度放大出走少年的聰明才智來滿足個人的文學想象,這與兒童文學作家強烈的“言說欲望”有著密切的聯系,兒童形象成為他們表達觀念的載體,失去了兒童作為審美主體的品質。
母題中關于父母老師的書寫則呈現出作家固有的刻板印象,將父母老師放置在兒童的對立面表現為“惡”的一方,著力突出少年以出走為反叛方式的正義性,可能會使兒童讀者對父母老師產生抵觸。如《六年級大逃亡》中的“曹大頭”曹老師常常對學生暴力相向,掄起巴掌就打,最后甚至把小喬送進了警察局。雖然作者主張從兒童本位出發充分理解和關心兒童心理,然而對老師形象臉譜化的刻板書寫會造成與現實的脫節,在兒童文學作品中塑造出畸形的教師形象,對兒童產生不正確價值觀的引導。
(三)逆反式的與被動式的成長敘事則顯得過剩
班馬作品中少年主人公的出走通常都不是一種自主的選擇,而是被逼到絕境的無可奈何。如《沒勁》中校園廣播喇叭全校通緝李小喬,最終被逼無奈只能踏上出走的道路;《少年的野蠻航行》中主人公被父親托付給船員,在非自主選擇的情況下被迫航行出走……可見少年還未建立起獨立的自主意識,仍處在被動前進的初級階段。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兒童文學中的成長小說仍處在摸索時期,曹文軒甚至談到“中國幾乎沒有成長小說”,班馬作品中的出走少年建構也處在朦朧的探索階段。少年出走的中國式書寫班馬傾向于建立在外部壓力上進行,而非兒童內心出走意愿的自主表達,被動式的成長書寫使得主人公始終在外力的作用下前行,難以建立起自我同一性,因此被動式的成長其實也是成人話語施加在兒童身上的又一次體現。顯然,班馬雖極力倡導兒童本位論,且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傳統浪漫主義對兒童文學書寫的美化,但仍舊無法擺脫文化語境中成人本位的桎梏。
三、小結
班馬在當代兒童文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本文通過介紹兒童文學作家班馬及其系列小說來闡釋班馬作品中極具代表性的少年出走母題,盡可能發掘班馬蘊含在母題書寫中的強烈個人特點,感受班馬在兒童文學母題書寫上做出的大膽創新。同時,本文對班馬母題書寫局限的總結以期促進當代兒童文學的創作,以及完善當代兒童文學中兒童形象的全新建構提供理論借鑒。
參考文獻
[1]班馬.六年級大逃亡[M].南京: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1995.
[2]班馬.幽秘之旅·少年絕境自救故事[M].蘭州:甘肅少年兒童出版社,2012.
[3]方衛平.我們所不知道的童年更深處——重新解讀班馬[J].南方文壇,2013,(05):105-110.
[4]班馬.上海街頭流浪記[M].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
[5]黃金娟.論曹文軒少年小說中的成長母題[J].沙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2):3.
[6]孫恒存.論曹文軒成長小說中的流浪情結——以《根鳥》為例兼談曹文軒的文學觀[J].名作欣賞,2008,(06):77-79.
作者簡介:
許超,女,漢,江蘇常州人,現碩士研究生就讀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兒童文學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