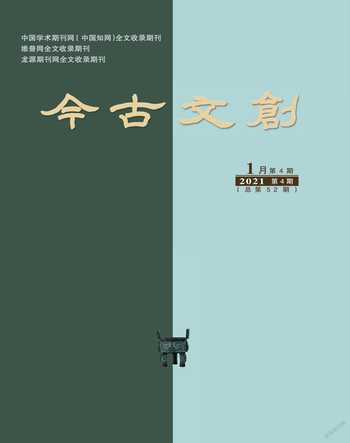中國當代科幻小說中的民族歷史
鄧鐘靈
【摘要】 中國當代科幻表現出對歷史的濃厚興趣,出現了以歷史為題材的新分支,也提供了從歷史視角解讀未來題材的新方法。中國當代科幻中的民族歷史書寫具有自身的獨異性,與歐美相比,外星入侵的書寫折射出民族被侵略的歷史,這一歷史痛點成為中國當代科幻歷史意識的重要部分;與中國科幻其他時期相比,當代獨特的歷史興趣伴隨著強烈的悲觀色彩;與主流文學相比,呈現關注整體性的特征。對歷史的書寫在當代科幻內部也存在差異,“新生代”對人類危機的民族寓言式書寫,因時空背景的差異,并不能喚起民族主義式的人類共同體意識,甚至會在無意中加強民族意識;“更新代”的歷史類科幻,則表達了對人類共同體的懷疑和對民族身份的自覺追求。
【關鍵詞】 科幻;民族;歷史;劉慈欣;“更新代”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04-0022-03
一、科幻中的歷史新熱
科幻似乎總是關于未來的,將科幻與歷史相提并論,是近年來才在中國科幻“更新代”中開始的一股新潮。作品集《中國科幻大片》《科幻中的中國歷史》《時間外史》等的相繼出版及相關批評共同塑成了“歷史類科幻”這一新的分支。這是就創作題材而言,而在此之前已有研究者從歷史角度將劉慈欣的“三體”系列闡釋為民族寓言。劉慈欣在其科幻理論與隨筆、訪談中顯露出強烈的未來意識與目的性,看起來與歷史性解讀格格不入。但是正如寶樹在《當科幻遇到歷史》中所寫:“科幻中蘊含著更廣大深遠的可能性。它仿佛雙面的雅努斯神,既朝向未來也回望過去。”這種可能性其實一直都在—— “當人們投入一種嶄新的未來時,也必然帶著他們的整個歷史。”[1]
“三體”系列本名“地球往事”,整個故事講述人類作為一個種族與外星文明的遭遇。當接納了科幻的歷史視角,就會發現“種族”與“民族”的天然相似性、可類比性,自然聯想到科幻對未來種族故事的書寫與民族歷史之間的聯系。
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將小說情節與中國歷史一一比附,尤其是對于“三體”系列這樣復雜的作品。《科幻式的異文化表達——? 〈三體〉的文學人類學解讀》很有新意:“從各種意義上來說,三體文明都是對日本文化的一種影射。當然,以歷史的整體眼光來看,三體文明更多的可能是近代以來所有妄圖瓜分中國的列強的共同象征。人類的幾次反抗則可以視為近代中國為探索救亡圖存的各種嘗試,中間人類科技的進步類似洋務運動的短暫繁榮,最終‘末日戰役’的一敗涂地影射了甲午和辛丑的慘象。”[2]但后文一發不可收拾,直至將羅輯類比為早期共產主義領袖,明顯過于牽強。
相比于龐雜的“三體”系列,中短篇小說或許更適合進行這種原型解讀。以郝景芳的中篇《弦歌》為例,故事設定在未來,已經高度發展的地球文明遭到了外星鋼鐵人的入侵,他們居住在月球上,取用地球的資源,只攻擊抵抗的地球軍隊,對平民則比較寬容,承認鋼鐵人的統治就可以平安度日,而對于地球上的科學藝術群體甚至還給予保護。面對這樣的入侵者,抵抗的意義令人懷疑。主角在經歷一番內心掙扎之后,選擇繼續抵抗,最終以意料之外的方式成功地摧毀了鋼鐵人的基地。
《弦歌》并非歷史類科幻作品,可是讀者(至少對許多中國讀者而言)可以很容易地遇見非常熟悉的歷史的真實:鋼鐵人的進攻與統治可以聯想到侵華日軍“大東亞共榮圈”的謊言;臣服、投靠甚至崇拜鋼鐵人的地球人與當年的親日派如出一轍;而少數抵抗者絕望的抗爭正對應我國軍民決絕的抵抗。郝景芳細膩的筆觸延伸到無數細節與非常細微的心理,這些細節與劉慈欣在《三體II:黑暗森林》中“思想實驗”的推論不同,它們似乎來自記憶,來自一個民族真實的創傷記憶。
這種民族的創傷記憶也可以不借助“種族”的寓言,例如韓松的短篇《一九三八年上海記憶》。在1938年上海的亂世中,人們選擇通過一張神奇的碟片回到過去,尋找個人與國家的另一種可能性。這篇小說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核心”,也并非對1938年上海歷史的真實回憶,而像是錯亂的夢境,但危亡與絕望的歷史心境是真實的,透過歷史的無數可能性永恒地烙在“我”的記憶里。
上述科幻小說中明寫或潛行的民族記憶均有關外族入侵,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中最刻骨銘心的痛點,它通過“民族”與“種族”的可類比性進入以種族為描寫對象的科幻視野,并成為中國當代科幻的歷史意識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外族入侵的民族記憶還會以更加隱秘的方式潛行于其他科幻小說中,例如劉慈欣的《天使時代》與寶樹的《關于地球的那些往事》。前者將其推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后者則在億萬年以后思念已被外星文明毀滅的家園。
二、中國當代科幻中歷史書寫的獨異性
在世界科幻的譜系中,與外星文明的相遇自凡爾納、威爾斯的時代起就一直是熱門題材。如前所述,由于民族與種族顯見的可類比性,對這種相遇的幻想往往隱含著作者各自的民族記憶。歐美作家對地球以外的空間、文明有強烈的探險、征服的欲望,背后是大航海時代的開拓欲望與殖民歷史。中國科幻師法西方,對這一舶來的題材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演繹。從前述文本中即可看到,中國科幻作家筆下的征服者角色往往由外星文明扮演,而地球人只是被動地抵抗。這種演繹自然來自中國近代被侵略的歷史記憶,即使當代科幻作家身處的已經是獨立富強的中國,但民族歷史的慣性已經塑成了內心深處對“他者”的恐懼。這種表述還不夠完整,中國當代科幻對這一題材的處理其實還有更加豐富的層次性,一種是對高級文明的史前書寫,如《贍養上帝》《關于地球的那些往事》;另一種是以中國人作為拯救地球危機的英雄主角,如“三體”系列的羅輯、章北海,《弦歌》中的林老師、齊躍、陳君。前者對應中國古代領先世界的輝煌歷史,后者對應當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中國科幻史上,當代科幻第一次顯露出如此濃厚而沉重的歷史意識,在此之前,中國科幻更多地向前看而很少回望。中國科幻歷史上與當代最相似的時期當屬晚清,晚清一代與甲午戰爭的時間距離和當下與抗日戰爭的距離有著巧合的相似。不同的是,彼時的晚清尚未脫離民族危機,而如今的中國富強安定。相較而言,晚清一代科幻作家應該比當代科幻作家的歷史痛感更加強烈、清晰,但事實并非如此。晚清的作者帶著迫切的民族焦慮想象未來,興致勃勃地建構了一個又一個烏托邦,立身貧弱卻豪情萬丈;當代的科幻作家卻在大國崛起的語境中一次次回憶民族的疼痛、凝望人類的末日。
這種反差可以用“時間”來解釋。晚清科幻的時間尺度以中西方的文明差距為參照,跨度不過百年左右;而當代科幻的時間以宇宙文明的興衰為尺度,跨度可達數億年或直抵末日。時間觀念上,晚清科幻作者經西方科學理性(尤其進化論)的沖擊,跳出了古典的循環時間觀,逐漸建立起線性前進的時間意識,“進入的是一個新的時空,這是由工具理性所規劃的時空,而這一時空的指向,是建設新的世界和新的國家”[3]。而當代科幻作者在擺脫了民族危機并基本實現了晚清一代的強國理想后,所探尋的是宇宙的終極。在巨大的時間跨度上文明以星球、星系甚至是整個宇宙為單位更迭,日常感知的線性時間被納入了更大尺度的循環之中,這就使得“歷史”與“未來”不再處于“現在”的兩端,而具有了某種同一性。在晚清一代的時間軸上,歷史的苦難會因為國家的發展而成為永遠的歷史,因而只需奮力向前;而在當代科幻的世界中,文明的演變會在漫長的時間與廣袤的空間中無數次循環,歷史的痛苦還將無數次重演。在這無盡的循環構想中,一個文明的興衰不再具有真實歷史的或然性,而在大尺度上必然走向衰敗滅亡的宿命。這種認識使得當代科幻呈現與晚清不同的悲觀態度,并在科技突飛猛進的時刻出現整體性的社會性轉向。
共時層面,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科幻的民族歷史書寫也顯示出鮮明的獨異性。最突出的特點是宏大敘事,這同樣可以用 “主流文學”/“純文學”與科幻之間經典的“內-外”之別來解釋。主流文學將整個時代、整個民族的記憶內化于個人的經歷與感受;科幻則將個人符號化,納入民族歷史的整體書寫中。
上述特性在“新生代”與“更新代”之間略有差異,但同大于異。從前文提到的作品集中可見,雖然在后者中出現了社會性轉向與向內的傾向,但仍延續著整體性的視野與“個人”的符號化。
三、“當代”的內部演變與現實觀照
強調科幻中的“種族”與歷史中的“民族”具有可類比性,是一種解讀方式。但二者的差異同樣不能忽視,它們為理解中國當代科幻中的民族歷史及其意義提供了鑰匙。
從歷時性角度,“種族”是“民族”的延伸,是經濟全球化與問題全球化時代呼喚的“人類共同體”。從“民族”到“種族”,是利益單位與視野擴大的結果,這種延伸其實已經發生過多次。以中國歷史為例,從原始社會的“部落”到分封制下的“國”,再到近代的“民族國家”,都可以看成相似的延伸模式,并形成一條延伸的鏈條。從《贍養上帝》《鄉村教師》《關于地球的那些往事》以及阿西莫夫的《銀河基地》等科幻作品中,還可以看到這種延伸的繼續:它還可以由“人類”擴展到太陽系、銀河系,甚至是整個“碳基文明”,或者在一些關于“平行宇宙”的作品中延伸為單個宇宙,如《纖維》《六道眾生》。
現代性理論會強調這種延伸的內在差異,認為進行到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一環時,事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安德森將“民族”界定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4],這種界定與中國歷史上其他共同體的最大區別或許在于“有限性”。即使有地域的邊界與他者(蠻夷)的存在,但由于中國古代“天下”觀的存在,這些有限的共同體都可以被視為是無限的;只有到了近代,在西方諸國的參照中建立了民族國家意識,才對邊界、主權等概念有了“有限”的認識。從“民族”到“種族”的延伸中又發生了改變。近現代世界歷史中,各競爭主體雖力量不均但在身份上都是對等的民族國家;但在地球人類與宇宙他者之間,我方的有限性依舊有效,但“他者”卻變成了無限與未知的。
具有這種差異的“人類共同體”想象是否能像“民族共同體”一樣激起某種熱情——類比“民族主義”的“人類主義”?“新生代”與“更新代”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新生代”科幻作家劉慈欣相信并呼喚這種“人類主義”精神,集中表現于其作品中為人類而犧牲的英雄主義;但“更新代”的作家們則很懷疑這種團結的意義與有效性,例如《弦歌》中借人物內心活動所說:“愛國主義早已被詬病,此時的‘愛球主義’則更像一場笑話。”[5]郝景芳將文中“英雄主義”“民族氣質”的消散歸因于人類面對強大外星文明時的弱小與潰敗,這種因果關系在民族歷史中是不成立的,外族入侵反而會激起并加強民族主義,英雄主義也正是在此時最為彰顯。這種因果關系的成立正在于“他者”的無限性與前述循環的文明觀、時間觀,所有的反抗都會因為失敗的宿命而失去現實意義。即使在慣性(民族主義的慣性或者“新生代”創造英雄的慣性)的驅動下有少數人選擇繼續抵抗,“他也一定知道這不是英雄的抵抗,而是向悲劇結局邁進的毀滅的抵抗”[6]。劉慈欣崇高的悲劇感到“更新代”作家這里演變為絕望的反抗,宏大敘事中的英雄主義淪為個人選擇之一種。
其實“更新代”的很多“新變”都可以在《三體III:死神永生》中找到源頭:他者的無限性、必然滅亡的命運、宇宙維度的循環……正是這些因素最終殺死了劉慈欣所崇拜的英雄主義,而必然滅亡的命運對文明與藝術的重新肯定,或許也可以看做“更新代”科幻社會性轉向的部分原因。
共時地來看,“民族”與“種族”對應著共同存在于“現在”的民族國家與“人類共同體”。在現實世界中,后者并未獲得相對于外星文明才成立的政治性與主權。另一個不容否認的現實是,“人類共同體”與民族國家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即使作者關于人類共同體的書寫只是對民族歷史的借鑒,讀者卻也只能在民族歷史中找到現實的對應;外星入侵的描寫一遍遍地將讀者拉回民族歷史的痛點,科幻中所宣揚的英雄主義也只能在民族主義中聽到回聲。那么科幻對人類種族的民族式書寫,是否會反過來造成民族意識的加強與人類共同體意識的削弱?
這對劉慈欣而言或許只是意料之外的逆轉,但對“更新代”作家而言已經是一種自覺的追求。“三體”系列還有另一種民族寓言式的解讀:將天真的地球文明與黑暗森林式的宇宙,對應于自成一體的古老中國與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競爭[7]。在這組關系中,宇宙循環、他者無限等悲劇因素被取消了,劉慈欣的態度清晰地表現為發展進步的目標與不惜犧牲一切的信念。劉維佳的短篇《高塔下的小鎮》具有與“三體”系列相似的寓言結構:田園牧歌般的小鎮與周圍弱肉強食的蠻荒世界的對立設定。不同的是,劉維佳的小鎮是被高塔保護起來的,因此提供了兩種選擇:小鎮中的人(自成一體的中華文明)可以走進蠻荒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但再也無法回到小鎮;也可以安然地故步自封,美好但停滯。可以說劉慈欣的民族寓言是已經發生的歷史,而劉維佳提供了歷史的或然性;也可以說二者反映了中國歷史的不同階段,以及中國科幻在不同階段的身份焦慮。劉慈欣的民族寓言與外族入侵的歷史相聯,關注點在于如何生存,而當時中國科幻的身份焦慮是如何在歐美主導的國際科幻中立足,同樣是關于生存的問題。劉維佳的寓言發生在一個假想的“選擇前”的時間,但安全穩定的小鎮與弱肉強食的叢林卻明顯是當今中國與國際環境的抽象,生存已經不是問題,困境在于選擇。投射出中國在融入國際社會、高速發展時的民族身份焦慮,以及劉維佳等“更新代”科幻作家的身份焦慮:如何用科幻講出中國故事,如何形成科幻的中國特色。正是在這樣的大國氣象與身份焦慮中,“更新代”作家創作了一大批以中國歷史為題材的科幻小說。其實無關歷史,立意在當下。如果說劉慈欣“在歷史感消逝的時代,通過想象未來去觸摸歷史”,那么“更新代”則是“在未來不可知的迷茫中,通過扣訪過去以尋找前進的可能性”[8]。
科幻只與未來相關的時代已經過去,或者從未存在過。在科幻的符碼里,可以看見一個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參考文獻:
[1]寶樹.科幻中的中國歷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2.
[2]張未未.科幻式的異文化表達——《三體》的文學人類學解讀[J].美與時代(下),2016,(5).
[3]楊慶祥.作為歷史、現實和方法的科幻文學——序“青·科幻”叢書[A].寶樹.世間外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4](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M].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5]郝景芳等.弦歌:中篇科幻小說集[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7:24.
[6]郝景芳等.弦歌:中篇科幻小說集[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7:22.
[7]王瑤.全球化時代的民族寓言[J].中國比較文學,2015,(3).
[8]王瑤.“新青年”的科幻進行式——“更新代”科幻作家筆下的中國與世界[A].王瑤.未來的坐標: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科幻論集[G].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