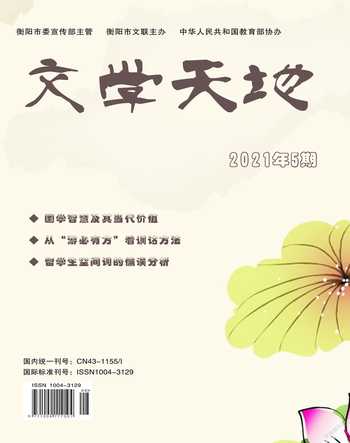淺談法海寺壁畫帝釋梵天圖的時代意義
摘要:法海寺壁畫為明代壁畫藝術水平的最高代表,其不論在研究佛教藝術方面還是從繪畫本身的價值上,都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其中位于大雄寶殿內的《帝釋梵天圖》現如今保存完好,從材料技法、畫面形式語言、審美價值上來說都極具代表性。本文試圖從帝釋梵天圖兩幅壁畫出發,初步分析其中二十諸天人物形象的代表意義,以期傳遞它所蘊含的時代意義以及對當代社會的價值。
關鍵詞:法海寺壁畫;二十諸天;社會價值
一.助名教而翼群倫的社會價值
法海寺是由明代統治者主持修建的皇家寺院,建成于明正統四年——八年( 1439- 1443),位于北京西郊翠微山南麓。據法海寺碑文記載,緣起是明英宗寵宦太監李童“托夢”說,而后由皇家主持,李童集資,漢藏兩族官員僧眾共同設計修建而成,可見法海寺和政治的密切聯系。明代是中央集權制發展到頂峰的一個時期,歷史上歷代官方所推崇的思想文化幾乎都與統治者的喜好密切相關。佛教雖為外來文化,但在其傳入中國之后一直和本土思想文化融合得比較好。早在北周時期,中國主流思想文化逐漸有了儒釋道三者鼎立發展之勢,佛教在唐朝發展到鼎盛,統治者推崇佛教所追求“彼岸”的超凡脫俗的思想境界。而儒學一直到北宋中期發展出新形態,即理學時,才得到統治者的青睞,又替代佛教成為官方的統治思想。直到明代,統治者又喜愛佛教思想,明初朱元璋極為重視佛教的教化功能,認為其可以“暗理王綱,于國有補無虧”,于是他招募僧人參政。宣德年間,統治者還曾特賜西藏喇嘛住持寺廟,以表關懷和重視。這些都大大促進了儒釋道的融合,促進了佛教世俗化、本土化的進程,佛教在明初成為官方的統治思想,中后期則和道家融合,無明顯區分。
據《楞嚴經憅》記載和相關研究資料證明,法海寺廟中的壁畫繪制者為當時的宮廷畫師。明代的畫師人數之多,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據徐沁《明畫錄》所記,明代畫家人數有850余之多,而《圖繪寶鑒·續編滕序》有述:“自軒轅以至宋,又自宋以至元,(畫師)凡一千五百余人。”可見明代繪畫發展之盛。且文化思想均服務于政治,明代宋濂在其畫論《畫原》中強調繪畫“致使圖史并傳,助明教而翼群倫”的作用,其觀點自然為治國安邦出發。他認為文字不能表達的,可由繪畫制圖顯示。在當時“助名教”是為封建禮教教化人的作用,筆者認為其中還有宣傳官方主流思想的含義。宋濂作為“開國文臣之首”,50歲才應朱元璋之邀成為明代重臣,所以他提倡、反對什么,是極具權威性的,他的“助名教而翼群倫”的繪畫教育理論自然對明初藝術發展成產生了重大影響。聯系到法海寺壁畫,在當時封建制度下,教育并未普及平民百姓,識字通史的人占社會群體的小部分,對于大多數人而言的“教育”便是通過識圖和口傳。法海寺壁畫作為宗教題材的壁畫,本就具有“傳教”的功能意味。法海寺壁畫在整體上為明代宮廷繪畫的樣貌,又宮廷繪畫一脈相承,法海寺壁畫的風格來源不難追溯到唐宋宮廷院體畫,加上元代的繪畫主流以抒發主觀意趣、以簡為上、追求古意和士氣。在佛教世俗化和思想開明的背景下,宮廷畫師融合了這種較為自由的繪畫精神,在法海寺壁畫的繪制上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既表現了當時宮廷繪畫的特點,也將佛教神祗人物形象進行了世俗化的處理,更貼近現實,具有親和力,便于發揮“助名教而翼群倫”的功能。
二.二十諸天人物形象的意義
二十諸天是中國佛教美術歷來都喜愛表達的題材。其中這些神祇皆非佛教原生神祇,幾乎都是印度佛教自外部(其他宗教、民間信仰等)吸收而來。寺觀壁畫里常將其作為整體組合圖像或是單個神祗圖像進行繪制展現。根據佛教文獻記載,約南北朝后期創制的“金光明懺法”中首次出現了較為完整的諸天組合,隋代天臺智者大師依據《金光明經·功德天品》制定了《金光明三昧懺法》,后代將其整合簡略成《齋天科儀》,又結合《金光明經·鬼神品》等文獻資料,選定了二十諸天人物。另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時期其實因為道佛相融的現象出現,當時的二十諸天實則加入了四位別的天神(其中三位為道教神明),成為“二十四諸天”。但是在法海寺大雄寶殿的兩幅帝釋梵天圖中,卻無任何道教神明的蹤影。有學者觀察總結道:只有在法海寺壁畫中才能看到唐宋時代佛教一脈相承的“帝釋梵天圖”的形象。雖然法海寺壁畫描繪的是“二十諸天”而不是參雜了道教神明的“二十四諸天”,但在法海寺殿中的三大士圖的文殊菩薩圖和普賢菩薩圖里都出現了以道教形象為代表的“信士”老人,且在構圖和、神態、動態方面也有互動和相似性,值得考究。所以道佛的融合并未在法海寺壁畫中完全無體現,只是相對比較含蓄。筆者猜測,佛道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可能法海寺壁畫的繪制時期正是為這個過程的見證。所以帝釋梵天圖里沒有道教神明的出現,但這并不妨礙筆者在此探討帝釋梵天圖的社會價值和時代意義。
法海寺壁畫帝釋梵天圖分為東、西兩壁。西壁以大梵天為首,描繪了包含侍女、隨從和鬼怪在內一共十七個人物形象。從右到左依次為帝釋天、北方多聞天王、西方廣目天王、菩提樹神、辯才天、月天、鬼子母、散脂大將、密跡金剛、閻摩羅王。東壁以大梵天為首的行進隊伍包含侍女、隨從和鬼怪在內一共十九個人物形象,從左到右依次為大梵天、東方持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大自在天、功德天、日宮天子、摩利支天、堅牢地神、韋馱天、娑竭羅龍王。其中所有的神祗的形象幾乎都進行了漢化和世俗化的處理,不同于原傳說或造像中他們本來所形容的形象。這些改動和處理都是在基于一定依據上的,或反映了當時時代的背景。或傳達了神祗人物本身的象征意義,又或是傳達了統治者對于世間百姓的慰藉和護佑的心愿。接下來筆者選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神祗人物進行分析。
西壁中的訶利帝母,原為婆羅門教中的惡神,也叫鬼子母、愛子母。據佛典所記,“鬼子母”以其為五百鬼子之母。專食王舍城中人家小兒,但對自己孩子卻十分愛憐。佛陀規勸不從,為了訓誡她,遂以法力藏起她最疼愛的幼子賓伽羅,“鬼子母”于是驚悲狂亂。佛說: “汝有子五百,今僅取汝一子,汝已悲痛若是,然汝食他人之子,其父母之悲又將如何慟乎! ”鬼子母聞言便幡然悔悟,痛徹前非,皈依佛教,成為了專司護持兒童的護法神。而后其影響隨著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傳播而風行一時,加上民間素來就有求子心理,于是我國歷史上鬼子母便從兇惡的“食子惡鬼”漢化成慈祥的母神形象,多表現為生育女神、送子女神的形象代表。法海寺帝釋梵天圖中鬼子母便是貴婦人的形象,右手持寶扇,左手輕撫愛子畢哩孕迦的頭,她臉上的慈愛和溫婉與孩子稚氣天真的氣質相互照應,畫面充滿了溫情的氣氛和人性的光輝,讓人見之動容。對于人物形象的刻畫畫師既順應了佛典和傳說,又刻入了現實人性的內在情感,不愧為時代的經典之作。在當時醫療不發達的時代,兒童感染時疫是常有的事,人們非常渴望一位守護兒童的神靈來進行祭拜。通過對“鬼子母”慈母愛兒畫面的刻畫,法海寺壁畫表現出了時疫泛濫時神靈對孩子的保護和關愛,反映了人間社會的訴求,同時也傳達了佛教普度眾生的慈悲情懷。在政治方面,也傳達了政府對于百姓的關愛之情和祈求國泰民安的心理。
東壁和西壁繪制有四大天王,他們均為佛教護法神,也稱“四大金剛”。據佛教經典,須彌山腹有一山,名犍陀羅山,山有四山頭,各住一山各護一天下(四大部洲,即東勝神洲、南贍部洲、西牛賀洲、北俱蘆洲) 故又稱護世四天王,是六欲天之第一。佛教中的一切形象皆包含有深刻的教化藝術,比如四大天王中的東方持國天王,“持國”就是保持、護衛國家的意思,也代表修行人也要護持個人的身心。他的代表法器持物是琵琶,所以掌握著“風調雨順”中的“調”。南方增長天王的“增長”由梵語音譯而來,意為能傳令眾生。增長慧根。護持佛法。他的經典形象是手持寶劍,衍生為“鋒”,所以掌管“風調雨順”中的“調”。西方廣目天王如其名,擁有天清凈的天眼,觀察世界,守護人民安寧的生活。另相傳其為群龍的領袖,所以其法器為青龍。但在法海寺壁畫中其法器為青蛇。延伸含義為掌管“風調雨順”中的“順”。北方多聞天王的法器為雨傘(寶幡),執傘者,雨也。在帝釋梵天圖中其手持雨幢,掌管“風調雨順”中的“雨”。四大天王常為組合形象出現,在法海寺帝釋梵天圖中則為兩壁各兩個。古代即使是太平時期國土周邊還是時常有戰亂,明朝邊關戰事一直較為頻繁,北方有蒙古族侵擾,沿海又有倭寇時常登岸劫掠,各地農名起義繁起,朝廷在需要練兵籌握以備戰時之需。除了人為侵擾,還有各種天災。明英宗統治時期,國家各種自然災害屢發不斷,旱災、洪災、饑荒等等,給百姓帶來了很大的傷痛,也給國家帶來了大量損失,朝廷不得不出面賑災。即使在安世,各種天災人禍還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法海寺帝釋梵天圖中,四大天王均漢化成了明朝武將的形象,身披盔甲,手持法器,捍衛邊關的和平和人民的平安。他們本身也代表了“風調雨順”的含義,被人們寄托了安穩、豐收、祥和的美好心愿。帝釋梵天圖通過對現實生活和佛教神祗人物的融合描寫,反映了明朝的時代背景下,政府和人民的美好心愿和寄托。通過對人物的神情、動態刻畫,佛教精神已經不是程式化的、有距離的,而是具有人文主義精神的、時代精神的、貼合現實的產物。反映了明朝時期朝廷對于宗教教化作用的支持和人民需要時代精神的支持和慰藉。
三.對于當今時代的價值
法海寺帝釋梵天圖中,不論是神祗人物還是侍女隨從的刻畫都是極為生動和細膩的,這些人物服飾、裝飾、神態、動態都不盡相同卻又互相呼應,極為和諧。禮佛行進隊伍氣勢浩大,嚴謹有序,宛如宮廷帝后王妃盛裝出行。畫師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好似將明朝宮廷生活搬到墻壁上去,將遙遠神秘的佛國世界和明朝宮廷現實生活融合到一起,消除了佛教的距離感,更具有親和力。一方面,我們現在可以通過畫面感受真實的明朝宮廷生活的華貴艷麗,感受當時的物資豐盈。畫面中奇珍異獸的出現也彰顯了國力,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明朝的開放程度。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宮廷使用的服飾、文玩、器具。為研究明代宮廷生活和社會提供了豐富鮮明的圖像資料。
對于當今社會來說,社會指導精神的主題性創作仍然在繼續,法海寺壁畫通過對佛國世界的人性化描繪,為當時社會成功樹立起了精神追求的目標。誠然,經典不可復制,但我們需要優秀文藝作品來充實現實生活和寄托人民的美好愿望和期盼,法海寺壁畫作為古代經典之作對我們當今進行精神文明建設的路徑是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的。我們應當在保護、傳承經典文藝作品的基礎上,進一步弘揚當代的時代民族文化和社會主義精神,為新時代的中國的精神文明建設添磚加瓦,為我們的祖國躍升“文化強國”而服務。
參考文獻
[1] 張淑霞.北京法海寺[M]北京:北京市石景山區文物管理所編,2001
[2] 金維諾、羅世平.中國宗教美術史[M]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1995
[3] 程至的.中國歷代繪畫理論評注(明代卷)[M]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9
[4] 郭麗平.北京法海寺壁畫中的藏傳佛教藝術因素探析[J].中國藏學,2010
[5] 林輝.北京法海寺壁畫的歷史意蘊和文化精神[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9
作者簡介:曹玉斌(1996— ),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湖北美術學院學生,碩士在讀,主要研究方向:壁畫與綜合材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