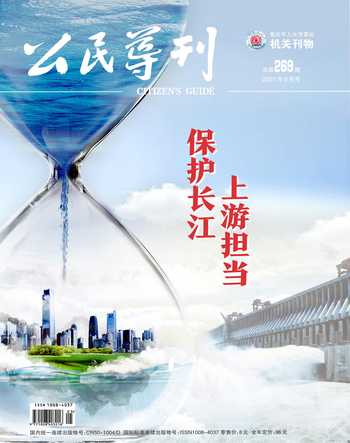勞動法的歷史故事
目前,我國勞動保障的相關法規如同一座頂天立地的大廈,不但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而且“風雨不動安如山”。然而,它的由來與變革,卻經歷了一個復雜而又曲折的過程。
新中國成立前的勞動規定
為了維護工人利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1922年8月16日發動了大規模的勞動立法運動,提出《勞動法大綱》19條等。大綱中要求實行8小時工作制、保障工人最低工資和享受勞動保險以及保護女工、童工等。大綱規定,禁止雇傭16歲以下的男女工,禁止18歲以下的男女工擔任劇烈、有害衛生及法定工作時間外的勞動,重工的法定工作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等。
大綱發布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向全國工會要求向工人廣泛宣傳,征求工人的意見。要求將《勞動法大綱》納入憲法,但是這一代表工人利益的《勞動法大綱》并未得到當時政府的承認。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才產生了真正代表職工利益的勞動立法。1931年11月7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
抗日戰爭時期,各邊區政府也曾公布過許多勞動法令,如晉冀魯豫邊區1941年11月1日就曾公布過《晉冀魯豫邊區勞工保護暫行條例》。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1948年8月召開的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了《關于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對解放區的勞動問題提出了全面的、詳盡的建議,對調整勞動關系提出了基本原則。
各個解放區的人民政府也曾先后頒布過不少勞動法規。而這一切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勞動相關立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的相關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目的都是為了促進就業,解決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40萬城市人口的就業問題。
用人單位和個體勞動者之間雙方地位并不是完全對等的,相對而言,用人單位處于強勢地位,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而法律是一個調整器,要給予弱勢群體更多保護,所以勞動法更傾向于保護個體勞動者。
1950年,勞動部公布了關于勞動爭議解決程序的規定,規定提出:如果勞資雙方有爭議的首先協商,協商不成的再調解。調解一般都會有行政機關參與,調解不成再至仲裁。今天我們相應的勞動爭議,在法律當中也基本是按照這樣的程序進行。所以上世紀50年代頒布實施的這一勞動爭議解決程序,對今天的勞動規定影響也很大。勞動者遇到問題,最便捷、最經濟的解決方式就是勞動仲裁。
從1953年起,我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
上世紀50年代開始頒布的勞動保險法,其內容和今天并不完全一樣,但是那時候的整體思路一直沿用到現在。
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當中,我們國家的法制都處于相對停滯狀態,因此勞動法也處于停滯狀態。
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盡管勞動法還沒有制定出來,但出臺了很多行政規章、部門規章和行政法規。這也為勞動法的頒布實施奠定了基礎。
1978年 5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獎勵和計件工資制度的通知,這對鼓勵工人工作的積極性具有很大意義。
有些特殊行業的安全問題,總是不時地給我們敲響警鐘。國務院1982年頒布了《礦山安全監察條例》《鍋爐壓力容器安全監察暫行條例》。這兩項法律文件是出于對整體勞動者安全環境的考慮,也是對勞動者安全工作環境權益的保護。
1988年國務院頒布了《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對女性職工在哺乳期或者懷孕期的勞動措施和保障做出了規定。
1992年,第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1993年,出臺了《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
兩把大火燒出的勞動法
1994年7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經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并正式頒布。
談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部勞動法,總是不由讓人將其與法律出臺半年多前那兩場災難相連——1993年11月19日,港資企業深圳市葵涌致麗工藝制品廠發生特大火災,87名工人失去生命,有名單的傷者51人。僅隔20多天,同年12月13日,福州市馬尾經濟技術開發區內的臺商獨資企業高福紡織有限公司再次發生特大火災,造成61人死亡,7人受傷。
接連兩場特大火災,舉國震驚。特別是致麗大火經《工人日報》詳細報道后,引發各大媒體跟進,立法保護勞動者權益話題由此進一步升溫。
“這兩把大火的確加速了勞動法出臺。讓大家感到,如果再不立法對勞動者權益加以保護,將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時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和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的張國祥更強調,勞動法得以頒布,關鍵取決于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取決于市場化的勞動關系必須要有法治來保駕護航。
作為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同時又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張國祥參與了勞動法起草工作。“不管付出多少辛勞、經歷多少曲折,都要制定出勞動法!至少我們這些參與立法的人的信念從來沒有模糊過。”張國祥說。
如果將追溯的目光投向勞動法頒布前的中國勞動領域,觸目所及的是市場經濟活力初現但又缺乏規則而又魚龍混雜的“二元交叉”局面:一方面,公有制企業用工依然僵化,盡管也開始引入市場因素,可以面向社會通過勞動合同招用勞動者,但卻是“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固定工仍然是用工主體;另一方面,非公企業用工極度自由,用工不簽勞動合同,也不繳納社會保險費等問題時有發生。
顯然,如果再不通過立法進行調整和矯正,必然會影響社會穩定。對此,時任勞動部部長的李伯勇1994年3月2日在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六次會議上做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草案)》的說明”中,便不無坦率地提出:“由于缺少比較完備的對勞動者合法權益加以保護的法律,在一些地方和企業,特別是在有些非公有制企業中,隨意延長工時、克扣工資、拒絕提供必要的勞動保護的現象時有發生,以至釀成重大惡性事件。”
致麗和高福這兩把大火便是這類“重大惡性事件”的典型。當然,作為勞動領域的基本法,勞動法強調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障,在深層次是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
眾所周知,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過程,而人力資源的市場化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后,我國勞動體制必須向市場配置勞動力方向發展,必須將勞動關系納入市場運行的軌道,并通過法律來明確勞動關系主體的權利、義務,維護勞動力市場秩序。
“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勞動者的擇業自主權和企業的用人自主權、分配自主權,對于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勞動力市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將會起到強有力的推動作用。”這是勞動法起草小組負責人、時任勞動部副部長的張左己于勞動法頒布后在一篇文章中談到的。
事實上,在勞動法實施后的幾年里,我國勞動力市場比較快地扭轉了計劃用工與終身制、市場選擇與合同制并存的局面,在法律框架內依照市場規則和勞動標準力求勞動關系雙方權利合法、行為合規的理念,逐漸成為社會共識。
“勞動法確立了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為建立統一、公平的勞動力市場提供了基本原則和法制規則,為生產要素在價值規律作用下,按照市場規則自由流動打開了通行的閘門。同時,為公有制企業改變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用工方式在法律制度上提供了依據。”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王勝俊對勞動法為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勞動關系市場化的重大貢獻給予高度評價。
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