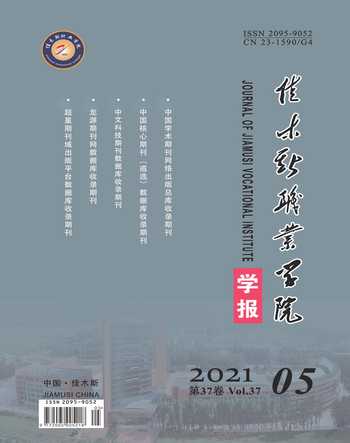鄉村振興背景下宅基地“三權分置”的困境以及對策研究
朱凡雨
摘? 要: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遷移,所以其使用的宅基地多被閑置。同時現有法律也限制宅基地的市場化流轉,造成資源配置的效率低下與農民權益性收益的缺失[1]。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了宅基地“三權分置”,為宅基地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我國對于“三權分置”的權利構造存在爭議,“資格權”“使用權”的定義不明確,相關法律規定存在沖突,易造成適用的疑難。因此,通過明確“資格權”法律定位,設置用益物權性質的“使用權”,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方能較穩妥地促進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完成。
關鍵詞:宅基地使用權;資格權;使用權
中圖分類號:D92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9052(2021)05-00-03
鄉村發展是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一環,鄉村振興政策提出宅基地“三權分置”體現了我國對盤活鄉村經濟的重視。但是,我國目前對于“三權分置”有著不同理解,要想推進“三權分置”就要明晰其權利構造,結合一些地方試點經驗,探索“資格權”與“使用權”的實施路徑,明晰法律規定,既讓農民獲得保障,同時也開放農村市場,繁榮農村經濟。
一、宅基地制度——從“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的現實需求
(一)兩權分離實踐困境
“兩權分離”制度是指宅基地使用權歸農戶和所有權歸集體,這一概念自20世紀60年代首次提出并延續至今。通過“兩權分離”,農民對于宅基地的長期使用得到了保障,但是也限制了宅基地的靈活流轉[2]。隨著時代的發展,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宅基地被大量空置,“兩權分離”的實踐面臨著現實困境。
第一,宅基地的限制流轉不利于資源有效利用。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進城打工,房屋的空置率很高,但是“兩權分離”的宅基地政策,具有很強的成員權性質,宅基地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之間流轉,身份屬性被強化。這種流轉方式阻礙了第三方資本進入,極大地限制了宅基地資源的有效利用。
第二,宅基地無法抵押,不利于農村農業長期穩定發展。我國實行“房地一體”主義,且法律也禁止宅基地使用權的抵押,這就導致農戶是享有社會資源較為缺乏的群體,無法通過宅基地房屋抵押這種融資渠道獲取資金,既不利于農戶擴大生產或發展副業,也不利于提高農戶面對重大疾病、自然災害等突發事件的抗風險能力,對農村農業的長期穩定發展造成了一定阻力。
(二)三權分置的法律內涵
宅基地制度“兩權分離”的模式已經不適應時代發展,于是在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了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的實施路徑[3]。探索出一條“所有權”歸集體、“資格權”歸農戶、“使用權”歸投資人的“三權分置”道路,目的是盤活農村的宅基地市場,既保留宅基地社會保障作用,同時也強化宅基地的財產屬性。“三權分置”創設了“資格權”,既讓宅基地繼續發揮其保障性的作用,也讓第三人沒有身份限制的利用宅基地。農戶也可以將房屋抵押,給予農民充分自主性,對于盤活閑置的農村房屋、增加農村的經濟活性都有價值。
二、宅基地“三權分置”法律的困境
(一)“資格權”的法律規定模糊
“資格權”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在以往法律規定中幾乎沒有提及,在學界也存在很大爭議,主要分為成員權說和宅基地使用權說。成員權說,即將“資格權”從宅基地使用權中抽離,使其只具有身份性;宅基地使用權說則是將“資格權”直接定義為現有的“宅基地使用權”。
第一,成員權說。成員權說將“資格權”直接認定為身份性的權利,將流轉權利讓渡出去,看到了目前宅基地流轉的必要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宅基地更高效的流轉。但是成員權說在農民權利的保障上存在不足,農戶所謂的“資格權”極易虛有化。在實踐中如江西省余江縣的農戶退出宅基地模式,該模式下農戶若自愿放棄宅基地使用權,集體組織便重新分配收回的土地,按照規劃調整為建設用地或復墾為農用地。農戶如果將宅基地使用權轉讓,就只剩下成員權,很容易出現集體侵占農民權利的現象,這也與“三權分置”政策的社會保障功能相背離。另外,我國法律對于成員權的定義并不清晰,與宅基地亦無關聯,存在法律銜接的問題。
第二,宅基地使用權說。宅基地使用權說中“三權分置”中的“資格權”也就是現行法律規定的“宅基地使用權”,它同時具備財產屬性和身份屬性。農戶在擁有“資格權”的前提下,在宅基地上設立可以用于流轉的“使用權”,這個“使用權”可以進入市場流轉。但是,宅基地使用權說在協調農戶的權利以及市場化流轉時存在疑難,投資人的“使用權”能否獲得有效保障,需要進一步明確。成員權說與宅基地使用權說各有側重,成員權說更注重于宅基地的市場化需求,宅基地使用權說更側重農戶權利的保障。
(二)投資人使用權的定位不明確
宅基地“三權分置”創設的目的是讓投資人進入鄉村市場,使其更具活性。對于投資人而言,最關注的就是自身所有享有的權利,如果自身權利得不到保障將會很大程度影響其積極性。目前針對投資人的權利法律未有規定,投資人使用權的性質也存在爭議,是定義為債權還是物權,還需要法律進一步明確。
(三)宅基地制度的法律規定存在沖突
我國涉及宅基地的法律規定不多,散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4],并不能很好地保障農村宅基地制度的正常運行。民法典與土地管理法也存在銜接上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363條規定宅基地使用權轉讓,適用土地管理的法律有關規定。但是土地管理法中并未對宅基地的流轉作出規定。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362條規定,宅基地使用權人只是占有和使用,但是宅基地使用權屬于用益物權下的權利[4],而用益物權的權能是占有使用和收益。因此宅基地使用權與用益物權的規定有出入。
三、宅基地“三權分置”的困境破解
(一)明確“資格權”的法律定位
“資格權”的法律定位是宅基地“三權分置”的重點和難點,目前兩種學說各有利弊。筆者認為采用宅基地使用權說,將“資格權”定義為現行的“宅基地使用權”,同時針對投資人設置用益物權性質的“使用權”,既可以保障農戶的權利,同時也能減輕宅基地使用權說對于宅基地流轉的限制。宅基地使用權說可以保留使用多年的宅基地使用權的定義[4],有利于政策的實施,降低政策變動的成本。同時,也有利于農地權利體系的統一,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中將土地承包權分為土地承包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承包人可以流轉土地經營權、由他人經營這一規定相協調。
此外,還要明確宅基地的“資格權”取得、登記和退出機制。明確宅基地“資格權”的取得有助于劃分宅基地的范圍,同時也有助于宅基地流轉。目前對于宅基地的取得方式僅規定了申請,還可以加入法定方式,滿足既定的條件就可以獲得宅基地的“資格權”。宅基地的登記制度也值得關注,要推進電子化登記制度的發展,明晰權利屬性。明確宅基地“資格權”的有償退出機制,使得農戶可順利退出,同時也獲得一些保障。比如,安徽省六安市規定對于農戶放棄“資格權”進行一定補貼,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在城市買房的壓力,平羅縣的試點還可以用“資格權”換取養老服務。使用宅基地有償退出機制,可以實現雙贏的局面。
(二)為投資人設置用益物權性質的使用權
“資格權”采取宅基地使用權說可以保障農戶的利益,同時為了保障投資人的利益,將“使用權”定義為用益物權可以更好地與“資格權”相協調。
在實踐中,有些試點地方將“使用權”的性質認定為債權,比如,云南大理的農戶出租農房模式,承租人的身份不受限制,集體以外的第三人可作為承租人,農戶讓渡宅基地約定年限內的占有、使用權。但將其簡單的定義為債權是存在一些弊端的。因為債權是相對權,對第三人的保護性弱,一旦權利受到侵犯難以獲得物權性的保障,容易導致第三人缺少安全感和投資積極性。同時,租賃權缺少登記,缺乏公示公信力,如果設立多個租賃權合同,將造成權利的復雜化,引發一些不必要的糾紛,增加風險。另外,債權的性質讓其不能作為抵押權的標的,也違背了“三權分置”制度設立的初衷。而將“使用權”定義為一種用益物權,第三人有著物權的保障作用,可以進行使用、獲利增加其積極性。農戶可以繼續享用宅基地使用權,宅基地制度也可以繼續發揮其社會保障的作用。
第一,理論層面上,物權體系可以與用益物權性質的“使用權”相協調。首先,在“資格權”這個用益物權之上再設立一個用益物權,不違背一物一權的原則。同時,隨著社會交易的多樣性,對用益物權權利需求也日益復雜化。民法典也新增加了居住權這種用益物權來滿足不同人的居住需求。其次,我國物權體系也可以與“使用權”相協調,土地承包法將土地承包權分為土地承包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對于承包人而言選擇范圍更加廣泛。承包人可以選擇自己經營,也可以選擇流轉其土地經營權。此外,德國也有在地上設立兩個用益物權的立法經驗,我國可以借鑒。
第二,技術層面上,電子登記技術的發展可以容納多種用益物權。我國《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規定,登記原則上采取電子形式,輔以紙質。這一規定表明如果有條件就應當采取電子登記的形式。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大數據的應用可以實現在一物之上設立多種層次的用益物權,采用電子方式進行公示簡潔明了,既有公示對抗第三人的物權效力,也不會造成權利混雜不清的局面。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新增的用益物權——居住權,也是債權向物權的轉變,將只規定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的居住權,這種債權性質的權利將轉化為物權性質,因此“使用權”定義物權不存在立法上的疑難。
(三)增設專門宅基地管理法規
關于宅基地的法律規定,各個法律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明確宅基地可以用于流轉,宅基地使用權人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同時,出臺“宅基地管理條例”,使得宅基地流轉有法可依,解決不同法律規定之間的沖突現象,規范主體行為使得農戶享有身份權以及財產權,投資人享有用益物權性質的使用權,從而盤活農村的宅基地市場,解決目前宅基地非法流轉的現象。
四、結語
目前法律規定的農村宅基地“兩權分離”模式是滯后于社會發展的,“三權分置”改革迫在眉睫。其重點就是理清“資格權”和“使用權”的權利屬性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會增加農村市場的活性,有利于推動我國農村現代化改革。
參考文獻:
[1]梁穎.銻污染土壤固化-穩定化的影響因素[J].化工環保,2020,41(1):61-65.
[2]王志鋒,徐曉明,戰昶威.我國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評估——基于義烏市與宜城市對比研究的視角[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1):33-42.
[3]胡振華,承露.中國現階段農村宅基地流轉探究[J].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2(6):28-35.
[4]張賀.論我國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法律制度的完善[D].吉首大學碩士論文,2020.
(責任編輯:董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