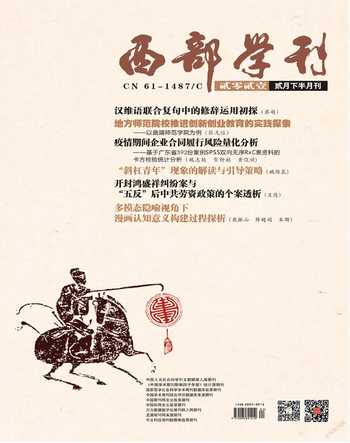漢維語聯合復句中的修辭運用初探
摘要:聯合復句為修辭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是組織話語、完成交際任務的重要手段,了解并掌握這些句式的修辭功能和適用語境,對于漢維語學習者正確有效地組織話語、提高修辭效果是十分重要的。將漢維語聯合復句與側重于形式的修辭方式加以聯系和對比,如將漢維聯合復句與對偶、排比、頂真、回文、重復、層遞等進行對比,發現漢維語聯合復句與修辭均具有極為密切的關系,修辭格具有不少相似之處,可以看出漢維兩個民族在長期地相互學習交流中已經形成了十分親密的關系,在彼此的思維、認知上也有許多共性。通過探索兩種語言聯合復句中修辭格的異同以歸納其中的規律。
關鍵詞:漢語;維吾爾語;聯合復句;修辭
中圖分類號:H2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916(2021)04-0005-04
聯合復句是指各個分句間沒有主次之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句平等地聯合在一起,聯合復句的聯合項(分句)無論多少都是同一層次的[1]。修辭活動和修辭手段及其成果(修辭成例)統稱為修辭現象;從各種修辭現象中總結出來的普遍規律便是修辭規律;研究修辭規律的科學就叫修辭學[2]。聯合復句句式不同,功能不一,可以組建不同的話語,塑造不同的風格,完成不同的交際任務。所以,了解它們的結構,掌握它們的功能,熟悉它們的用法以及它們需要的語境,對話語組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不論漢語還是維吾爾語,聯合復句都既有語法方面的特點,也有修辭方面的作用,將其語法上的特點和修辭上的作用加以對照研究,對于我們學習和運用語言,都有一定的幫助,且漢維語的修辭對比作為漢維對比語言學的一部分與其他對比研究內容相比顯得較為不發達,目前還未有將漢維語聯合復句中存在的修辭現象進行對比研究的成果,因此對其加以對比,進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漢維聯合復句與對偶
對偶是用結構相似或相同、字數或音節數相等、語義相關、兩兩相對的一對語句,表達兩個相反、相似或相關意思的修辭方式,即組成聯合復句的兩個分句的字數、結構相同或相似,表達兩個相反、相似或相關的意思時,就組成對偶。跟維吾爾語中的“parallelizim”有相似之處[3]。書面的對偶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甚至更早[4]。它在詩歌、對聯中還有楹聯中占據半壁江山。在聯合復句中也存在不少對偶現象。
例1:詛咒使人振奮,贊譽使人松懈。(布萊克)
從形式上來看,“詛咒”對應“贊譽”、“振奮”對應“松懈”;從語義上來看,詞語的意思也都是一一相反的。這個復句用維吾爾語可表達為:
tilla? ad?mni rohlanduridu,maχta? ad?mni bo?a?turidu.
同樣,在這個維吾爾語復句中,“tilla? ”對應“maχta? ”、
“rohlanduridu”對應“bo?a?turidu”,上下兩句,不但語法結構相同,詞語的詞性也相同,且其意義相互對立。
例2:虛榮的人注視著自己的名字,光榮的人注視著祖國的事業。(何塞·馬蒂)
在這個復句中,“虛榮”對應“光榮”、“自己”對應“祖國”、“名字”對應“事業”;相同的詞性,相同的音節數,加上恰好相反的意義。將這個復句使用維吾爾語表達出來時,則變為:
abrojp?r?sl?r ?z ismi?a,??r?plikl?r w?t?nni? i?liri?a k?z tikm?kt?.
此句前后表達的意義依然相反,但此時原本聯合復句的形式已消失,原因在于維吾爾語的復句中,當前后分句的謂語相同時,往往會省略前一個謂語,只在句末出現該謂語;且“abrojp?r?sl?r”與“??r?plikl?r”雖然都是由派生法+復數詞尾構成的表達“一類人”概念的詞,但究其根本附加的是“p?r?s”“lik”兩個不同的詞綴,導致在聽覺上兩者也產生了較為不和諧的律感。
以上兩例表明,漢語聯合復句中的對偶顯示兩句話的字數或音節數相等,句法結構相同或相似,對應的詞性多相同或相近,意思也是相近或相關的。聯合復句中成功的對偶,不但具有聽覺和視覺上的整齊美,而且顯得言簡意賅。與維吾爾語相比,漢語在對偶這方面更具優勢,原因其一,漢語多以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為主,而且每個音節都有元音,沒有復輔音;而維吾爾語一個詞的音節數是不定的、存在復輔音;其二,漢語的每個字都是一個音節,且呈方塊字,視覺上更為工整;其三,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可以形成抑揚頓挫的韻律,但維吾爾語沒有聲調,只有詞重音或語調,不易形成十分明顯的韻律對仗。綜合這三點,導致了漢語聯合復句中的對偶同時可以兼有視覺上的工整美和聽覺上的韻律美,而維吾爾語則不易同時滿足這兩點。
但與此同時,以上這有限的兩個維吾爾語復句都是以漢語為原文而翻譯表達出來的形式,事實上在許多維吾爾族詩人、作家的作品中,含有對偶的聯合復句也是大量存在的。
例3:在艾比布拉·熱介普所著《春天的歌》中:
kyjliri?din tapalmisam rohimni,hesli?ni? qatqini ?u muz bolup.ymidlirim ?aχlimisa q?lbi?d?,baharimiz k?tkini ?u kyz bolup.
很明顯,上下兩個分句非常具有對偶的特點,它們不僅在音節數上完全相等,而且其后附加的人稱詞尾與格詞尾也是相互一一對應的,甚至“qatqini”與“k?tkini”出現了“q”對“k”、“a”對“?”這樣根據舌位前后的不同而產生的對偶修辭效果,同時具有視覺美與聽覺美。
二、漢維聯合復句與排比
排比不論在漢語中還是維吾爾語中都是一種常見的重要修辭方式。它要求組成它的幾個分句句式相同或相似,語氣一致,內容密切相關,分句需在三個或三個以上,并且有共同的重復的詞語。當復句的幾層意思敘述的分句出現排比的特點時,從修辭的角度看,它就是排比。維吾爾語中的“janda? turu?”[3]或“t??da? ”與這種辭格互為對應。聯合復句中存在大量的排比句。
例4: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millij,ilmij,ammiwi m?d?nij?t χ?lq ammisini? ?ahangirlikk?,feodalizm?a qar?i m?d?nijiti,je?i demokratik m?d?nij?ti,?u?χua mill?tlirini? je?i m?d?nijiti.
在這個漢語例句中分句用三個“就是……的文化”連用起來,三個句子層次逐漸深入,語義上有明顯的層次性,構成排比;而在維吾爾語的這句話中,無論判斷系動詞“就是”是否隱現,從句子層次上來看也是標準的排比,前有不同限定語的三個“m?d?nijiti”增強了話語的氣勢,充分、強烈地抒發了情感。當然,如果僅僅想把這句話的意思表達出來,不論是在漢語還是維吾爾語中,完全可以只出現一次“文化”(m?d?nijiti),此時復句就會變成: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millij,ilmij,ammiwi m?d?nij?t χ?lq ammisini? ?ahangirlikk?,feodalizm?a qar?i bol?an,je?i demokratik,?u?χua mill?tlirini? je?i m?d?nijiti.
很明顯,變化后的句子雖然在結構、語義上意義沒有發生什么改變,但卻失去了其原本的內在氣勢,從中也很難體會話語的情感邏輯脈絡,即此句失去了它原有的修辭表達效果,讀之乏味,經對比我們可以體會到排比的功能強大。
例5:虛心向群眾學習,真心對群眾負責,熱心為群眾服務,誠心接受群眾監督。(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這是一個并列復句,句中連續出現四次“……群眾……”的形式,且體現出一種濃烈的政治理念,同時讓人真切感受得到當政者的政治熱情和其對人民群眾的重視,整句氣勢雄渾。其維吾爾語表達形式如下:
ammidin k?mt?rlik bil?n ?ginip,ammi?a ?in dilidin m?sul bolup,ammi?a qiz?in mulazim?t qilip,ammini? nazaritini s?mimij qobul qili?i ker?k
這時原句的政論文體依舊不發生改變,以“amma…p/?i”+“ker?k”的句式,也將語義情感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出來,使復句的節奏感加強,條理性更好了。
可以發現,例4中的排比成分較長,而且情感不是十分強烈,所以這里排比的氣勢比較弱,節奏比較柔緩,例5中的排比成分較短,情感濃烈,句中四個主謂結構各有五個音節,帶有節奏急促、語勢有力的修辭效果。由此可知,在排比句中語勢的強弱,往往取決于句子或句子成分的長短,而且會受制于話語信息中情感成分和語氣的強弱,這一點在漢語和維吾爾語中都是相同的。
三、漢維聯合復句與頂真
“頂真”在修辭學中也叫“聯珠”“蟬聯”,它是前句末尾的詞語,做后句開頭的詞語,使鄰句首尾遞接的一種修辭方式。維吾爾語中尚未確定“頂真”辭格的術語。“頂真”這種修辭方式多用于聯合復句中的承接復句,運用“頂真”可使語言氣勢連貫,音響流美,感情綿密,說理透徹,利于打開讀者思路。
例6: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查,和對于各種偵查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前三句話首尾相接、前后承繼,以上一句的結尾作為下一句的開頭。此句使用維吾爾語可表達為:
qomandanni? to?ra orunla?turu?i to?ra iradidin,to?ra iradisi to?ra h?kymdin,to?ra h?kymi ?trapliq w? z?ryr bol?an t?htittin kelidu,h?r χil t?hqiql?? materijallirini? ba?lini?i?a bol?an ojlini?tin kelidu.
可以發現,與漢語一樣,維吾爾語中也存在頂真的修辭格,且其表達效果與漢語很相似,句中“to?ra irad?”與“to?ra h?kym”分別首尾相接,環環緊扣,耐人尋味。
例7:胡楊生下來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下去千年不朽。
“死”接“倒”,“倒”接“朽”;頂真的存在使這個復句更加具有藝術性,用維吾爾語可表達為:
to?raq tu?ulup mi? jil?i?? ?lm?jdu,?lg?ndin kejin mi? jil?i?? jiqilmajdu,jiqilsa mi? jil?i?? ?lm?jdu.
在維吾爾語聯合復句中,頂真既可以表形又可以表意,也十分適合用于闡述事物之間的邏輯關系。頂真能夠使聯合復句分句之間首尾蟬聯,既可以揭示事物之間的辯證關系,又可以使語氣連貫,語音和諧流暢,這一特點在漢語和維吾爾語中都是相同的。這種辭格在實際使用時應注意,頂真主要用于表達多種事物或現象之間的連鎖關系,運用的時候不能一味地追求形式,應切實考慮事物間的邏輯聯系。
四、漢維聯合復句與回文
與頂真有些相似,還有一種叫做“回文”也叫“回環”的辭格,它是用循環往復的語言形式,表現兩種事物或兩種情況相互關系的修辭方式。維吾爾語里與漢語“回環”相對應的辭格是“ajlanma”[5]。“回環”的修辭方式,多借并列復句表現出來。它能使語言顯得精確凝練,內容好懂易記。
例8:他們忘卻了紀念,紀念也忘卻了他們。(魯迅《頭發的故事》)
在這個復句中,以“他們”和“紀念”這兩個詞為單位,顛倒順序,構成了具有連貫意義的話語,后一句正好是前一句的倒置,兩句話正念反念都成句,趣味盎然,具有一定的藝術韻味。該句可用維吾爾語表達為:
ular χatirini untup qaldi,χatirimu ularni untup k?tti.
可以看出,“ular”與“χatir?”也是相互顛倒的,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回環的定義,可是,這兩個詞的音節數是不同的,導致在聽覺上缺失一定的韻律。
例9: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毛澤東《實踐論》)
此句出現的是“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這兩個詞組的語序互換,恰當地體現出辯證唯物論的本質。其維吾爾語表達如下:
?qlij bili? hessij bili?k?,hessij bili?ni ?qlij bili?k? t?r?qqij qilduru?qa to?ra kelidu,mana bu dialektik materijalizmliq bili? n?z?rij?sidur.
此時,“?qlij bili?”“hessij bili?”音節數相等,其語義也剛好相反,分句間回環往復,表達出了兩種事物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邏輯關系。
回環重在話語形式的倒反,用得巧妙,可使話語新穎有趣,在使用時應注意內容與形式相互和諧。漢維語的“回環”修辭,都能恰當、有效地反映事物之間的辯證關系,具有實際交際價值。漢語和維吾爾語對回環辭格的理解與運用,在根本語義上都是不謀而合的,且外在的表現形式也十分相似,運用在聯合復句中的回環辭格,不論漢維語,都具有視覺上的工整美和聽覺上的和諧美,修辭效果十分顯著。
五、漢維聯合復句與重復
重復也是修辭學里的一種重要修辭方式。重復的主要特點是:為了強調某一點意義,表現對事物的強烈而深厚的感情,表示對事物的某種迫切的要求和愿望,而在語言上讓同一詞語反復出現。這種形式只有在復句中才能得以表現,運用得好,就可以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起強烈的共鳴。維吾爾語的“t?krarla?”其形式、作用與漢語的基本相同[3]。在漢語聯合復句中,并列復句時常出現重復的修辭手法,有時選擇復句中也會出現這種修辭。
例10: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紀念劉和珍君》)
此句中將“敢于”二字重復了兩次,增強了這個聯合復句的韻律,而且逐漸深化語義、步步強化表達,留給讀者深刻印象,達到了作者抒發強烈情感、表達深刻思想的目的。這個復句使用維吾爾語可表達為:
h?qiq?t?n batur,e?ini?liq hajatqa jyzlini?k? ?yr?t qilalajdu,?ipildap eqiwatqan qan?a to?ra qara?qa ?yr?t qilalajdu.
顯然,在維吾爾語的表達中,不論在形式還是語義上,其修辭效果都與漢語相同,這句將謂語部分“?yr?t qilalajdu”重復了兩次,既強調了語義,又突出了重點。
例11: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此句中“是……而不是……”的句式重復出現了兩次,在分句間的銜接與層次的區分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個復句使用維吾爾語可表達為:
kompartij? ?zaliri χ?lq h?rikitid?,ammini? dosti bolu?i,χ?lqni? ba?liqi bolmasliqi,erinm?j ?gitidi?an oqutqu?i bolu?i,bijurokrat sijas?twaz bolmasliqi ker?k.
此時,“…bolu?i…bolmasliqi”的句式也重復兩次,像這樣在一個復句中重復出現同一項語言形式,使得各部分在主題上得到了極高統一,將前后分句有機地聯系在了一起,更能體現出分句間的銜接與連貫。
漢維語聯合復句中運用重復,有時不僅僅是為了韻律的和諧,更重要的是強化需要表達的語義,而且重復多用來抒發十分強烈的情感,所以在使用重復的辭格時,一定要把握好感情的強度,不能違反聯合復句內在存在的情感邏輯,這樣才能發揮較好的修辭效果。
六、漢維聯合復句與層遞
將語意排成由淺到深,由低到高,從小到大,從輕到重,或者反過來由深到淺,由高到低,從大到小,從重到輕,這種節節前進,或節節退縮的方法,在修辭上人們稱為“層遞”。現維吾爾語中缺失對“層遞”的規范術語。聯合復句中的并列復句與承接復句中常用“層遞”。
例12:這在中國是如此,在整個東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這個并列復句的分句由“中國”向“東方”,再向“世界”,節節前進,逐層擴大范圍,非常有力地說明了革命勢力勢不可擋。該句用維吾爾語可表達為:
bu ?u?goda ?undaq,pytkyl ??rqtimu ?undaq,dunjadimu ?undaq.
同樣,由“?u?go”到“??rq”,最后到“dunja”,兩個民族在這三個詞語所對應的范圍大小上的認識是完全一樣的,范圍由小到大,層級步步擴大,可感受到主題的逐步升華。
例13: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后,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這是一個承接復句,用了三個分句把“冒險主義”“保守主義”“逃跑主義”依次排列起來,加以敘述,使我們深刻地了解到那個所謂反“游擊主義”的空氣,從理論到實踐都是錯誤的,用的是一步步向后退縮的論述方法。此句用維吾爾語表達為:
birin?i basqu? h?rbij t?w?kkyl?ilik boldi,ikkin?i basqu? h?rbij mut??ssiplikk? ?tti,aχirqi basqu?,y?in?i basqu? qa?qunluqqa ajlandi.
從語義上來看,“h?rbij t?w?kkyl?ilik”“h?rbij mut?? ssiplik”“qa?qunluq”程度由淺到深,語氣由輕到重,十分具有邏輯順承性,是典型的層遞辭格。
經對比,漢語與維吾爾語中都存在層遞這種修辭現象,但維吾爾語中急需給“層遞”規范其專屬術語,這是一種功能較為強大的辭格,可使讀者層層跟隨語句,因而內容引人入勝。“層遞”在聯合復句中,如果用來敘事,可使復句條理清洗,如果用來說理,可使復句的說服力增強,如果用來抒情,也可加強整個聯合復句的感染效果。
結語
聯合復句為修辭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是組織話語、完成交際任務的重要手段,了解并掌握這些句式的修辭功能和適用語境,對于漢維語學習者正確有效地組織話語、提高修辭效果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主要從形式化的修辭方法出發,指出漢維語聯合復句與修辭都具有極為密切的關系,從漢維聯合復句中側于形式的修辭格具有不少相似之處,也可以看出漢維兩個民族在長期地相互學習交流中已經形成了十分親密的關系,在其思維、認知上也有許多共性,也發現一直以來維吾爾語中的確存在豐富的修辭現象,但仍沒有受到學界高度重視,維吾爾語中還有部分辭格的術語面臨著存疑、缺失的情況。因所學尚淺,分析闡述不夠全面深入,希望本文引起各位學者、老師的興趣,進一步探討,以期拓寬漢維修辭方面的對比研究范圍。
參考文獻:
[1]張斌,陳昌來.現代漢語句子[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273.
[2]劉煥輝.修辭學綱要[M].修訂本.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4.
[3]帕提曼·塔西.漢維語常用修辭格對比研究[D].伊寧:伊犁師范大學,2019.
[4]陳汝東.修辭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62.
[5]劉珉.論漢維語的回環修辭格[J].語言與翻譯,1992(4).
作者簡介:蔡萌(1998—),女,漢族,新疆喀什人,單位為新疆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維吾爾語)。
(責任編輯: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