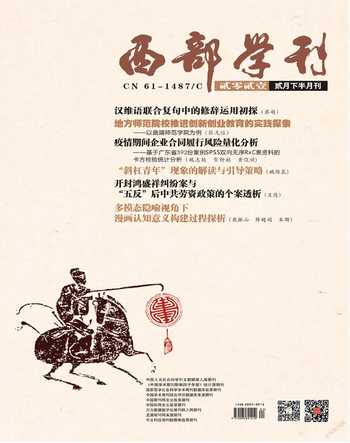營商環境法治化視角下環境行政執法的現狀與對策
摘要:環境行政執法的現狀存在明嚴實松、政企關系緊張的問題,其主要原因在于監管任務繁重,自由裁量難以把握,環保督察高壓以及中小企業自身抗風險能力較弱。因此,要解決環境行政執法目前存在的問題,對策是:執法頻次:放管服改革下的智慧執法;自由裁量: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寬嚴相濟;監督問責:完善責任追究機制;市場主體:提高法律意識。
關鍵詞:營商環境;法治化;環境行政執法
中圖分類號:D922.1;D922.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916(2021)04-0102-03
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的全球營商便利度與西班牙并列全球第30位,在實施監管改革后,中國成為全球優化營商環境提升幅度最大的十大經濟體之一。
營商環境指企業等市場主體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各種影響條件和因素,主要包括市場準入、勞動力雇傭、生產要素保障、產權保護、融資、稅收、合同履行以及糾紛解決機制等,貫穿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的整個過程。營商環境優劣決定了地區經濟發達程度,是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營商環境法治化是優化營商環境的一大原則,完善法治保障是營造良好營商環境、激發市場經濟活力的關鍵。
2019年,國務院發布《優化營商環境條例》,該條例主要在市場主體保護、政府服務、監管執法和法治保障等方面作出規定。近年來,國務院各部門綜合考慮行業發展需要,相繼出臺落實優化營商環境政策的部門規章;地方各級政府也根據職權相應頒布了相關條例和有關辦法,共同形成了當前立體化的營商環境法治建設格局。
營商環境法治化從制度層面,對政府積極履行管理和服務職能、嚴格依法進行行政執法提出了要求,而“史上最嚴環保法”下的環境行政執法問題,一直是政府管理和法治建設的痛點和難點,因此有必要以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建立和諧的政商關系、完善法治建設為目的,分析環境行政執法存在的問題和成因,并提出對策。
一、環境行政執法的現狀
(一)行政執法名嚴實松
《環境保護法》自出臺之初便確立了污染者負擔原則,按照經濟學的“外部性理論”,將污染者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同時設置多種法律責任,試圖提高企業違法行為的成本,但與企業獲得的利益相比仍顯得微不足道,從而導致企業環境違法行為依舊泛濫。為了適應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新道路,摒棄對自然資源掠奪式的開發,2014年修訂的《環境保護法》新增按日連續處罰、限制生產、責令停業以及行政拘留等行政執法措施,起到了震懾生產經營者的作用,預防環境污染行為的發生。
然而,在實際的環境行政執法過程中,執法主體對裁量條件和幅度有較大的選擇空間。一線調查人員具有信息優勢,可以有選擇地決定調查取證的內容,難免存在折扣執法的情況。更有甚者,個別執法人員將法律法規作為牟利工具,對當事人進行選擇性適用,或者區別對待不同當事人。這種不作為、亂作為現象目前在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西部地區依然存在,省級生態環境部門對一些高耗能、高污染小作坊式企業未進行嚴格管制,加上地方政府基于人情利益等因素考量對其視若無睹,擾亂了正規生產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該行業處于集中度比較低的無序競爭狀態。如此復雜的執法環境不僅不利于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也不利于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有效落實,更無法發揮行政法本身的“控權”功能。
(二)政企關系日趨緊張
環境監管過程中,環境執法主體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企業守法需要投入成本,違法要接受行政處罰。一方面,生態環境部門面對嚴格的法律規定以及行政監察,需要依職責對企業進行日常監督管理,并對違反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的經營者嚴格執法。另一方面,對于經營者來說,在經營前,環保設施若建設不到位,則很難通過生態環境部門驗收繼而無法投入生產;在生產過程中,污染物的環保處理和環保設施的運行維護無疑是一筆長期的生產成本,自身產品結構單一、嚴重依賴自然資源且污染高、附加值低、生存周期短的中小企業自然無法負擔。
顯然,如何在法治框架下協調好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成為關鍵問題。地方政府缺乏對當地營商環境深刻認識,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規時,無法滿足市場主體的需求。加之政府政策宣傳、法治宣傳力度不夠,經營者對營商環境政策的解讀存在困難,造成了政企信息不對稱。與將法律當作牟利工具選擇性執法相反,生態環境執法人員對企業一刀切式執法,不尊重市場主體對執法行為提出異議的權利等現象時有出現。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建設,不止是政府部門的責任,也需要政府部門和市場主體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機制,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激發市場經濟活力。
二、環境行政執法的問題
(一)事中事后監管檢查繁重
隨著放管服①改革向縱深推進,為優化營商環境,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對于納入管理名錄的生態環境影響小、風險可控的行業及建設項目,施行環評豁免和告知承諾制的行政審批方式。告知承諾制是指,在申請環境影響評價文件審批時,行政機關告知申請的依據、條件和程序,環評編制單位和建設單位書面承諾已符合相關標準和要求,并愿意承擔不實承諾的法律責任,環評審批機關可不經評估直接作出審批決定。上海、廣東、安徽、淄博、昆明等省市的生態環境部門已率先出臺了建設項目環評告知承諾制審批改革試點實施方案。事前審批的簡化勢必需要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如此一來,生態環境執法部門需要根據環評審批機關移交的報批材料,檢查建設單位承諾內容的落實情況,加大了地方環境執法部門的工作量。
此外,地方環境執法部門要進行日常檢查、污染源在線監控,也要參與“雙隨機、一公開”抽查,接受中央及上級生態環境部門環保督察,調查群眾舉報和反映的線索。多項執法內容、多種執法形式和多級執法,對于本身人手不足的基層來說,任務較為繁重,也給企業的日常生產活動帶來了不便和困擾。
(二)環境處罰的自由裁量困境
為解決環境行政執法上一直存在的自由裁量問題,生態環境部最新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適用環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指導意見》(環執法〔2019〕42號)。該意見要求各地區健全貫穿生態環境執法全程的相關配套制度,以科學合理、公正公開的分工與監督來保障自由裁量權的合理規范適用,綜合考慮多種因素,結合地區法規和規章,細化、量化裁量規則和基準,并通過函數運算得出處罰額度。
盡管如此,行政處罰的自由裁量仍有不足。首先,與法規、規章等相比,效力位階較高的環境保護法律,如《水污染防治法》等,本身規定的處罰幅度較大,任何細化都屬于法定范圍內,自由裁量始終留有一定適用幅度。其次,基層執法人員學習和應用法律法規的能力參差不齊,在細化后的范圍內作出處罰,也無法避免適用裁量細則時產生偏差,出現同一地區同一問題不同處罰的情況,影響當地企業經營。其次,不同地區的執法水平、信息化水平有所差異。往往經濟不發達、生態環境脆弱的西部地區,需要制定細致、嚴格的規則,更加考驗執法人員水平,而西部地區信息化水平也較為落后,不便于當地的統一適用。
(三)環保督察制度下的整改壓力
中央環保督察制度自2016年建立以來,兩年內完成了全國第一輪省級覆蓋式督察,彰顯中央對環境治理的決心。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規定》,為環保督察的持續穩定開展提供制度基礎。中央辦公廳、中央組織部、司法部、生態環境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等多個部門,組成專門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領導小組,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負責具體任務,對省市黨政及有關部門、國務院生態環境相關部門以及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大的央企等進行例行督察、專項督查,防止地方違背上位法立法、軟性執法、縱容違法,并通過“回頭看”驗收整改情況。
“以‘督政’促進地方環境執法,是實現最嚴格環境保護制度的重要體現”[1]。誠然,面對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的壓力,地方各級為快速整改到位,采用“一刀切”式環境執法,對一些行業或區域內的企業整體關停,不利于對市場主體的保護,與營商環境法治化理念相悖。
(四)中小企業自身基礎實力羸弱
中小企業自身抗風險能力弱。高污染行業的中小企業,往往產品附加值較低,同質化嚴重,發展受限,從而導致行業陷入價格競爭,生存空間進一步受到擠壓。“就環境行為而言,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如果違法收益大于守法收益,那么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導向的企業必然會選擇違法,并采取各種手段隱藏違法行為、躲避違法檢查和處罰。”[2]
環保設施建設和污染物排放標準是企業合法經營的前提,而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中小企業,重利益而輕環保,守法意識和社會責任淡薄,違法才有利可圖,購置環保設備,則增加企業運營成本,入不敷出。這類市場主體往往在存亡間搖擺存活,若經過合理整改,企業可能會進入良性發展,若獲處罰,動輒數十萬,企業一擊致命。環境執法倒逼營商環境優化,考驗著基層行政執法能力和水平。
三、環境行政執法的出路
(一)執法頻次:放管服改革下的智慧執法
在新時代的營商環境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應盡量減少對市場活動的干擾,加強和規范事中事后監管,提供公共服務,激發市場活力。
放管服改革要求“寬準入嚴監管”,監管也是政府政務水平的重要體現。環境執法部門要履行監管職責,驗收新建企業環保措施建設、污染防治和承諾事項落實情況,合格后可推遲或暫緩對新建企業的檢查。另外,合理安排日常檢查和“雙隨機、一公開”抽查等執法頻次,避免重復檢查和多頭執法。根據企業環境影響情況設定執法周期,以免增加市場主體負擔。強化污染源在線監控,緩解倒金字塔形的基層執法人員人手不足的情況。建立統一的信用監管平臺,將企業嚴重污染環境的違法失信行為在平臺上公示。
(二)自由裁量: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寬嚴相濟
面對靈活的行政權時,行政相對人容易受到侵犯,因此需要法律對政府行政行為進行約束和限制,這也是營商環境法治化的要求。自由裁量幅度較大的法律,應該進一步細化,“通過法律來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并把它控制在必要的范圍之內”[3]。與此同時,各級生態環境部門要依據經濟發展狀況和環保需要,合理制定自由裁量標準,為地區內執法統一奠定基礎。生態環境執法人員要提升執法能力,以保市場主體為主要目的,在環境行政執法中,根據違法事實、過錯程度、社會危害性以及整改情況等,認真聽取市場主體的陳述申辯,依法公正地給予相應的處罰。
(三)監督問責:完善責任追究機制
在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的巡視下,地方在對提出的問題進行積極整改時,既要避免一刀切式執法影響合法經營的市場主體,也要避免執法不到位,被督察組問責。環保督察作為生態環境問責制度的主要方面,通過“黨政同責”的問責方式,督促地方黨政領導履行環境保護責任,兼具基層性、廣泛性和嚴厲性[4]。
除了環保督察,其他的監督機制也應協同發揮作用。首先,環境執法全過程都要接受社會監督,事前公開法律法規,事中表明執法身份,事后公開處罰決定,公開透明執法,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同時,根據環保垂改制度的要求,地市級生態環境部門實行以省級部門為主的雙重管理體制,依然是本級政府的組成部門,縣級生態環境部門則作為地市級生態環境部門的派出機構,這一改革既使省級生態環境部門對轄區內的環境保護問題可以一管到底,也讓生態環境部門對基層政府的監督具有了現實可操作性[5]。此外,監察委員會作為公職人員的監察機關,也有權對生態環境執法人員的執法行為進行監督。行政權的合理行使有利于和諧政商關系,合理行使權力有賴于監督環節,是營商環境法治保障的重要內容之一。
(四)市場主體:提高法律意識
市場主體作為營商環境的重要參與者以及行政相對人,其先進的法治觀念,是形成持續推進優化營商環境的合力的重要前提。“具有環境意識和環境法治觀念,會計算環境利益,尋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最佳化、最大化”[6]的“理性生態人”才是符合環境保護基本要求的市場主體。營商環境法治化建設,不僅需要政府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規,提升環境執法能力,更需要市場主體自覺守法,保護環境、敬畏自然。
一方面,生態環境部門應積極開展法治宣傳,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傳播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提升市場主體法律意識,為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提供基礎。對違法行政相對人嚴格依法執法的同時,也要對環保處理做得好的企業進行宣傳和表彰。另一方面,企業自身要提高法律意識,將守法納入經營理念,自項目建設到投產運營全程,建好環保設備,配合環保檢查,做好環保處理,積極主動學習環保法律法規,依法依規經營。
注 釋:
①放管服:就是減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簡稱。
參考文獻:
[1]石磊.基層執法糾偏的路徑探索——以環保“一刀切”為例[J].長白學刊,2020(1).
[2]何香柏.我國威懾型環境執法困境的破解——基于觀念和機制的分析[J].法商研究,2016(4).
[3]余光輝,陳亮.論我國環境執法機制的完善——從規制俘獲的視角[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0(5).
[4]張梓太,程飛鴻.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生態環境問責制度?——兼議生態環境損害賠償中地方政府的兩難困境[J].河北法學,2020(4).
[5]熊超.環保垂改對生態環境部門職責履行的變革與挑戰[J].學術論壇,2019(1).
[6]蔡守秋,吳賢靜.論生態人的要點和意義[J].現代法學,2009(4).
作者簡介:孫寒璞(1997—),女,漢族,河南登封人,單位為蘭州大學法學院,研究方向為社會保障法。
(責任編輯: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