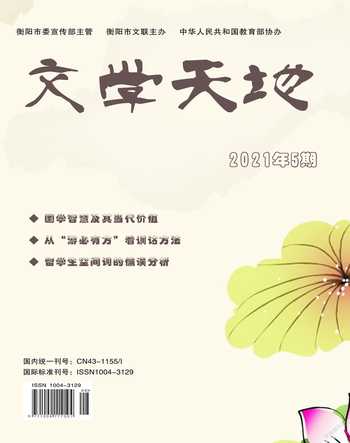麥都思與《福建方言字典》
黃自然
摘要:麥都思是19世紀中期來華的英國新教傳教士,漢語語言學家。他來華活動四十余年,先后編撰了六部字典,翻譯過四個版本的《圣經》。《福建方言字典》是麥都思于1832年出版發行的一本英漢雙語方言字典,也是新教傳教士編寫的第一本閩南語字典,成為近代來華工作或傳教人士學習閩南方言必備的普及型工具書。該字典翻譯收錄了大量漢語經典作品精華,是這一時期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參考資料,也對其后福建方言字典的編纂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傳教士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筆名尚德者 ,自號墨海老人,是英國倫敦宣道會繼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米憐(William Milne)之后又一位重要的來華宣教士。他來華活動四十余年,除先后掌握馬來語、漢語、日語、朝鮮語等語種外,還能熟練使用福建和廣東方言。麥都思一生專注于圣經漢譯,前后翻譯過四個圣經譯本。此外,他還編纂了六部字典,包括兩部官話字典,兩部方言字典,一部英日日英字典和一部中、朝、日、英字典。麥都思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圣經漢譯、語言研究、典籍翻譯、出版印刷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為中外語言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貢獻。
麥都思生于英國倫敦,父親是一家小酒店老板,1807至1812年在倫敦圣保羅主教堂學校(St. Paul's Cathedral School)學習,后為補貼家用,赴其原籍格羅切斯特(Gloucester)做學徒學習印刷技術。《麥都思行略》 記錄了他的這段經歷:“入塾讀書,頭角嶄然……。十五歲,習裝印書籍事,得值以瞻父兄。”從此他與印刷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印刷技術也對他日后的文字出版工作幫助很大。17歲時,麥都思受洗入教。
1816年,麥都思被英國倫敦會以印刷工身份派往馬六甲。1817年2月,抵達印度馬德里,在那里逗留期間,認識了一位印度官員的遺孀伊麗莎白(Elizabeth Martin)并與其喜結良緣。到達馬六甲后,麥氏主要協助米憐從事英華書院教學和印刷出版工作。他一邊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一面鉆研印刷業務,幫助米憐編輯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成為他的重要助手。1817年,他在巴達維亞 (今雅加達) 建立印刷所,成為倫敦會在南洋的主要基地。1819年,麥都思在馬六甲被按立為牧師,之后在馬六甲、檳城和巴達維亞傳教,并用雕版法和石印法先后印行30種中文書籍。
1842 年鴉片戰爭后,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并把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辟為通商口岸,原來活動于東南亞的傳教士紛紛來到香港、上海和廣州等地,進行傳教和出版活動。1843年麥都思代表倫敦會到上海,成為最早到上海的外國傳教士和倫敦會上海區的開拓者。麥氏利用負責道路、碼頭建設和管理英僑公墓之便,圈買了上海縣城北門外的大片土地(今山東路一帶),作為倫敦會的在華總部,在此建造天安堂教堂。1844年將在定海的醫院搬至其住宅旁,取名基督教醫院(今仁濟醫院),是上海第一所對華人開放的外國醫院。除了宣教工作外,他還和美魏茶、慕維廉、艾約瑟等宣教士創建了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印刷出版中文書籍。墨海書館為上海最早的現代出版社,是最先采用西式中文鉛印活字印刷術的印刷機構。墨海書館培養了一批通曉西學的學者,如王韜、李善蘭等。他們和艾約瑟、偉烈亞力等西教士撰寫、翻譯了許多介紹基督信仰、西方科技、文化的書籍。
1848年3月,麥都思與雒魏林、慕維廉擅自去青浦傳教,與船民發生沖突,被打傷。英領事借此挑起事端,激起中國近代第一件教案,史稱“青浦教案”。
1854年,麥都思當選為上海工部局首位董事。同年1月24日,麥都思在倫敦逝世。為紀念他,人們將墨海書館、天安堂和仁濟醫院一帶稱為“麥家圈”。曾經的上海公共租界有一條以其姓氏命名的麥特赫斯脫路(Medhurst Road,今泰興路)。1904年,倫敦會將位于山東路的華英書院遷至虹口兆豐路,并更名為麥倫書院(Medhurst College)。
麥都思只受過初等教育,但他勤奮好學,在語言學習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因此在語言學領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初到馬六甲,麥都思便全身心投入到中文學習中。他最初學的是官話,但發現移民馬來群島的中國人并不懂官話,于是轉而學習福建方言。他的好學給米憐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評價他“非常好學,年輕人有這樣的性格總是讓人尊敬和喜愛,并愿盡可能幫助他。他學習起中文來,堅持不懈,充滿熱情,看到的同工都認為他的中文長進飛快,不需多久就會成為傳教的好助手。”如米憐所言,麥都思的語言水平進步神速,幾年之后,他不僅能與當地居民順利溝通,還能為他們翻譯 。
麥都思編譯著作甚豐,計有中文59部,馬來文6部,英文27部。在語言學方面,麥都思編纂著譯的作品包括在雅加達傳教期間編著的《漢語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1832),在上海編著的《漢英字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 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Dictionary ,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兩卷,1842—1843)、《英漢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兩卷,1847—1848)、以及《臺灣虎尾壟語字典》(Dictionary of the Favorlany Dialect of the Formosan Language)(1842)、《書經》(Ancient China : The Shoo King ,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s: being the most ancient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1846)等書。此外還有與郭實臘合作編纂的《漢語文法述論》(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Part I. Orthography and Etymology)(1842),幫助偉烈亞力在上海發行的刊物《六合叢談》(Shanghae Serial)等。
《福建方言字典》是繼馬禮遜的《廣東省土話字匯》之后的第二本方言字典,也是新教傳教士編寫的第一本閩南語字典,對其后的閩南語字典的編纂影響很大。該書共860頁,收單字12000個,有注音,有例句。字典后附有一篇介紹福建和有關福建方言正字法的論文及索引,是研究十九世紀初葉漳州音與《雅俗通十五音》的音讀的寶貴記錄。這本字典與以前的傳教士詞典一樣,在封面將字典內容做了簡要介紹,其封面內容這樣寫道: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Containing about 12,000 Characters, the Sounds and Tones of Which are Accurately Marked; and Various Examples of Their use, Taken Generally from Approved Chinese Authors. Accompanied by A Short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Province of Hok-Keen; A Treatise on the Orthograph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the Necessary Index,&c.
麥都思之所以編寫福建方言字典,是因為東南亞當時的傳教環境。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嚴禁傳教士在華傳教,也不允許民眾與傳教士往來,所以來華傳教士把落腳點放在了馬六甲、雅加達、新加坡和檳城等華人聚居區。東南亞的華人以廣東和福建人居多,而他們基本又不懂官話。《麥都思行略》這樣描寫當時的傳教環境:“是時閩無方言之書告竣,麥君居彼,宣布道義也益勤,刊發簡編也益廣。” ?和中國本土相比,馬六甲的傳教環境相對寬松,不僅沒有限制傳教的禁令,當地政府還給予支持,傳教士享有極大的自由。但他們也面臨著諸多難題,其中最大的難題就是語言障礙問題。當地的華人,大多說福建話,也有一部分人說廣東話,官話雖然有些人懂,但說的不多。而早期來華傳教士重要的宣教方式是口頭宣教,需要到街道巷尾向路人宣講,甚至挨家挨戶地拜訪。如語言不通,傳教就無從談起。五花八門的中國方言讓傳教士十分頭疼。飽受溝通交流之苦的麥都思決定編寫一部福建方言字典,希望通過編訂此字典解決溝通問題,并能“有裨益于中國文學的傳播”,也希望學習中文的人,“不論是為文明交往之目的或宗教目的,都會從中獲益”。由此可以看出,麥都思的字典編訂已經不只是為了傳教,也有促進文化傳播交流的目的。
《福建方言字典》是在謝秀嵐1818年出版的《匯集雅俗通十五音》的基礎上編寫而成的,關于這一點,麥都思在字典的“序言”中相關介紹。麥都思還模仿《十五音》,以羅馬字斜體表白話音,以羅馬字正體表文讀音。麥都思在“序言”中還介紹了《十五音》拼讀漢字的方法,即取一字的字頭與另一字的字母,拼寫成一個新字。麥都思在書前《福建方言的拼音方法》(On the Orthography of the Hok-Keen Dialect)一文中詳細描述了這種拼字原則。對于麥都思對閩南方言的這種反切法的詳實描述,有學者指出,“對傳統閩南反切法的說明,麥都思的這本字典大概是所有文獻中最詳細的了。”
因為編寫的是一部方言字典,所以麥都思不希望像《華英字典》一樣把每個字的義項都列出來并配上例句,而是盡量控制字典的篇幅,但每個字最為普通并廣為接受的義項都已列出。在拼字法上,麥都思基本仿照馬禮遜字典的模式。但獨立編輯詞匯的義項,“每個詞匯的義項上,可能和馬禮遜博士的字典會有一些不同。如果情況的確如此,作者也不是故意而為,對于這位不屈不撓的先行者的精心之作,作者很少或就沒有參考過其詞匯的義項;因完全獨立編寫,義項及例句則來自中國人所編寫的字典,和馬禮遜的字典如有一些微小的分歧也不是沒有可能。”此處可見,《福建方言字典》沒有受到前人和本土人作品的限制,而是力求超越和創新。
麥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對后來福建方言字典的編纂影響深遠。1838年,臺約爾(Samuel Dyer)的《漳州方言字匯》出版,這本字典基本上采用了麥都思的標音法,并以《福建方言字典》為基礎,采用了新的聲調標記。麥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對其后衛三畏于1856年出版的《英華分韻撮要》和1874年出版的《英漢韻府》都有影響,后兩本字典“可以說分別是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廣東話版和官話版,因為兩書都采用了該辭典的版面形式。”
作為詞典編纂學者和語言學家,麥都思的貢獻被華語屆充分肯定。上世紀九十年代,臺灣學者洪惟仁在《臺灣文獻書目解題》一文中肯定了麥都思《漢語福建方言字典》一書的價值,認為這本字典對后世閩南語字典的編纂有開創之功,是“研究十九世紀初葉的漳州音與《雅俗通十五音》的音讀最寶貴的記錄”。黃時鑒的《麥都思〈漢語福建方言字典〉述論》對這一字典的序言部分做了深入探討,認為麥都思以羅馬字拼讀漢字的創新成果是與他那個時代的歐洲語言學背景密切相關的。
注釋:
①1842年與郭實臘合作編纂《漢語文法述論》(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Part I. Orthography and Etymology)時曾使用筆名Philo-Sinensis
②《麥都思行略》是一篇簡略的麥都思傳記,記載了他的傳教經歷、貢獻及著作概況。該文是麥都思去世后,墨海書院同仁為紀念他而作的一篇悼念文章,載于1857年的《六合叢談》。
③W. H. Medhurst.A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edhurst's preface on July 29th 1831.
④《麥都思行略》,載于《六合叢談》1857年一卷四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