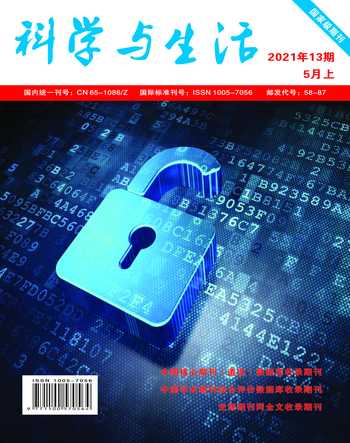圖書館與博物館整合前景
馬碩藜 馬婧婷 柳強
摘要:本文探討了在疫情的襲擊之下,對傳統圖書館功能的反思。通過城市規劃思想中“場所營造”的角度對圖書館在日常以及特殊之時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發現了超越其書籍本身的意義,并對未來,疫情之后的圖書館功能性的延伸進行探索,基于迪曼·科恩和謝爾曼將圖書館與博物館的合作描述為“未來的浪潮”展開討論,對其可能性進行詳細剖析。
關鍵詞:疫情、場所營造、未來的浪潮、社會責任、圖書館、博物館、整合
一、疫情下的圖書館
2020一場疫情席卷全國,突如其來的音符打亂了整個世界的節奏,我們觀察到,無數的行業采取千奇百怪的急救措施,有的有備而來平穩過渡,有的則因為種種原因措手不及,一些新生業態,甚至還沒等發芽,就早早夭折。作為高等院校的圖書館管理者,也見證著在這場疫情中種種自救行為,激發人們對實體機構功能性延伸的想象。
二、圖書館比書籍更強大
1. 圖書館場所的營造
美國大學圖書館協會研究與研究圖書館協會(ACRL)收集的統計數據表明,授予博士學位的機構中的圖書館每周平均開放109.75小時,每年平均有966,000多名用戶訪問。全面的大學圖書館每周平均開放91.02小時,每年平均訪問296,000次。學士學位圖書館每周平均開放89.74小時,每年平均訪問179,000次。社區學院每周平均開放63.77小時,每年平均訪問203,000次。總體而言,大學圖書館報告稱,2018年訪問量超過10億次,每名FTE學生平均訪問47次。
對于疫情期把如此大的人群體量單純依靠網絡消化到達一勞永逸的方法,未免有所粗燥。如何延伸圖書館的公共屬性,開展多樣的生長方式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亡與生活),凱文·林奇(《城市的形象》)和威廉·懷特,他們提出創造性的場所營造和“場所營造”(placemaking)的概念,總體思想源于城市規劃,了如何利用人們和社區的力量來提高城市公共空間的規劃效率和美學來設計①進行“場所營造”的關鍵是要認識到對空間的規劃應該是一種全面的,多管齊下的方法來改善場所的美學,提高安全性的社會觀念
2. 超越書籍的圖書館
“關閉圖書館對我們服務的社區有巨大影響”美國公共圖書館協會主席兼圣安東尼奧公共圖書館總監Ramiro Salazar說。“直到關閉為止,人們才意識到圖書館對他們來說多么重要。”西雅圖的圖書館經理達西·布里克西(Darcy Brixey)說:“圖書館是任何人都可以去而不必買東西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地方之一。“這是能夠去洗手間的地方,或者能夠去溫暖干燥的地方,這是最基本的事情。長期以來,圖書館一直是人們無家可歸或住房不穩定者非正式避難所。加州州長加文·紐瑟姆(Gavin Newsom)表示,他預計僅在加利福尼亞州,就有60,000無家可歸者會感染冠狀病毒。在較小的城鎮中,這個問題尤為嚴重,那里的圖書館為這些人群提供了庇護場所。
圖書館還是低收入家庭的生命線,他們不僅借書,還貸更多的東西—烘焙材料,電動工具和一般用品,較富裕的人可能會理所當然。圖書館為處境不利的兒童或年長者提供社會資源,及在農村社區或無力負擔互聯網絡的人們。”
三、圖書館與博物館結合的可能性
1. 功能
博物館和圖書館同處一地可能會使其功能性更加強。施拉格也支持“共享空間的創造和管理”,同時“物理存在也可以是不必要的”,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技術手段進行溝通,他們之間有許多交叉資源,可以達到互通互享。并且,博物館傳統上收集具有文化,宗教,歷史重要性的材料和物品,以保存,研究,與圖書管不同的多了展示給公眾,以供教育和娛樂的功能,但大部分與圖書館的功能有所重合,二者也能能夠利用各自優勢相互彌補②。
2. 語境與理論
2003年,迪曼·科恩和謝爾曼將圖書館與博物館的合作描述為“未來的浪潮”。“圖書館-博物館合作”可以定義為圖書館和博物館之間的合作,他們也可以衍生出其他合作。這些合作可以是一次性項目或連續的活動計,它們可以在同一地點,也可以相互遠離。可以讓圖書館成為不全是博物館工作人員和研究人員的圖書館。所以這里的“協作”一詞指的是更深入地共享和匯集資源的更復雜的合作③。
3. 相關法律法規
2012年7月國家典籍博物館于經中央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批復國家圖書館加掛牌子成立,國家圖書館同時成為國家典籍博物館。并且作為國家典籍博物館開館之后的首展,“國家圖書館館藏精品大展”這為全國其他地方推行圖書館與博物館結合的可能性做了積極探索。
4. 協作的有益之處
1)吸引新的觀眾,擴大圖書館和博物館的范圍;提高公眾對博物館和圖書館作為傳統保守機構的認識;
2)尋找鼓勵文化遺產和保護的新途徑
英國,圖書館主要利用博物館的遺產功能作用,與圖書館的歷史館藏形成了伙伴關系。其中還包括將材料數字化,并通過互聯網提供。在美國幾乎沒有歷史項目,重點是利用參與組織的物品和書籍開發一個合作網站。
3)共享物理資源,如空間和材料
而更廣泛的意義是,協作將博物館和圖書館服務與工作人員專業知識相結合,并使兩個機構都有所受益,增強了用戶體驗,鼓勵機構間的交叉訪問,向各種目標群體推廣資源,改善機構間的協調,展示聯合工作和培訓,或提供工作實踐的模式,并能夠借此獲得額外的教育項目空間,改善收藏的獲取途徑,提高包數字化進程。
5. 雙方職責
圖書館和博物館對合作的貢獻各不相同。非圖書館或博物館特有的貢獻包括項目管理、申請資助、撰寫報告、計劃規則、給員工時間、獲得資金、提供空間和設施、提供設備、營銷、制作攝影收藏品和提供工藝方案。圖書館的具體貢獻主要集中在圖書管理、購買其他材料、提供故事時段以及為項目提供必要的研究。圖書館也更有可能承擔硬件和軟件維護以及目錄數字化的責任。博物館通常提供展覽和工作室空間以及相關的藝術品。總的來說,博物館經常參與項目,制定活動指南,設計展覽和舉辦開幕招待會。
結論
總之,開展圖書館-博物館合作有相當廣闊的前景。“未來的浪潮”成為現實,發掘其巨大的潛力。冠狀病毒雖然造成對社會造成種種破壞,圖書館的意義也隨之產生了一些連鎖變換。這樣的時態讓我們思考圖書館更多的可能性。失去了單一實體的框架,多種機構的有機結合,新事態的圖書館讓意義穿透建筑的外墻。
注釋
①場所中的場所:場所中的場所如何構建場所和社區,Susan Silber berg,Katie Lorah,Rebecca Disbrow和Anna Muessig(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城市研究與規劃部,2013年),可從https://dusp獲得。mit.edu/sites/ dusp.mit.edu/files/attachments/project/mit-dusp-places-in-the-making.pdf
②Emmanuel N. Arinze的“博物館在社會中的作用”所述
③戴曼-科恩和謝爾曼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