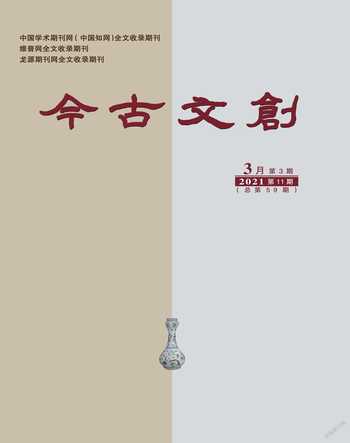關于中日文化背景下語言差異的研究
【摘要】 跨文化交流中,一方對另一方的社會文化傳統沒有充分地了解,說出不得體的話語,做出不恰當的行為,是導致交流障礙的重要原因之一。跨文化交流所產生的障礙、沖突及誤解,不僅僅只是與語言的發音、語法及單詞有關系,還與使用該語言者之間的交流有關系。
【關鍵詞】 跨文化交流;文化語境;語言差異
【中圖分類號】H030?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11-0106-02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國家、民族所使用的語言也相應不同,彼此之間的交流會產生各種語言障礙問題。這些問題的研究吸引了眾多語言學者的關注,成為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新的研究領域。不同文化圈的交流是指不同民族、語言及文化背景下的交流,即“跨文化交流”。
文化不同,行為模式不同,這是文化規則的一種表現。在跨文化交流過程中,文化規則和語言規則都參與其中,并有著直接關系,不同文化之間,由這兩個規則產生的差異是導致交流障礙的根本原因,語言研究學者將此交流障礙問題統稱為“語言差異”。關于“語言差異”的研究,顧日國、陳融、沈家煊等學者都有研究,但是卻未曾涉及中日交流所產生的“語言差異”問題。本文將以中日不同文化背景下引起的語言差異為考察對象,通過介紹具體事例加以解釋說明。
一、語用學理論——“文化語境”
關于語用學,美國的語言哲學家H.P.Grice曾經提出“合作原則”理論。正常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會話不是毫無關聯性的語言組合,而是會話參與者抱有共同目的,彼此接受對方的意識。為了使話題能夠順利展開,會話參與者要遵循“合作原則”。在參與話題時,參與者需要意識到自己所要表達的內容必須符合話題公認的目的或者方向。同時,H.P.Grice還提出了四個基本準則:1.數量基準(信息量的提供);2.質量基準(內容必須真實可信);3.關聯基準(內容具有相關性);4.方式基準(表達需要簡潔明了)。Levinson S.C.承接并延續了H.P.Grice的研究成果,但是索振羽認為還有補充的必要,在保留“合作原則”理論的基礎下,進一步提出“得體原則”,即根據語境的需要而采取委婉方式表達說話內容,包含3個準則:“禮貌基準”“幽默基準”“抑制基準”。關于索振羽提起的語境問題,王建萍等學者指出語言和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語言影響著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而作為語境之一的文化相應地推動著語言的發展。對此,稱之為“文化語境”,具體是指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一個民族所形成獨特的文化傳統及風俗習慣會直接影響到該民族語言的表達。
二、從具體實例看中日語言差異
接下來,本文將依據語用學的文化語境理論,通過具體事例考察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出現的語言差異。
實例1 進電梯?乘電梯?「エレベーター」に「入る」?「乗る」?
中國留學生張某進入電梯(エレベーター)之后,看到小孩子飛奔過來,很親切地問了一句:“入りますか。”(你進來嗎?)結果,小孩子回答道:“あ、はい、乗ります。”(啊,我“乘”,謝謝。)張某很奇怪,明明自己問的是進不進,對方為什么回答“乘”。當然,張某知道像公共汽車、電車等交通工具會使用“乗る”這個單詞(バスに乗る、電車に乗る),但是為什么上下移動的電梯也要使用“乗る”。為了解開這個疑惑,張某請教周圍的日本朋友,“進電梯也要用‘乘’這個單詞嗎?”(エレベーターに乗る)大家的回答很一致,“電梯是交通工具,當然是用‘乘’啊。”然后,張某又問:“如果我人在車里,問車外的人要不要進來,還是要用‘乗る’嗎?”(車に乗る)朋友回道:“車是交通工具,那自然是用‘乘’啦。”
在密閉的空間入口處,對著門外的人問:“你進來嗎?”(入りますか)比如“進教室(教室に入る),進食堂(食堂に入る)”,張某知道在這種場合,中日文的表達是一致的。但是,像交通工具這樣的移動物體,在日語里是使用“乘(乗る)”,而不是“進(入る)”,比如坐地鐵(地下鉄に乗る),坐飛機(飛行機に乗る)等等。但是對于這種用法,中國留學生張某卻不能理解,甚至有時會出現讓張某覺得很有趣的場景。這次是在等電梯的時候發生的,當時門打開了,張某對著里邊的人問道:“下嗎?(降りますか。)”對方雖然回答道:“對,對,是下。(はい、降りますよ。)”卻完全沒有要出電梯的意向。當時,張某覺得很奇怪。之后從朋友那得知,問別人從電梯出不出來時,要說“出(出る)”這個單詞。張某覺得不可思議,進電梯不說“進(入る)”,出電梯卻要說“出(出る)”。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漢語和日語在表達使用交通工具時,動詞的異同。在日本人看來,不管是哪種交通工具,自己進去的時候,都會說“乘(乗る)”。但是,中國人雖然在使用交通工具時會說“乘(乗る)”,而由外入內(密閉空間)時,會說“進(入る)”。這是因為日本人將注意力集中在“物體”(交通工具)上,選擇使用“乘(乗る)”,中國人則重視的是由外到內的“移動過程”,選擇使用“進(入る)”。然而有意思的是從里邊(密閉空間)到外邊,漢語和日語使用的都是“出(出る)”這個單詞。
眾所周知,日語漢字是從中國流傳過去的。但是,這些漢字在日本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伴隨著日本人的習慣以及思考方式,原本的意思慢慢地發生了變化。例文中的“乗る”的漢字“乘”除了漢語“乘坐”的意思之外,還衍生出其他意思。對這樣“一字多意”的現象,Marina Rakova 指出一般情況下,單詞不僅僅只有一層含義,隱喻下會派生出其他含義,而這些含義正是其民族文化背景下衍生出的語言產物。
實例2 對家人的稱呼
留學生小王在語言培訓班做兼職,教日本人漢語。某次暑假,小王說要回老家上海,有兩位學生表示想一起去。抵達上海之后,學生問小王:
(1)“媽媽在家里等著嗎?”(ママはお家で待っているんですか)
小王對學生說的“ママ”(媽媽)感到很不解。隨后,兩名學生又說出讓小王困惑的話語。
(2)“媽媽很能干吧!”(ママは働き者ですね)
(3)“爸爸去哪兒了?”(パパはどこに行ったの)
(4)“哥哥今天也上班嗎?”(お兄さんは今日もお仕事ですか)
小王終于明白原來她們是在問自己的家人。年底,學生發出邀請說是去看歌舞伎表演,小王欣然答應前往。這時,其中一位學生說道:
(5)“我可能會把家父帶上。”(うちのお父さんも連れて行くかもしれません)
那天,小王到達劇場,跟大家打招呼。這時,正好聽到那位學生在跟周圍其他人介紹:
(6)“這是我父親,請多關照。”(うちのお父さんです。よろしく)
小王仔細一看,被介紹人是她的先生。那位學生稱呼自己的先生為“お父さん”。那之前她說的應該是“我可能會帶我先生來”“這是我先生,請多關照。”
這里的“語言差異”恰恰反映了中日文化和習慣的差異,也符合H.P.Grice的語用學理論里所提到的“合作原則”之“關聯基準”,正是因為兩個民族的文化底蘊不同,才導致交流時出現“語言差異”。
實例3 直接表達和委婉表達
在中國快餐店買食物時,經常聽到這樣的對話:
(7)店員:“要不要吸管。”
客人:“要。”
而在日本的快餐店點餐時,對話是這樣的:
(8)店員:「ストローをお付けしましょうか。」(配上吸管嗎?)
客人:「お願いします。」(請配上。)
店員:「かしこまりました。」(知道了。)
通過這兩組對話可以看出,日語是間接含蓄地表達個人情感的,漢語是直接明了地表達個人意愿的。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盡量避免“是(はい)”,“不是(いいえ)”這樣直接的表達。類似的還有表示拒絕的單詞“ちょっと(稍微有點)”,比如,邀請朋友看電影,對方拒絕道:“明日ちょっと……”(明天稍微有點)在表達拒絕時,日本人認為直接拒絕會傷害對方的感情,所以盡量選擇溫和的表達。
日本人這樣的語言文化和習慣正是H.P.Grice提到的“方式基準”和索振羽提到的“得體原則”之“禮儀基準”,這也側面反映了在歷史進程中,不同民族使用的語言在社會文化環境影響下,會慢慢形成符合該民族特色的表達方式,同樣的詞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表達上會有很大差異。
三、結語
本文從語用學的文化語境理論出發,通過列舉單詞、稱呼以及說話方式等具體實例解釋說明中日兩國文化背景下的語言差異。為了能夠完全理解對方所說的內容,就必須要提前去了解其成長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風俗習慣。基于文化背景不同,人們的說話方式或者說話習慣也隨之不同。跨文化交流過程中,社會文化知識是交流能力的關鍵組成部分,所以在學習外語時更應該注重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與比較,從而避免語言差異引起的障礙與問題。
參考文獻:
[1]何自然,冉永平.語用學概論(修訂版)[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顧曰國.禮貌、語用與文化[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2,(4).
[3]陳融.面子 · 留面子 · 丟面子——介紹Brown和Levinson的禮貌原則[J].外國語,1986,(4).
[4]沈家煊.不對稱和標記論[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5]王建萍,周明強,盛愛萍.現代漢語語境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
作者簡介:
何娟娟,女,漢族,文華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涉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