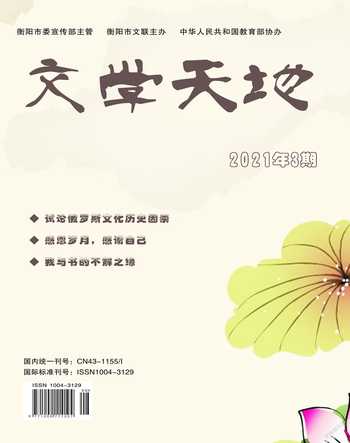從薩特的“介入”美學看作家與讀者的互動
唐競
摘要:在《什么是文學?》的文本當中薩特關于寫作結合存在主義和現象學進行了有力闡釋,而“介入”理論作為薩特思想的關鍵詞之一也在其中有較為充分的說明。本文試圖圍繞薩特《什么是文學?》這部作品尤其是其中《為什么寫作》的相關內容,把握薩特關于作家和讀者之間關系的觀點,從作家與讀者的互動關系中解讀薩特文學服務于社會的介入思想,從人學的角度思考寫作作為作家和讀者介入現實的手段所包含的意義。
關鍵詞:介入;作家;讀者;自由
介入文學在20世紀的法國作為重要的文學現象而受到當時乃至現在學界的重點關注。而薩特的介入理論象征著二戰之后其思想觀點的一次躍進。經歷了戰爭,他意識到面對重大現實的重要性,逐漸在現實中覺醒,從遠離政治走向介入政治的主張。“介入”一詞并不是薩特的發明,將它放在社會這一語義層面上使用,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逐漸普及的,隨后,薩特將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放進他的美學思想作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補充,“介入”就是他重要的美學思想之一。
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的“介入”最早出現,介入在獲得其政治含義之前首先是一個哲學概念,“介入從一出場就是一個涉及自我與他人關系的概念,是作為主體的自我意識與客體世界發生聯系的行為。” 到1945年二戰結束,薩特在《現代》雜志上發表文章,號召作家積極介入到現實的歷史洪流之中,面對現存的社會困境。薩特認為,現實的困境會把人禁錮住,人需要自由也必須是自由的。人本身是擁有自由并被賦予選擇和行動的自由以證明自身在世界的存在,而人是不得不做出選擇的,連放棄也是一種選擇,做出了選擇就要對此負責。因而,面對無法逃離的困境,人們有兩種處理方式——消極的回避和積極的介入,薩特則認為,在文學中應該大力主張介入,作家要對這個世界負責任用他們的作品揭露世界,呼喚人們走向自由。介入于薩特而言就是人的一種積極入世的選擇,一旦做出選擇就要為此負責,這種選擇意味著進入社會現實加入到時代斗爭之中,完全地表明自己的立場態度,徹底的“介入”。隨后,薩特通過《什么是文學?》系統論述了他對于文學的構想,將介入與文學有意識地結合在了一起,其中,特別地從寫作論和閱讀論的角度關注到文學作品產生過程中作家和讀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從這個角度上可以看到作家和讀者作為薩特介入理論的兩個重要部分發揮的巨大作用。
一、關注作家和讀者
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學的四要素即作品、藝術家、世界、欣賞者對于此前西方文學理論研究中關乎世界、作家、文本、讀者文學四維度的獨立分析和四者之間關系的爭執討論來說算得上階段性總結式的發言。事實上文學批評活動很容易著重關注到一個方面,因而出現“作家中心論”、“讀者中心論”和“文本中心論”,為克服各自的缺陷避免批評的片面性,在此之下力圖綜合作家、文本、讀者三個要素的概念也就隨之提出來了,這之中,有將文本與文本相關聯的“文本間性”的觀點,也有將文本與讀者相關聯的“接受美學”的觀點……由此可見,文學四要素必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不同要素可以相互搭配融合的復雜關系,僅就作家、文本、讀者三者之間的關系而言,任意將其中一個要素暫時抽離,也并不影響對其他兩者之間的關系研究。將薩特的“介入”理論放置于20世紀文學批評的場域來看,他在文學創作的整個過程中,對于作家和讀者的關注一方面正是表現了上述將文學要素納入文學批評活動的方法,可以看作是一種合流,另一方面則體現的是他存在主義的重要思想。
薩特的介入理論很大程度也受到海德格爾存在主義的影響并有進一步發展。存在主義關心存在的問題,“人”的問題正是薩特和海德格爾都關注的話題,人的本質性就能夠很好的證明“存在”的意義。海德格爾認為“此在”有一個變化的過程。一開始海德格爾確認人就是世界的“此在”,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的存在證明了整個世界的“在”,如果人不存在了似乎世界也就會因為不能思考而陷入虛無。到了后期,海德格爾認識到“人”對于存在而言只是存在的一種證明者是世界存在的守護者,除了人之外,詩歌、音樂、畫作都是存在者,它們同“人”一樣都是展現“在”的一種方式。因此不能只關注到作為存在者的人而應該更加關注存在本身。海德格爾的哲學要求主客觀的統一性——世界與我同“在”,人的主觀思想意識同外在的世界統一于“在”。而“在”本身就是一種活動擁有無限選擇性和無限可能性的活動。在要先于存在者而產生,只是當選擇作為“我”而存在之時“在”成為了一個實體,其可能性也隨之消失了,也就意味著活在當下,立足于此在。因此人也好,藝術也好,在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中儼然成為了表現“在”的一種方式,它們是具有實體形式的一種存在。
薩特的存在主義對存在的問題做了新的理解闡釋將存在同“人”相關聯。在存在主義的立場上,薩特也認同“存在”的重要意義,他提出“存在先于本質”,但這個存在首先就是指人的存在,人要首先出現對自身加以說明從而證明“存在”。意識由人自身出發,先意識到我的存在然后再認識到整個世界的存在,因而在薩特這里人之存在就有極其重大的含義。由此來看,薩特的存在主義就從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中跳脫出來,直接進入到屬于“人”的世界,雖然海德格爾也關注人,但是人僅僅只作為一種存在形式出現,但從薩特的觀點來看,人的存在要優先于一切。
正因如此,薩特從存在主義的角度出發來思考介入理論,更加關注到主體和主體之間也即是作家和讀者的關系問題,從人學立場出發來探討文學對社會的介入。薩特的介入政治的美學是“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美學”,他試圖用存在主義補充馬克思主義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一樣關注人,認為“存在的問題是關于人學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都有推崇自由和行動哲學的共同點,二者可以結合起來。” 薩特關于介入的美學理論從存在主義的觀點出發,強調人的實在性以及人之于世界的本質性,藝術創造的主要動機也在于認識到人對于世界而言是重要的,感受到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之中“我們”是本質的。尤其在文學作品創作的過程中,正是需要“我們”即作家和讀者的共同參與。寫作一方面是作家體現自我存在,召喚并追求自由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則是讀者感知作家及其自我存在,走向自由的方式。因而,薩特關注到寫作中作家和讀者的問題,尤其是在《為什么寫作?》中更強調了作家、讀者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對于薩特文學介入政治的美學理論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出發進行思考。
二、作家與讀者的互動
從作家的立場上看,寫作首先需要作家創作,薩特認為寫作是作家介入現實政治的行動選擇。薩特的存在主義立場上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認為了實現自由本質必然要進行選擇,而作家選擇寫作來面向自由。作家寫作有其目的性,在薩特的介入理論中更多的是政治意味,就是站在復雜社會及其尖銳斗爭面前通過作家寫作介入現實政治,揭露世界為自由而抗爭。作家通過寫作投入到現實斗爭之中也就是介入。
從讀者的立場來看,作家的寫作首先就是為他人而寫作,因此需要讀者的參與。作家寫作的一個目的就是召喚讀者的出現,如果一個作家的作品寫完以后就被束之高閣那么作品將毫無意義。“藝術品首先在事實上存在,它首先是純粹的召喚,是純粹的存在要求。……你完全有自由把這本書擺在桌子上不去理睬它。但是一旦你打開它,你就對它負有責任。” 因而讀者的閱讀也是一種介入,介入作家的世界從而介入現實的社會從而尋找自由、實現自由。
在薩特介入美學中,作家和讀者的關系絕不是孤立的,藝術的創作和接受本身就是意向性的連貫行動,與此同時作家同讀者之間也存在著互動關系,寫作活動包含閱讀活動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1.自由立場上的互相信任
自由是薩特美學思想的核心,是人的本質,寫作的本質就是一種要求自由的方式,自由是作家寫作的目標也是社會的指向,作家介入保衛自由的斗爭正是借助于寫作來完成。作家創作本身是自由的。作家借助于語言實現對客觀事物的超越,揭露世界保衛自由。與此同時,作家創作是對讀者的召喚,對自己和他者自由的召喚。“作家向讀者的自由發出呼喚,讓它來協同產生作品。” 作家需要讀者的自由來承認自身的自由。只有通過讀者的閱讀作家的自由才能真正從作品中解放出來,與此同時讀者也得到自由的召喚認識到自己的自由。“為了能訴諸自由,只有一個方法:首先承認它,然后對它表示信任;最后用它自己的名義,也就是說用人們給予它的信任的名義,要求它完成一件行為。”作家的自由需要讀者通過閱讀作品來承認,只有得到這樣的自由才能真正是作品存在,才能證明作家之于世界的一種本質性。
薩特認為,就作家和讀者的關系來看,作品創作是對讀者自由的召喚,讀者在無拘無束的閱讀過程中意識自己的自由,這種自由包括閱讀的自由和情感的自由。作品中的文字只是作為讀者閱讀的指引但讀者閱讀行為并不受外界任何對象的控制,具有主體性,因此薩特把閱讀當作一場自由的夢。閱讀活動需要情感的參與,薩特把這種沒有外在現實制約的讀者情感稱之為豪情——以自由為根源和目的的情感,這種豪邁情感的運用是作家要求讀者將自己的情欲、思想、價值觀、性格等等方面全身心地奉獻于作品中,有了這種奉獻從而獲得閱讀和情感的自由。
因此在介入理論中,作家和讀者的互動都要關涉到自由,在自由的立場之上形成二者信任的關系。正如上文所說,讀者的閱讀活動會產生自由的豪情,這種豪情實際上正是一種作家與讀者的信任互動——“閱讀是作家的豪情與讀者的豪情締結的一項協定;每一方都信任另一方,每一方都把自己托付給另一方,在同等程度上要求對方和要求自己。” 作家和讀者之間擁有這種豪情的信任,作家對自由的運用和讀者對自由的運用不是強迫性的承認,而是雙方的自由決定。因而,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得到越多則向作家要求的也更多,同時,作家也同樣會要求讀者更多的要求,由此雙方的自由得到顯示的同時也能夠揭示別人的自由。讀者在閱讀時就要相信作家創作時的情感與主觀情感已經保持距離處于自由的情感狀態,當讀者在閱讀作家作品時自己的情感也變得自由。
作家為讀者的自由而寫作并要求自己的自由得到承認,也正是需要作家與讀者之間的信任。只有通過自由立場上的信任關系,作家才能確信讀者能夠把自由歸還給他,并承認作家創造自由的能力,才能確信讀者有能力用相對稱的方式來呼喚作家的自由。薩特在此提出一個閱讀過程中的辯證矛盾:“我們越是感到我們自己的自由,我們就越承認別人的自由;別人要求于我們越多,我們要求于他們的就越多。” 作家向讀者的自由發出召喚,讀者只有得到這個自由才能與作家共同參與創作使作品得以完成,同時雙方都各有要求通過這些要求使得二者之間緊密相連從而還原出一個存在自由的整體,一個由人性籠罩的世界。總的來說,作家通過寫作承認讀者的自由,讀者通過閱讀承認作家的自由,可以看作是一個對于人的自由表示信任的互動。
2.作家創作與讀者再創造
寫作的過程首先是作家進行文本創造的過程。薩特反對康德審美無目的的思想也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傾向,把文學的介入社會的實踐活動作為寫作的重要目的,而藝術家則負有這樣的使命,文本創造要成為作家介入的行動選擇。同時,在薩特看來,作家的介入需要借助于語言,用文字揭露世界并伴隨著行動以求改變世界,通過語言的力量呼喚自由。語言在介入活動中要發揮重要的中介作用。薩特在《什么是寫作》中認為散文可以介入而詩歌不可以介入的一個原因就是散文作家對于語言的有效運用,用語言表現命令、憤怒、辱罵又不像詩歌一樣迷失于情感之中,感知語言的同時超越語言。介入作家通過語言創作文本,把溝通作為語言的目的希望有所揭露從而引發變革。作家應該把作品創作當作自己事業選擇,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這是一種正面的積極的投入展現自己的堅定意志。
寫作就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參與完成的。作家通過文本創作顯示自己的自由召喚讀者的自由,證明自己的存在;讀者在自由的閱讀過程中,承認作者的自由解讀語言創造文本意義。作品正是通過作家的創造和讀者的再創作實現其真正含義,展現全部的自由。作家的創作包含著一個準閱讀的過程,他寫下文字的同時也看到了文字但這種閱讀同讀者的閱讀是不同的。作家的閱讀帶有自己的主觀意志,并且他的閱讀實際上只是對于創作過程的再演,對寫下符號進行檢查,因而超出自己的思想和文本之外的東西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感知到,除了發現作家自己別無其他。如果作家只是隨心所欲的寫作只為自己不為他人那么就無法將作品轉變為客觀實在,因此作家作品期待讀者閱讀,也需要讀者的再創造。
讀者的加入讓作者創作的文本不在只是一個個軟弱無力的符號,閱讀“好像是知覺和創造的綜合。” 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沉浸于文本同時還需要超越文本。讀者的再創造首先需要語言發揮作用。在作者的引導之下,語言召喚讀者進入文本,符號成為一種審美對象,作者提供的符號會激發讀者的一系列情感,之后再將情感重新投射到文本當中,原始文本同讀者解讀后的情感意識融合起來實現一種新的創造,幫助文本轉變為客觀存在。同時,薩特認為語言一方面作為一種思想的表達形式,另一方面又禁錮了思想,單純依靠語言并不能證明存在本身。因此,讀者的閱讀必須要超越文本語言進行再創造,走向存在也即是自由。
讀者的再創造還需要情感的參與。文字激發讀者的一系列情感快樂、悲傷、同情、憐憫、憤怒,情感和想象力為文本語言插上翅膀賦予文字以新的生命而實現自身的超越。薩特還談到,閱讀會引發讀者的審美喜悅,通過這種審美喜悅讀者感知到自身處于自由的閱讀活動當中,與此同時閱讀還在這種喜悅中創造出一個新的自由的世界,突破自在世界與自為世界的鴻溝,讀者體會到,自己的自由創造了新世界實現世界從自在的實存走向自為的實存。這就是一個審美變更的過程。
作家的創造使得作品產生能夠揭露世界從而有機會介入社會,是嶄新的創造;而讀者的再創造是對作者主觀世界的進一步突破,是對文本中隱含意義的再發現,還原意義的完整性,“在揭示的過程中創造,在創造的過程中揭示”。
三、作家與讀者共同“介入”的美學
薩特介入現實政治的美學是一種行動美學,結合存在主義的思想,人要選擇和行動由此才能證明和實現自己的本質性,因此寫作成為介入的重要方式,而介入的主體必然要關注到作家和讀者。作家的介入是對自我存在的證明更重要的是對艱苦的現實世界的揭露和抗爭,特別是在二戰的背景之下,通過作家介入呼喚社會的自由擺脫生存困境。而讀者通過閱讀形式介入到創作當中,一邊同作者進行信任互動,一邊則通過閱讀了解到眾多自己之前所沒有意識到的東西比如自由接受喚醒從而投入改變現實的斗爭中。對于作者和讀者而言,他們選擇通過創作和閱讀的方式介入,而介入就意味著要承擔揭露現實世界的重任,使自由在最終得到實現,這是存在主義哲學在薩特介入政治的美學中的具體呈現。
薩特介入政治的美學鋒芒直指資產階級及其所在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在對社會深入思考之下,提出介入理論正是希望通過實踐改變破敗的現實生存環境。作家總是在為他人寫作,薩特認為作家們面向的應該是受壓迫的民眾,應該擺脫此前曾服務的階級站在普遍人性的高度對廣大讀者發聲,向他們發出召喚同時分擔民眾的痛苦。最終薩特想要表達的正是文學服務于政治的思想,體現在介入現實反抗壓迫的觀點上。他認為寫作帶有目的性和功利性,無論是作者的介入還是讀者的介入都應該是以推動社會新的變革為目標。作家與讀者在介入的過程中團結成為一個反抗壓迫的整體,一種整體性的文學在現實社會中發揮作用。自由的文學正是以被壓迫的讀者作為理想讀者而閱讀和寫作,“閱讀和寫作成為人們在文學活動中介入現實政治的行動”。 介入行動是為了保衛自由,而寫作的自由與閱讀的自由中恰恰包含政治的自由。社會上的壓迫、剝削、奴役等非正義的行為都應該被揭露、被認識、被反抗,包括作家和讀者在內的民眾都應該與這種壓抑自由的行為作斗爭。
參考文獻
[1](德)馬丁·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林中路》,《藝術作品的本源》,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2](法)讓-保爾·薩特著,施康強譯,《什么是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3]馮憲光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重慶出版社,1997。
[4]施康強,《薩特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文藝理論與批評》,1994(01)。
[5]趙勇,《文學介入與知識分子的角色扮演——薩特<什么是文學>的一種解讀》,《外國文學》,2007(04)。
[6]畢曉,《論薩特的“介入文學”與羅蘭·巴特的“作者之死”》,《國外文學》,2014(02)。
[7]冉一婷,《文學是他者的在場——由薩特<什么是文學>重審作家與讀者的關系》,《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03)。
[8]金松林,《介入與否:羅蘭·巴爾特與薩特的理論分歧》,《文藝理論研究》,2018(02)。
[9]殷寶怡,《論薩特存在主義文學觀——以<什么是文學>為例》,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2。
[10]王倩,《薩特“介入”觀研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7。
趙天舒,《西方文論關鍵詞 介入文學》,《外國文學》2018,(05)。
馮憲光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第378頁,重慶出版社,1997。
(法)讓-保爾·薩特著,施康強譯,《什么是文學?》,第4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同上,第43頁。
同上,第44頁。
(法)讓-保爾·薩特著,施康強譯,《什么是文學?》,第5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同上,第48頁。
(法)讓-保爾·薩特著,施康強譯,《什么是文學?》,第3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法)讓-保爾·薩特著,施康強譯,《什么是文學?》,第4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馮憲光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第395頁,重慶出版社,1997。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重慶 ?4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