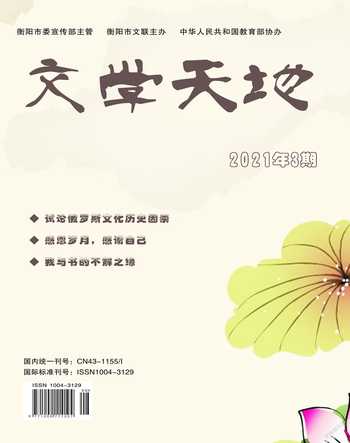中國丑學的審美功能
王思嘉
摘要:丑學與美學相對應,是一門研究丑的概念、形態和本質的學問,它以其特殊的方式負擔起美學的部分功能。而中國丑學有其獨特之處,本文將從具體例子出發,歸納中國丑學獨特的審美功能。
關鍵詞:審丑,中國丑學,審美功能
在中國審美理論框架中,素來以“溫柔敦厚,寧靜致遠”為審美主流,審丑的范疇便相對狹窄了。盡管相對于審美而言,美學體系中的“丑學”相對稀罕,但是審丑以其特殊的姿態存在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去審視固有的存在的事情事物、倫理觀念、哲學論辯等并形成特殊的區分與框架。中國“丑學”有其獨特的意義,這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丑”自身作為一種審美傾向存在于人類思維中,人類對“丑”并不趨之若鶩,相反,它甚至可以成為一種審美崇拜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從而發掘現實生活當中的某些丑在藝術上獨特的價值。
早在新石器時代,圖騰文化便已經興盛。扭曲的線條和猙獰的邊角共同構成幅幅圖騰,展示出一種怪誕、恐怖的意味,但它又以它的魅力活躍于宗教祭祀和人們日常生活等方面,為人所賞。尤其是那個時期,宗教祭祀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圖騰作為宗教倫理文化的載體更是呈現出了一種怪力之美。且以其中的龍圖騰為例。龍圖騰揚首張口、彎腰弓背,并不符合傳統對于“美”的形象的定義,卻歷來作為天子的象征,以奇丑的形象為人類所崇拜。這種藝術創造“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間滲透著、灌注著古人獨特的神話猜想、宗教體味、審美快感和藝術情趣。先秦時期的《山海經》中也記載了很多丑陋和奇異的人物和怪獸形象,中國文學歷史上更是不乏奇人怪物形象。例如中國傳統神話、唐傳奇、明清志怪小說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中國歷史上“審丑”事實的存在。即使到現當代,科幻小說、玄幻小說等文學形式的興盛設置了獨特的“審丑”地域,受到人們的廣泛喜愛。在新媒體技術發展的時代,小說中的各類人物更是被改編為熒幕、報刊、圖書上的各形各色的形象,其中不乏模樣奇怪而為人們欣賞的怪異形象,如《捉妖記》中的胡巴長得像個矮蘿卜卻十分討人喜歡。
第二,審丑又對這些丑惡的部分進行美學觀照,負責批判生活當中的丑惡現象。在中國傳統的古詩文中,以“丑”襯“丑”司空見慣。最典型的便是中國傳統的諷喻詩。
許多詩歌借某物諷刺某人或某類人。從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先秦時期的《詩經》開始,就不乏這種映襯手法。如我們常見的《詩經·氓》。“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桑樹葉子落下了,枯黃憔悴任飄搖,女子日夜操勞、容顏老去而被氓所遺棄,宛若飄零無依的落葉一般。借落葉之凄涼光景映襯出自身的悲哀處境,側面烘托出氓前后不一、朝三暮四的丑態,以此諷刺見異思遷、貪新忘舊的男子及其行徑。
后來也不乏以眼前慘象揭露社會黑暗和抨擊昏庸統治者的詩歌。例如唐代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便把人世間的丑寫進詩中。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別”將年事已高卻仍被抓走服役的老嫗、新婚卻得別離的新夫、上戰場慘死的兒子等等形象全部凝于筆尖,以血淚注塑,將人世間的陰面血淋林地擺在我們眼前,以此揭露社會的黑暗。
還有一類以他物觀照自己內心之詩詞,折射出心中之凄涼和生活之苦丑。如馬致遠《天凈沙·秋思》全文將慘淡的意象組合,“枯藤老樹昏鴉”“古道西風瘦馬”,直逼文末“斷腸人在天涯”一句,肝腸寸斷,將自己窮困潦倒的“丑陋”生活表現出來。
這一類現象也并不限于文學領域,在藝術的其他領域依舊常見,如繪畫、音樂等形式隱藏著許多令人唏噓的丑陋面目,只是在中國,以“丑”襯“丑”的表達方式更常為人訴諸筆端,或是以文字為載體展示出來。
第三,“美”與“丑”作為一種工具,定義哲學中的矛盾對立兩方,概括衍生出理念框架,展示人類獨特的哲學思維。而美丑作為矛盾雙方的總括,又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在這種語境下,我們更少關注“美”與“丑”詞義詞源和自身概念,更少關注美丑好壞、是非論斷,而是更強調美丑分化而來的具體內涵,由此推動中國框架的構建。
莊子的美學思想便將該觀點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從哲學上的相對主義出發,否定現象界美與丑的區別,主張“厲與西施,詼詭譎怪,道通為一”,進而認為人們對美與丑的審美評價也是相對的,“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 ,否定存在審美評價的客觀標準。《莊子·德充符》里的“真人”“至人”卻為“兀者”,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乃是“無形而心成者”。《德充符》中的有德之人樣貌丑陋殘缺、沒有權勢錢財卻為人景仰追隨,真正的為人所賞的美乃是一個人的美好品德,即德“使其形”。 在莊子這里,德是使一個人成為人的根據,它是一個健全生命所表現出的生命力,是人性中美好之處的彰顯。有些人雖然身體上“丑”,但殘疾亦是順應自然本性,且道德上的“美”早就成就了他整體的“美”。莊子提出的“以丑為美”的觀念大大消除了“美”與“丑”的對立,而他提出的美丑觀又為人們思想中的行為判斷做出了新的理解和范式。
從倫理學角度出發,儒家以“善”為美,以“惡”為丑;從哲學角度出發,道家以“自然無為”為美,以“矯飾華麗”為丑……這些觀念交織,使得“美”與“丑”的評定有不同的多樣的標準,“美”與“丑”的邊界相對模糊,削弱了二者的對立性。美丑并不絕對,但美丑概念的存在又輔助了人們明白各家理念,厘清并構建中國傳統哲學體系。
除了以上幾點,“丑”的存在還能為看世界提供新角度、新思路,能完善中國美學框架體系,還能使中國文化思考更具有深度……總而言之,審丑在中國具有豐富的審美功能,在人們的思維意識中,它也因其存在的必要占據中國美學的半壁江山。
參考文獻:
1.孫通海(譯注),莊子[M],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92-113頁
2.安小蘭(譯注),荀子[M],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4-53頁
3.高小康,丑的魅力[M],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
4.陳心恬,當代中國“審丑”現象解析[D], 黑龍江大學2015年碩士論文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