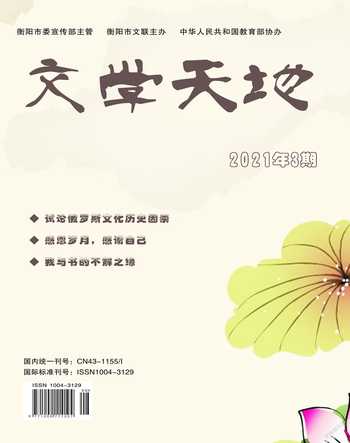田漢戲劇中的藝術家形象
摘要:田漢筆下的藝術家們既有著自己的藝術追求,也有著自己獨特的生命立場,他們追求的東西,往往看起來虛無縹緲不切實際,卻常常是高雅圣潔的精神世界,他們身上的那種精神,閃爍著那個時代的理想知識分子的影子。
關鍵字:田漢;藝術家形象;戲劇
田漢作為我國戲劇領域的改革者對我國戲劇事業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早在1927年,田漢創辦了南國社,為我國現代戲劇事業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戲劇人才。他在中國的現代文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為中國現代戲劇的三大奠基人之一,田漢創作了大量的戲劇作品,他在作品中塑造了許多藝術家的形象,包括琴師、詩人、演員等多種形象。
一、藝術家形象的分類
田漢戲劇當中藝術家們從事著不同的藝術形式,他們身上既有共同的精神特點,也有不同的人生追求。從他們對于生命、愛情、藝術的不同追求方面,我們可以把田漢戲劇當中的藝術家分成三類。
首先是對于藝術傳承和藝術追求有著執著堅守的藝術家。《名優之死》中的劉振聲注重戲德、戲品,對待藝術嚴肅認真,并精心培育了小鳳仙這樣的后起之秀。但是小鳳仙在小有名氣之后卻心猿意馬,“不在玩藝兒上用功夫,專在交際上用功夫”,成了流氓紳士楊大爺的玩物,背叛了先生為之嘔心瀝血的戲劇事業。劉振聲的失敗并不是單純的藝術家的失敗,更是那個時代想要在歷史潮流中逆流而上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的失敗,在這樣黑暗唯利是圖的環境下,任何純粹的藝術和理想追求,都只能是金錢的娛樂游戲。雖然藝術家的失敗是注定的,但藝術家身上的抗爭和覺醒更是田漢想要表現的核心精神,這種精神體現了二三十年代的時代主題,那就是對于封建傳統、封建勢力的批判與反抗。
第二類藝術家的形象是進行西方藝術表演的藝術家,他們既追求藝術,也追求愛情,卻往往在這兩種追求之中迷失自我,他們的生活往往漂泊不定,雖然衣食無憂,卻也無法享受生活的自由。《梵蛾嶙與薔薇》中琴師秦信芳是一個小提琴的琴師,每天的工作就是給演員柳翠伴奏,他自己對于藝術有更高的追求,想要去藝術的國家法國去深入學習樂器演奏,但身世悲苦,漂泊不定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與柳翠的日常相處中,與柳翠相戀。柳翠為了幫助秦信芳的留學理想,決定犧牲自己嫁給富商李簡齋作三姨太,以此來資助秦信芳的留學生活。但李簡齋其實是一個有情懷的人,他不但沒有娶柳翠作為三姨太反而促進了柳翠與秦信芳的愛情,還出錢資助了他們。
在這里秦信芳的藝術追求是不堅定的,愛情比他的藝術追求更加重要。他在藝術與愛情中掙扎游離,一方面想要完成自己的藝術理想。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能夠得到愛情的眷顧。秦信芳這一形象,更像是那些受到過新式教育但又無力反抗也沒有勇氣反抗的知識分子們,他們內心對于傳統的封建社會有著自己的反抗,但這種反抗又不完全徹底。
第三類的藝術家的形象是漂泊的詩人形象,他們在藝術和愛情的追求中,同樣去尋求自我的安定。他們身上有一種明顯地家國情懷,他們在漂泊中去尋求自我和藝術,愛情在他們內心當中是“白月光”。《南歸》中辛先生是一個四處流浪的詩人,在與戀人春姐相戀一年后回鄉,卻發現那早已不是記憶中的故鄉,在見過故鄉的物是人非之后,辛先生回尋春姐,在聽春姐的母親說春姐已經許人之后,辛先生重新踏上了漂泊之路。故事里的辛先生其實作者著墨不多,但卻表現出了一種漂泊之感,他在離開春姐的家重新踏上漂泊之路之前,把自己在樹上刻的詩劃掉,想要借此也擺脫掉自己和春姐在這段愛情當中的痕跡。他與那些在愛情和藝術當中糾結掙扎的藝術家們不同,他對于自己生命的追求有著強烈的堅持,即使后來春姐的母親說,他可以留下來一起生活,他也沒有認同,反而是平靜地迅速地離開了。藝術是他的伴侶,愛情只是流浪途中的一個驛站,卻不是歸宿。所以,他又走了,因為,詩人已確定自己的命運和使命。
二、藝術家形象中的“漂泊者”內涵
從 1920 年伊始,田漢筆下創作出的一系列的藝術家形象:秦信芳,顧梅儷、白秋英、名藝人劉振聲、詩人、辛先生。他們的心境會隨著“愛與藝術”的變奏而變化,但是,無論享有著愛還是失去了愛,無論對藝術的終極信念態度如何,是堅信不疑還是質疑動搖,他們心中不變的唯有 “孤獨與寂寞”,并如影隨形般的伴隨著漂泊者們的終生。這種感傷之情是與生俱來,是無法從心中排遣得開的,這都緣于他們共同的身世和身份:無家的孤兒。漂泊者們或者父死母亡,已無鄉可返;或父母還健在,或一方健在,但出于某種原因卻有家難歸,不能回家的游子形同孤兒。更重要的是,新的家園或正在建造中,或者,有一天發現,建造中的“家”僅僅是自己心造的“家的幻影”,他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漂泊者。流浪者只是沒有固定的家,但他們隨遇而安,走到哪兒,哪兒就是家;宗教教徒“出家”,但他們拋棄的是世俗之家,卻皈依了精神的教門;只有漂泊者才像無根的浮萍般漂泊,既無根,又無家。在這片美麗的國土上,沒有一處可供他棲身的居所,漂泊者如同一個孤獨的游魂,命中注定一生要在故國大地上不停地奔走、奔走,只為著尋求到“家”,因而,“家”的情懷便完全寄寓在“孤獨寂寞”的浩嘆之中;因而,抒發“孤獨與寂寞”之情便成為劇作家戲劇創造的重中之重。田漢劇作中為評論家們所稱道的那種獨有的“抒情性”便由此而生。每部劇中的每一位漂泊者(除《名優之死》中的劉振聲外),必定會在特定的氛圍中,不失時機地用大段大段的對白(獨白)傾訴著,為自己不幸的身世而唏噓嗟嘆,孤獨、寂寞、凄涼之情如滔滔江水,汩汩一瀉而出,反反復復,經久不息。田漢早期的劇作所抒發出來的悠遠綿長的深重的孤獨感,不是無人理解的思想者的蕭索,不是無人喝彩的藝術家的惆悵,而是漂泊者無家無根的凄冷,尋找返鄉之路而不得的痛苦。
我們返回到田漢出生成長的那個歲月,以歷史的高度審視,便會發現,這正是那個年代整個民族生存的真實境遇與情緒。田漢是“五四”一代人,“五四”時期,“大家族”遭解體,“孔孟之道”被打倒,年輕人紛紛離家出走,去尋求出路。“五四”這一代人被置于如此的境地:一方面是傳統的突然中斷、動蕩,激變;另一方面令人眼花繚亂的種種新主義、新思想紛至沓來。作為世紀的新生兒、時代的新生兒,“五四”這一代人由傳統文化哺育成人,卻已不能在傳統家園中安身立命,因為故園早已被拋棄;這一代人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新生的洗禮,但剛剛引入中國的外來文化,尚遠遠未在中國扎下根基。從根處說,他們成了無家的人。這中國從“古代國家”向著“現代國家”轉型以來,中國將向何處去?將建立什么樣的一個國家和社會?始終是高懸著的最大問題。
田漢在這樣社會環境之中,思考著中國人的出路,觀察著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藝術家們在這樣的處境下的艱難現狀,他仿佛看到傳統文化隨著中國社會的困境也處于了困境之中,他期待著也觀察者知識分子們的反抗和精神覺醒。
三、結語
田漢正是通過對于這些藝術家的悲劇命運的敘述,給我們展示了那個社會制度下的黑暗勢力和金錢勢利對于普通群眾的壓迫和腐蝕。他批判和反抗這樣的封建的社會制度,也對于對于新的理想知識分子的反抗與覺醒表達了贊美。
參考文獻:
[1] 田漢.田漢全集[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
[2] [1]馮麗珠.試論田漢早期話劇中孤獨的流浪者——以《咖啡店一夜》和《名優之死》為例[J].牡丹江大學學報,2019,28(08):63-66.
[3] [2]丁濤.論田漢筆下的“漂泊者”系列人物形象[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18(06):44-52.
[4] [3]張永忠.田漢早期戲劇創作中的女性形象[J].文學教育(中),2014(03):93-94.
作者簡介:鐘鎮(1993-),男(漢族),延邊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延邊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