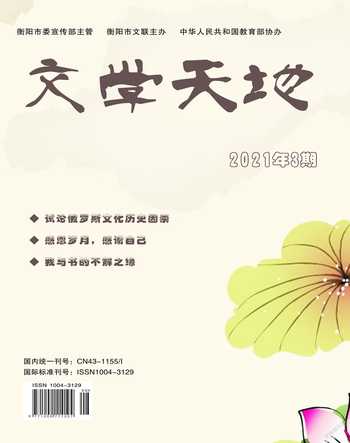淺談孔子天人觀,仁,禮的關系
顧春陽
摘要:天人關系問題是中國哲學最基本的問題,孔子是天人學說的開創者之一。圍繞著這個問題,演變出了一整套的社會倫理規范,他將仁義禮智信深深地刻進了中國人的血液中,時至今日,孔子思想已經深深地影響了每一位中華兒女。筆者將簡單介紹孔子的天人觀與仁和禮的關系。
一,性與天道
在中國歷史上,天有多種含義,歸納起來至少有三種:一,主宰之天(有人格神義);二,自然之天(有自然界義);三,義理之天(有超越性,道德義)。主宰之天與周的天命信仰有關,而自然之天與義理之天一脈相承。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天的作用是讓四季循環,萬物生養。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通史》中,認為孔子對天的看法“標志著有神論到無神論的過渡”。孔子這里說的“天”指的大自然。
我們所存在的這個大自然本身,就是所謂的天。在孔子看來天不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生命且不斷創造生命的,這就是所謂的“生”。而大自然在運轉中不斷地創造生命的過程,也就是“天道”,而這種天道的具體表現,就是創造生命的“生生”。
大自然的生命創造是向著完善的方向進行的,但“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中庸》)。也就是說天并不是完美的,正是因為天的不完美,所以才賦予了人能夠存在的意義:通過自身的行為來補足天道的缺憾。
這種行為由“性”來決定,性也是從天而來。“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
天命是上天賜予了人與生俱來的特點就是人的本性。人性大體相同,但有所差異。天命是一種功能,一個過程,“生生不息”就是天的‘言說’。人類應當傾聽天的言說,實踐天的言說,通過實踐去補足天。
如何實踐?“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我們在捕魚時,網的可持不要太細,要放過那些小魚,隔一段時間再上山砍柴,是為了讓樹木得以生長。這也是我們現在提倡續發展觀。大自然是一個生命整體,處于“生生不息”的過程中。天和人的關系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每一個生命都是天的一部分。
人應當敬畏天命,尊敬生命創造的過程。人可以為自然構建秩序,在建立文明的時候又不去破壞天下之生生。每一個生命都應找準自己的位置,“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當人與萬物真正能夠和諧共處的時候,這自然之天也就圓滿了。
二,仁
上天賦予了萬物以性,但人性不同于物性,上天賦予了人之所以為人的不同于萬物的性。這個性的屬性是善。
孟子的性善論的善,有更為復雜的內涵,而不僅僅只善良。
孟子還說人和禽獸沒什么兩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但是人有超越自身種類的普遍悲憫,人有突破生存本能的頑強意志,人有對自身存在的深切反思。這就是人與禽獸相比的不同之處,這就是人性之善。
這種特殊的人性之善可以概括為“仁”。“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 》)。人的仁愛必定有好惡,也有親疏之別,那這個好惡親疏的標準建在哪里?“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論語.顏淵》)。這個標準就是“知”。要實現“仁”,不僅要在情感上安于仁,也要在理智上利于仁,為的是避免盲目性。不能讓仁成為無原則的情感沖動或者受小恩小惠影響。仁與知必須統一,這是“心安而理得”的心之全德。
仁在行動上表現為“孝與忠恕”。儒家治理天下的方法論是修齊治平。凡是要從最基礎的做起。要實行仁,起點是處理好家庭關系,正所謂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孝是以家庭為起點把仁愛推廣至社會。
怎么做才是孝?“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庸》)。
最大的孝就是先人意志的傳承。愚公移山的故事家喻戶曉,起初山神嘲笑愚公,但愚公的子子孫孫無窮盡,移山的意志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水滴石穿,最終山海也能撼動。因此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古人特別重視香火的延續,無后就意味著意志傳承的中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是孟子提出來的,這是出于人倫的考量。舜帝的父母不喜歡兒媳,于是舜帝先斬后奏才告訴父母,孟子說這是在維護人倫(《孟子·萬章》)。為什么?因為有了孩子,就做到了最大的孝,這代表著香火得以傳承,舜的父母還再能說什么呢?
自古忠孝都是一體的,對父母是孝,對社稷則是忠。忠,并不意味著無條件的臣服。“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人與天相輔相成,人與萬物的關系是相互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相互的。只有君主對臣子有禮,臣子才有忠,同樣的,只有父母有慈愛,子女才有孝。
所謂忠恕,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將心比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才能夠由己及人。人人都有仁心,而不是個人的一己之心,只靠一個人是做不到的。這需要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相互尊重,因此,一套大家都認可的行為規范就誕生了,這就是禮。
三,禮
如果沒有仁,那么禮不過只是空洞的形式。“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孔子并不固執于“禮”的條條框框,他所強調的,始終是“禮”所體現出來的基本精神和原則:即禮是仁的外在表現形式。對于禮的內涵的解釋,顯然是孔子理想化的理解,這就是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因此,在宗教祭祀活動中,孔子更看重的是生者而不是鬼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古人認為人死后,子女要守孝三年。但孔子有個弟子叫宰我,他認為三年之喪太耽誤時間了,應該一年就夠了,孔子批判他“不仁”。為什么呢?因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論語.陽貨》)。子女要三年時間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守孝守的不是空洞的禮,而是為了同等的回報父母這三年之愛。使人養生喪死無憾,不正是一個社會的追求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慎終就是認真操辦喪事,追遠就是懷念遠代祖先。這種祭祀的目的不是祈禱鬼神,降福人間;而在于純正人心,教化生者。
把這種以人為本的精神放到國家層次上更為重要。“哀公問于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孔子家語》這里就回到了我們一開始說的“天命之謂性”,上天賦予人的使命就是通過自身的仁德來補足天道的不足,人要做的是天做不到的事情,人的生死存亡只能依靠自己。
參考文獻: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
蒙培元《孔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湯一介《儒學十講》,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
王肅《孔子家語》,北京,中華書局,2014
王苗苗《孔子天命觀研究》,文化學刊,2021年第2期
張立璟《析孔子思想中的“仁”》,湖北工程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
(浙江樹人大學 ?浙江省杭州市 ?31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