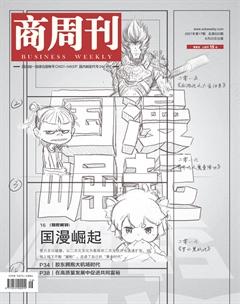超市的黃昏靜悄悄
謝易蓁



對于永輝們來說,它們的身家性命都成了別人的流量入口,多年的積累被摧毀。而對于那些“降維攻擊”永輝的公司來說,當它們的生意也被納入到一個更大的宏觀敘事中時,被抹去也不需要太繁瑣的過程。
在過去的18個月里,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先苦后甜”——先遭遇疫情考驗,再享受戰疫勝利。但有一大批公司的經歷卻恰恰相反——疫情期間它們逆勢雄起,疫情過后反而陷入了困境,可謂先喜后悲。
比如順豐,疫情期間大量商業航班停飛,擁有75架全貨機運力的順豐傲然立于快遞業內,其2020年上半年營業收入逆勢大增42%。但疫情過后,主動下場參與價格戰的順豐爆出巨額虧損,讓人大跌眼鏡。
教育行業是更典型的代表。疫情期間網課大為普及,無數線上教育公司都坐享“宅家”紅利,股價動輒幾倍漲幅。但疫情過后沒多久,教育培訓全行業遭遇政策調整,曾經的超級牛股紛紛掙扎在崩潰邊緣。
這些崩塌轟烈而輝煌,向來能夠占據頭條熱榜,但還有一些我們平素里耳熟能詳的公司,卻在靜悄悄地滑向深淵。
比如曾經遍布大小城市的“大潤發”超市,在2019年仍然位列中國超市百強榜第2位,但其母公司——港股上市公司高鑫零售,疫情期間股價短暫接近歷史新高后便一路陰跌,市值自高點已縮水62%。
而排在中國超市百強榜第3位的永輝超市,基本上復制了高鑫零售的軌跡。其在2020年4月份市值達到頂點之后,股價也一路向南,陰跌不已,曾經超過千億的市值目前也只剩下了400億左右。
大型超市在疫情前期的上漲可以理解。2020年上半年疫情肆虐,菜市場、農貿市場紛紛關閉,但大型零售超市因為要承擔穩定食品供給、確保社會安定的作用,關店影響有限,部分超市的生意反而更好。
但疫情平穩之后,兩家公司的業務急轉直下。今年4月永輝超市披露一季報,凈利潤同比下降了98.51%,市場一片愕然。三個月后永輝董秘張經儀,在他發的幾百字朋友圈里,媒體檢索到了關鍵詞:
我們正在下山。
公司如果步行下山,那么持股的機構一定會乘滑翔傘下山。高鑫和永輝都成了機構砍倉的對象,就連興全老將董承非旗下兩只基金也是一只幾乎清倉,一只減持比例高達42.7%,并直言自己“看錯了”。
相比之下,海外超市巨頭沃爾瑪和Costco在美股市場勢如破竹,一路創新高,前者市值高達4000億美元,體量不差阿里多少,而后者市值也逼近了2000億美元,接近京東或拼多多的兩倍。
為何中美超市的巨頭們命運如此不同?永輝和大潤發這一年多的時間到底發生了什么?為何它們抗住了電商十幾年的輪番沖擊,股價甚至在疫情初期創下新高,但在之后的一年里卻連續崩塌?
本文將以永輝超市作為主線,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生鮮:難啃的骨頭
關于超市,有兩個相對比較冷的知識。
首先,超市是一個薄利甚至微利的行業。沃爾瑪的毛利率常年在25%上下,凈利率5%左右,要知道這已經是行業最頂尖的水平。一般來說,超市的毛利率往往也就10%-15%,凈利率只有2%-3%。
換句話說,超市是一個典型的靠規模吃飯的生意。在美國,包括沃爾瑪在內的前三家超市品牌占據了近80%的市場份額,成功把超市做成了收稅型生意。Costco雖然有意把毛利率壓低到10%,但憑借著豐厚的會員費收入,利潤也是一個天文數字。
而在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超市又是一個典型的“大市場、小公司”型的生意,市場前三加起來還不到10%的份額,大概率可以入選國家反壟斷局免檢單位。
另一個冷知識是,永輝超市主營的生鮮,更是一個苦活累活。
1995年,一個叫張軒松的福建男人在福州開了一家名叫“古樂微利”的小超市,別人毛巾賣3元,他只賣2.3元。靠著這種“微利”特色,3年后,張軒松在福州火車站又開辦了第一家以“永輝”命名的超市。
時值麥德龍、沃爾瑪相繼入駐,當地龍頭新華都聲勢浩大,剛當上資本家的張軒松心急如焚,跑到各個超市去調查,發現了兩件重要的事:
第一,外資超市和內資超市最大的區別在于,外資超市會賣生鮮;第二,雖然外資超市賣生鮮,但福州老百姓買菜還是去農貿市場。
老百姓愿意去菜市場的原因也很簡單:東亞人對食物“鮮”的追求冠絕全球,魚要鮮活的,雞要現宰的,前有壽司里對食材的苛刻要求,后有相聲演員于謙的父親每天必吃的“豬大腸刺身”。
初到中國的外資超市大多賣的是冷凍肉,蔬菜也多為保鮮期更長的根莖菜,在中國人看來,再便宜也沒有菜市場的活魚活蝦香。
2000年7月,張軒松開出了福州第一家專業化生鮮超市——永輝屏西生鮮超市。生鮮商品的經營面積達總面積的50%-70%。為了配合福州人買菜的習慣,張軒松專門把開門時間也提前到6:30。
生鮮在超市的缺位,有老外不了解中國國情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對超市而言,生鮮往往是一門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生意。
首先,生鮮損耗率非常高。相比日用百貨,生鮮的保鮮期非常短,大部分葉菜上架后只能售賣一到兩天,否則就會蔫掉,肉類的保鮮時間稍長,但不新鮮了就很難賣掉。如何控制損耗率,是一門地獄級難題。
其次,生鮮的物流成本高。生鮮運輸往往需要全程冷鏈。如今淘寶賣家從義烏、溫州發全國,物流費用低到1元就可以搞定。但是,生鮮就算只用泡沫箱、干冰或冰袋進行控溫,成本最低也需要6元左右。
最后,供應鏈管理難度極大。不同品種的生鮮所需的溫度、濕度是不同的:比如香蕉放在12℃以下環境中容易發黑腐爛、鮮荔枝在0℃的環境中容易變味、番茄黃瓜柿子椒需要10℃的環境、白菜芹菜蘋果桃子則適宜在0℃保存、葉菜類的保鮮濕度是95%-100%,果菜類是90%-95%,根莖類是70%-80%……
這里面的每一個變量,都是管理成本。而供應鏈管理不善,輕則影響成本管理,重則危及品牌聲譽:今年6月,河南焦作的一家永輝超市居然將死魚擺上貨架,并以“仰泳魚”的名字堂而皇之的售賣。
種種因素導致的結果,就是生鮮利潤空間小,標準化難度極大。
以水果為例,就算是產自同一個區域,因種植的農人不同,種在山的陰面、陽面不同,水果大小、甜度、含水量、光澤都有差別。就算能夠形成品牌,但考慮到生鮮消費群體對價格的極端敏感,也很難做出品牌溢價。
盡管有種種缺陷,但生鮮卻有一個很多消費品類無可比擬的優勢:剛需+高頻。
在中國,自己買菜做飯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執念。而對一個農業人口超過1/3的國家來說,生鮮的每個環節幾乎都與民生大計息息相關,也就注定這個行業不會缺少中央的引導、政策的支持。
這種引導、支持和關懷,發生在永輝超市開始賣生鮮的第二年。
崛起:供應鏈奇跡
永輝模式誕生的契機,是2001年前后開始推動的“農改超”工程:時值農貿市場設施簡陋、管理粗放的影響逐漸顯露,“黑心米”“瘦肉精”“注水肉”等食品安全事件在世紀初的高發,引起了決策層的擔憂。
由于攤販和農貿市場只有承租關系,農貿市場本身沒有監管的動力和能力,但超市作為品牌和大型公司,自我約束力通常相對更強,對消費者來說,雖然不喜歡東西貴,但更怕東西來路不明。
永輝超市瞬間成了典型,被國家七部委譽為中國“農改超”的開創者,開始接手福建地區的農貿市場改造工作。“農改超”開展三年后,永輝超市門店數量已達50家,集團營業額達20億元,躍升福建老大。
2010年12月,永輝超市在A股掛牌,被稱為“商超生鮮第一股”,增速迅速坐上了火箭。
但同一時期,“農改超”的發展卻難言順利,在后來的種種爭議聲中,政策開始逐步轉向鼓勵過渡式的“農加超”。
其本質原因在于,中國人去農貿市場買菜的習慣往往是“少量+高頻”,但大多數“農改超”而來的超市,其設計初衷往往是“大量+低頻”。另一方面,經營的生鮮品類越多,損耗控制難度就越大,導致生鮮超市往往沒有價格優勢。
永輝能堅持下去的秘密在于:一是讓消費者在買低毛利生鮮的同時,順便買點高毛利商品;二是想盡一切辦法,壓低生鮮上游的供應鏈成本。
永輝超市的生鮮毛利只有14%,但其綜合毛利率卻長期維持在20%以上。很顯然是因為更高毛利的商品拉高了綜合毛利率。用剛需+低毛利的生鮮引流,再用高毛利的商品拉高營收,完全是一套互聯網的打法。
但這種俗套打法,對于生鮮營收占比高達50%的永輝超市(高鑫零售為19%,沃爾瑪為25%)來說,依然是不夠的。
利潤還是要從供應鏈中摳出來。其實無論是超市還是農貿市場,其背后都是一套由菜籃子工程奠定的生鮮供應鏈體系:農戶-合作社/基地-一級批發商-農產品批發市場-二級批發商-零售端-消費者。
安信證券曾做過一次調研,在上海市場賣9.8元/斤的陜西蘋果,在陜西當地農戶只賣3.65元/斤,兩者之間的差價就讓批發商和倉儲物流賺走了。
在決策者眼里,這是維系就業民生的鏈條;在消費者眼里,這是層層加價的空間;在永輝超市眼里,這都是可以壓縮的成本。
和超市“大市場、小公司”的特點一樣,中國農產品的最上游同樣是“大市場、小生產”,在收購商/批發商面前,分布極為分散的農戶和超市基本沒有議價權,基本就是散戶和主力的區別。
作為最下游的超市,永輝一度利用規模優勢直接繞開批發商與批發市場,用“藥品集采”的套路奪取議價權,但這種方法的缺陷是,非常容易被別人模仿。
于是從2014年開始,永輝通過合資和入股的方式,逐漸綁定上游供應商,實現與上游的利益鎖定——既然要坐莊,不如大家一起坐。
在中游加價最嚴重的運輸轉存環節,永輝的做法是自己建物流配送中心,這種方案的缺點是前期投資巨大:比如成都的物流配送中心總投資高達1.2億元;但好處是給一個店供貨成本是1.2億元,給十個店供貨成本也是1.2億元。只要不超過該物流中心的最大承載力,多供一家店就是多一筆純利潤。
而在下游損耗最嚴重的銷售終端,永輝在2015年內部孵化了食品供應鏈品牌“彩食鮮”。這個業務可以理解為一個To B的生鮮加工廠,對于公司采購團隊來說,可以根據產品質量把品相好的生鮮放在定位高端的超級物種和永輝綠標店,品相一般的放在紅標店賣,品相差的交給彩食鮮加工處理,賣給B端商家。
從最上游的采購、到中游的運輸倉儲、再到下游的分類銷售,對供應鏈成本的極限壓縮,反映在終端就是能把生鮮價格賣的比菜市場還低,而通過低價做大用戶規模,又能進一步推動上游成本的壓縮,繼而讓門店穩步擴張。如果一切順利,一個中國版的沃爾瑪似乎在冉冉升起。
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改寫了劇本的走向。
肢解:存量的切割
過去幾年里,生鮮超市能在電商沖擊中存活下來、甚至活得越來越好的最大籌碼在于,生鮮是一個很難被線上化的品類。要知道強如順豐,也是在成立了24年后,才摸索出如何運送一顆櫻桃。
生鮮易壞高損耗的屬性,加上供應鏈的極端復雜,再疊加即時配送帶來的成本,讓燒了好幾年錢的生鮮電商仍然只能占據3%的市場份額。無論有多少優勢,對于“真實中國”來說,生鮮電商的體驗遠遠比不上拼多多橫空出世帶來的震撼。
每日優鮮創始人徐正比較實在,他對生鮮電商行業這樣評價:
撅著屁股撿鋼镚。
而以盒馬鮮生為代表的“店倉一體”模式,也很難解決供應鏈難度與配送成本的問題。很多省會城市的消費能力卻只能支撐一兩家店。
在其他領域的互聯網公司都在瘋狂下沉的今天,盒馬的快捷與便利似乎難以打動三四線城市那些時間充裕、價格敏感、習慣把逛菜市場當消遣的消費者。
真正在供應鏈上搞出降維打擊,繼而對生鮮超市產生威脅的,是“社區連鎖生鮮店”。
一類是以把“不賣隔夜肉”寫在門頭上的錢大媽為代表。它們一方面主攻單品,標準化空間大大提高,供應鏈管理難度也指數級降低;另一方面,跟喜茶差不多大的門店面積,比起上百個員工的生鮮超市,擴張起來非常快。
另一類則是區域地頭蛇,以在安徽占山為王的生鮮傳奇為代表。單單在合肥市,生鮮傳奇就有100家門店,而其他“友商”的門店加起來還不到80家,做成了生鮮領域的茶顏悅色。
由于門店密度極大,除了離消費者更近,更重要的是供應鏈的縮短,無論是地方版的“生鮮集采”,還是運輸距離的縮短,帶來的同樣都是供應鏈管理難度的指數級降低。
究其根本,生鮮更像是一個“在存量中尋找增量”的生意:在中國做生鮮生意,比起穩步擴張成為寡頭的天方夜譚,更實際的做法往往是在已有的存量市場中,尋找優化供應鏈結構,提高毛利率的方法。
上述對手各有絕招,但永輝們尚能應付。真正給永輝超市致命一擊的,是在疫情中逆勢崛起的社區團購。
由于餐廳、菜市場和農貿市場因疫情停業,生鮮超市成了保障居民日常餐飲為數不多的選擇。但更重要的是,疫情又是一場大型“網上買菜”普及教育,生鮮電商公司在在疫情期間GMV數據紛紛飆漲,并終于催化出了一種能夠極具優勢的模式——“興盛版”的社區團購。
在做社區團購之前,興盛優選已經是一家長沙本地的零售巨頭,擁有一張便利超市網絡——芙蓉興盛,旗下的門店大都是夫妻老婆店改造而來,面積30-80平米,店主起早貪黑,賺點兒辛苦錢。興盛基于自家的這張網絡,而不是開新店來做社區團購,成本自然極低。
興盛做社團團購的第一步,就是把這些傳統零售店的“店長”,變成社區團購場景下的“團長”,讓他們憑借著對社區的熟悉來拉附近居民“拼團”,通過“預售+自提”的方式來銷售零售店里沒有的品類商品,而興盛則負責提供背后一切的供應鏈和技術等基礎設施。
成本低(沒有自建實體店負擔+自提降低物流成本)、損耗低(預售模式降低庫存壓力)、流量支出低(由團長線下招攬顧客)、使用方便(微信小程序)、利益分配好(能夠大幅提升團長的收入),最重要的是,社區團購的定時配送解決了生鮮電商最頭疼的問題——即時配送的高成本。
隨后,社區團購像野火一樣瘋漲起來,并迅速引來眾多互聯網公司“抄作業”。
一旦互聯網巨頭攜帶大量資本入場,這場戰爭的硝煙味兒就驟然濃郁起來,巨頭們一邊沿著興盛優選的模式來四處搶團長,一邊用扶貧價吸引流量,比如0.01元/斤的大白菜,5毛錢一把的金針菇、0.99元/盒的雞蛋、3塊錢10斤的橙子,迅速收獲大批用戶。
對于社區團購這門生意,消費者看到的是1塊錢一盒的雞蛋,巨頭們看到的是繞開中間環節,重構商品流通渠道。賣菜只是作為社區團購引流動力:興盛優選一開始以生鮮品類的爆品做引流,后期逐漸推出酒水飲料、母嬰百貨拉動利潤。隨著商品品類逐漸增加,平臺也會徹底掌握價值鏈條的話語權。
換句話說:那些對永輝來說是身家性命的東西,對巨頭來說只是一個流量入口。名創優品的創始人葉國富曾經一針見血的指出這種殘酷性:“社區團購再干一兩年,500平方以上的超市基本上沒戲了”。
就差直接報華潤萬家、大潤發和永輝超市們的身份證了。
泥淖:彷徨的反攻
對于種種威脅和憂患,永輝并非沒有應對。
旗下超級物種對標阿里旗下的盒馬鮮生,曾被業界寄予厚望。2017年,騰訊傾情投資,占股15%,欲扶持其與阿里對峙,并定出了開店100家的目標,但實際開店數量在不斷減少,2018年46家,2019年15家。2021年2月,據多家媒體報道,超級物種將關閉除福州外的所有店鋪。
業態類似便利店的永輝生活,一度打出過“家門口的永輝超市”的旗號,同樣經歷了高調成立、大幅擴張,關店調整的拋物線。此外,試水中型超市業務的永輝mini,依然難逃大面積關店的命運。
一系列創新業務中唯一相對發展不錯的,是對標生鮮電商的到家業務:2020年,到家業務實現銷售額59.1億元,同比增長147%。同期,每日優鮮、叮咚買菜的營收分別為61億元、113億元。看起來到家業務好像可以與新玩家們一搏。
但實際上,永輝到家面臨著更加復雜的業態融合。
相比生鮮電商的“前置倉發貨”模式,永輝到家業務的發貨地更加復雜——既有超市門店、mini店,也有獨立的“前置倉”。這種規劃看起來很好——既能加快門店的商品周轉,又能避免前置倉模式的巨額虧損。
但在實際運轉中,線下的生鮮都是散裝,轉到線上還要再次稱重、分裝,結果往往是買菜高峰期線上線下難以兼顧。線下超市POS系統和進銷存系統,融入到家業務時,還要將線上和倉庫商品庫存同步到電商交易系統。其負責人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兼具線上運營和門店運營很困難。同時要照顧到線上生意和配送生意更困難。
還有一個在業界廣為流傳的例子:永輝曾經嫌超市后倉分揀太慢,于是想抄“店倉合一”的盒馬的作業。但是測量下來,發現自家店的層高大部分都不夠,沒地方裝懸掛鏈,只能作罷。
另外,盒馬后倉面積占到整體店面的三分之一,傳統商超的后倉面積僅會占到十分之一。如果永輝想要通過改造已有店面,擴大后倉面積,那就縮小前店面積,也就勢必會影響既有的商超業務。
很多時候改革做不下去,就只有一條原因:既要照顧舊的,還要開拓新的,神仙都做不到,何況臣妾呢?
更重要的,生鮮作為一種“高頻+剛需”的消費品,注定了其受眾對價格的極端敏感,這又導致即便形成了生鮮品牌,也幾乎沒有任何產品或功能上的溢價,客戶太容易叛逃,很難形成真正的品牌效應。
薄利甚至微利的特征,讓永輝超市靠著十多年來的規模優勢與精細運營,才換來了1%-3%的利潤率。面對不惜承擔幾十甚至上百億虧損押注社區團購的互聯網巨頭,永輝遇到的遠遠不是“怎么轉型”的問題。
2007年,科恩兄弟導演的電影《老無所依》上映,片中手持空氣炮的殺人狂魔安東有一句臺詞:
如果你遵守的規則把你帶到了這幅田地,你的規則還有什么用呢?
如何去適應財大氣粗的互聯網巨頭們塑造的新的商業規則,如何去面對一個正在被燒錢、“優化”和內卷定義的商業世界,似乎也是一大批發跡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企業家遇到的問題。
他們的溫文爾雅也好,囂張跋扈也罷,在內卷的商業世界里的生存空間,正在逐漸被壓縮。
這批企業家大概能夠分成兩類,一類可以叫做“功成身退的人”:比如陳天橋,在騰訊阿里戰略露出頭角時離開盛大,旅居美國投身生命科學研究投資。比如段永平,早早退休全職投資,閑云野鶴。
另一類叫做“不愿下牌桌的人”,比如蘇寧張近東。而在超市行業也有一個現成的例子:2013年,大潤發推出電商平臺飛牛網,董事長黃明端豪言“要玩就玩大”,現在還有幾個人聽說過這個網站?
當然,更諷刺的是《老無所依》的結尾:
不守道上規則的殺人魔安東,開著一輛車在馬路上乖巧地等紅綠燈。綠燈后,安東平穩地開著車過路口,結果被一輛闖紅燈的轎車撞了個頭破血流——靠不守規矩崛起的人,必然有另外一個無視規矩的局來等他。
對于永輝們來說,它們的身家性命都成了別人的流量入口,多年的積累被摧毀。而對于那些“降維攻擊”永輝的公司來說,當它們的生意也被納入到一個更大的宏觀敘事中時,被抹去也不需要太繁瑣的過程。
在商業的每一個角落,黎明總是靜悄悄的,黃昏也總是靜悄悄的。
(據遠川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