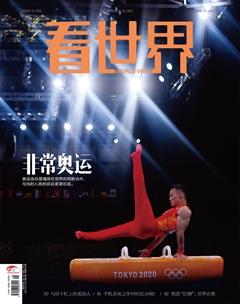西歐洪災暴露預警機制漏洞
葉晟
2021年7月15日,比利時列日遭遇洪災
7月14日起,西歐部分國家下起大暴雨,洪水在西歐平原泛濫肆虐。截至7月下旬,洪災已造成至少189人死亡,近千人下落不明,特別是德國西部的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已有110人死亡,670人受傷。
德國氣象專家稱,這是“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是德國戰后遭遇的損失最慘重的自然災害。
與此同時,德國迎來了風云變動的時刻,德國大選將于9月舉行。這意味著執政了16年之久的默克爾即將退出歷史舞臺。而德國政壇的明日之星仍未有定數。
大選之年與百年一遇的大洪水相遇,救災現場淪為政治舞臺。在波譎云詭的政治場域,科學應對洪災以及氣候變化,成為政治家們換取選票的“籌碼”。
洪水泛濫,政客必爭
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災難。
根據當地氣象部門數據,在7月14—15日,位于德國中部的維伯費爾特遭遇強降水,成為這次西歐極端降水的中心:1小時最大雨量達到23.7毫米,24小時最大雨量162毫米,過程累計雨量182.4毫米。波恩—科隆測量站雨量最大,最大日雨量88.4毫米,3日過程累計雨量98.6毫米,打破了該站的歷史紀錄。
由于德國在早期已經歷了長達半個月的陰雨天氣,泥土含水量飽和,遇到強降水容易發生洪水以及地質災害。
洪水所經之處,房屋坍塌,殘垣斷壁隨處可見。街道被水淹沒,汽車漂浮在街道中,電力和下水道系統被破壞。面對著被洪水破壞的家園,民眾只能以淚洗面。
德國當局表示,在德國遇難的人數中,有90多遇難者曾居住在西部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的阿爾河流域的城鎮和村莊。當地政府為受災嚴重地區需要物質或心理支持的市民設立了熱線,并呼吁社會各界提供設備,援助救災地區,提供基礎設施以及清潔飲用水。
目前,西歐地區的洪水正慢慢消退。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在7月17日視察災區時,形容這場洪災是“巨大悲劇”。德國總理默克爾分別于7月18日與20日前往本國受災最嚴重的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和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7月20日,她承諾將為受災地區提供及時援助,并將在國家層面制定一個長期性的重建計劃。
2021年7月18日,德國巴特諾因阿爾-阿爾韋勒,洪水過后,淤泥、垃圾遍布街道
德國乃至歐盟主流人士都將洪災與氣候變化“掛鉤”。
作為德國的鄰國,比利時也成為了此次受災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截至7月17日,比利時因洪災造成的死亡人數已上升至27人,失聯人數為103。
此外,瑞士、荷蘭和盧森堡等國也受到此次強降雨影響。此次洪災雖然是天災,但系列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等嚴重后果,都深刻地反映了一個嚴峻的問題:西歐多個國家是否在洪災來臨前,做好了充足的應對準備?
反思氣候保護
德國多名領導人以及歐盟領導人一致認為,造成此次西歐大范圍洪災的主要原因為氣候變化。施泰因邁爾表示,等洪水過境,需要對氣候變化采取更堅決的行動,這將會是控制極端天氣的唯一方法。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則稱,歐洲西北部的洪水警示著,需要采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
在訪美期間,默克爾和拜登簽署了一項協議,其中涉及“采取緊急行動解決氣候危機”的承諾。歐盟在7月14日前公布了一項名為Fit for 55的計劃,旨在到2030年,歐盟碳排放量減少55%;在2050年前實現歐盟碳中和。
一天后,波及德國、瑞士、荷蘭和比利時的大范圍洪水來襲,環保活動人士和眾多政界人士將這場災難與氣候變化的影響進行了類比。德國乃至歐盟主流人士都將洪災與氣候變化“掛鉤”。
2002年,德國發生“ 世紀洪災”,時任總理施羅德(左)穿膠靴走過易北河邊的泥濘街道
洪水預警系統的好壞都取決于其最薄弱的環節。
世界氣象組織對此表示認同,認為今年全球極端洪水、高溫和火災多發,與氣候變化不無關系。
但正如德國公共電視臺在社論中所說,“天氣是政治性的”,當洪災遇上大選年,氣候變化問題就被推到了德國政治舞臺的中心。評價當局在大選前應對洪災的表現,成為了德國政壇各黨派爭取民心的“籌碼”。
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主席拉舍特是本次大選的熱門候選人,被稱為默克爾的“接班人”,他同時也是在此次洪災中受災最嚴重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州長。
當拉舍特被問及“洪災的發生是否會促使他對氣候變化采取立場”時,他對主持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回答道:“我是州長,不是活動家。”他說:“我們經歷了這樣的一天,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政治。”
但歷史給出的答案是,無論天災還是人禍,都將改變政治的走向。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嚴重核泄漏后,默克爾決定吸取教訓,將徹底關停德國境內核電站的決定提上日程,哪怕會為此付出24億歐元的賠償。福島核泄漏的災難,促使默克爾將目標關閉日期從2033年提前至2022年,同時增加了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
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家托爾斯滕·法斯認為,在未來兩個月里,世界上某個地方總會出現極端天氣事件,而焦點將集中在萊茵蘭—普法爾茨和北萊茵—威斯特法倫的災難之后。極端天氣這個話題將貫穿整個德國競選活動,并起決定性作用。
2021年7月16日,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市民圍觀洪水過境
事實上,在德國的政壇歷史上,洪水對德國的政治競選產生過關鍵的影響。2002年,德國易北河溢流,發生了“世紀洪災”,造成81人遇難。
在救災時,德國時任總理施羅德身穿膠靴穿過易北河泥濘街道的照片,可謂“秒殺”了當時處于度假狀態的、來自保守派的對手。施羅德最終在大選中擊敗對手,成功連任。
7月15日,拉舍特以類似當年格哈德的裝扮現身重災區哈根,并會見了當地市長以及消防人員。他表示:“我們不會讓這座城市孤立無援,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將團結一致。”
而拉舍特的最大競爭對手,來自綠黨的候選人安娜萊娜·巴博克,在洪災發生后馬上縮短了假期,并前往萊茵蘭—普法爾茨的受災地區。她呼吁馬上對受災民眾進行援助,也呼吁保護好居民區和基礎設施免受極端天氣影響。“我們需要加快步伐,采取有效的氣候保護措施,立即實施氣候保護計劃。”巴博克說。
完善洪災預警系統
歐洲洪水預警系統(EFAS)負責觀察洪災發生的預兆,并向每個受影響國家的相關部門發送了信息。德國氣象局發言人表示,當局在洪水發生的早期,就將洪水警報傳遞給了負責啟動疏散或現場其他預防措施的地方政府,而不是聯邦政府。
此次發生在德國、比利時和荷蘭等國的洪災,給人們帶來一個教訓:未雨綢繆。在洪水發生前采取行動,更容易、更低成本、更有效,這是應急人員長期以來的共識。氣象部門能夠提前幾天時間掌握天氣變化情況,并發布天氣警告。
這并不是說這些國家應該受到譴責。其他國家的預警系統也可能會出現漏洞。但很多部門往往“不見棺材不落淚”,出現了巨大損失,才意識到改進完善相關機制的必要性。
正如“木桶理論”所表明的,洪水預警系統的好壞都取決于其最薄弱的環節。如果在采取行動時不認真聽取預警信息,那么哪怕再精確的預測也無法發揮其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行動不力可能有三個主要原因:要么是信息有誤;要么是信息沒有傳遞給正確的部門;要么是信息傳遞到相關部門后不被相信。實際上,造成這次西歐的洪災泛濫,可能是三種情況的綜合作用。
預警系統并不是完美的,其存在的意義只關注天氣狀況,具有局限性。兩天內150毫米降雨量的警告,對大多數人來說并沒有多大意義。真正重要的,是根據天氣變化細節來發出警告,例如“河流水位將迅速上升,將導致大面積洪水,預計會對道路和財產造成損害”等信息。這通常被稱為基于影響的預測。
2021年7月15日,比利時列日,居民撤離住所
2021年7月15日,比利時韋維耶市,被洪水沖過后的車輛
要完善預警系統以及更新全社會對災難信息的認知,往往需要一次重大事件。
還有一種合理的擔憂是,如果過于頻繁地發出警告,而沒有產生影響,它們將逐漸被忽視。所有這些,都可能導致人們傾向于等到下一次預報更新后才發出警告,這減少了采取行動的寶貴時間。
由此可見,盡管科學技術已取得巨大進步,但洪水預警的傳播方式仍有待加強,且執行應對政策以及告知公眾的職責,需要落實到位。
歐洲應急系統的支離破碎,不同國家部門各自為政,為本應時間充裕的預防措施帶來困難。事實上,歐洲部分地區的居民,直到家里被洪水淹沒才開始撤離。
洪水預警是洪水風險管理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確保正確的人在正確的時間獲得正確的信息,生命才能得到拯救。
然而,在各地修建防洪系統是不現實的。單靠警報系統,并不能減少洪水災害帶來的所有不利影響。防洪系統對于保護城市地區安全來說至關重要。
當地還應該建立更有彈性的社區,在人居環境附近應該要有足夠的水空間,盡可能使洪水過后當地水勢迅速干涸,并保證當地居民有正常的居住環境。
提高公眾的洪水風險意識也非常重要。需要建立全社會對預測結果的信心,確保每個參與預報信息鏈的人,從天氣預報員、水文學家、決策者和當地社區,自設計洪水預警系統開始就參與其中。
此外,還應公開討論預測模型的優點和局限性,以便不斷完善系統。這個過程越來越多地被稱為“聯合制作”。這種綜合方法可以提前做出決定以平衡風險,而不是一時沖動。
要完善預警系統以及更新全社會對災難信息的認知,往往需要一次重大事件。某種程度上,此次西歐洪災可作為“催化劑”,為歐洲以及國際災害管理界提供一次寶貴的機會,來反思全社會對極端天氣的預警、預防工作的完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