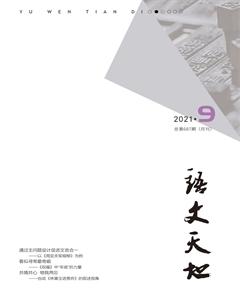《祝福》寫作解讀
求潔
在魯迅作品的教學中,我們一般是側重于文章主題思想的聚焦,即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黑暗社會現實的揭示。但由于魯迅作品時代背景較久遠,學生個人經歷、經驗有限,情感理解能力不高,學生在學習語文作品時尤為畏懼接觸周樹人先生的小說。筆者認為,如果語文教學中能輕主題思想挖掘,重魯迅文本的寫作分析, 或許能讓學生走進文本,消除畏懼感。現以小說《祝福》為例,尋求它對學生寫作的啟示。
一、依據主題選擇題材
寫作構思時,主題決定題材,主題相異,作者須挖掘更多精彩題材來展示主題。魯迅先生在探討其寫小說的原因時曾提到,在寫小說的前10年,始終抱著“啟蒙主義”理念、“為人生”理想來構思文章,試圖將這些內容滲透到作品中以引導改良“這人生”。也正因為有此觀念,魯迅極為痛恨小說的別號,為改變這種小說歧視,他特地擴大了小說取材范圍,納入了病態社會的底層困難民眾。《祝福》就是這樣一本小說。《祝福》旨在突出沒落封建禮教肆意殘害民眾,人情冷漠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狀。為了恰當有效地表現這一主題,魯迅先生選取了魯鎮這個他熟悉且不起眼的封閉小鎮,鎖定了祥林嫂這樣一個受封建禮教殘害致死的小人物,詳細介紹了她多苦多難的人生。原本生活在衛家山的女人祥林嫂在丈夫死后,被婆婆算計出賣。為保護自己,她拼命逃脫,來到魯鎮魯四老爺家尋獲了一份工作。然而,受封建社會思想影響,她在做工過程中備受虐待,每天的日子苦不堪言。一段日子后,她還是被婆婆找到,并被帶回家被迫與賀老六成親。不久,祥林嫂誕下了兒子阿毛,日子過得安穩了些。但這種安穩并沒有維持多久,由于長期受地主虐待,祥林嫂的新丈夫賀老六身心俱疲,最后死去,其子阿毛又被狼吃掉了。一重又一重的打擊讓祥林嫂難過不已,但周圍人不但不安慰她,還指責她克夫克子,要她捐贈門檻為自己贖罪,避免之后“在陰間”飽受苦難。為了不“在陰間”受苦,祥林嫂想盡辦法攢錢,買了門檻捐贈。盡管如此,人們依然歧視她,最終窮困潦倒的祥林嫂在除夕夜的鞭炮聲中凄慘地離世。這種結局,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主題。這告訴我們,在寫作中,應先確定主題,然后依據主題需要來選取題材,不求“高大上”, 但求恰如其分。
二、借敘述技巧增強表現力
小說本質上是在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否采用了合適的敘述技巧在某種程度上直接決定了故事主旨的呈現效果。目前,故事描寫可應用的敘述技巧相對較多,敘述方式和敘述視角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從敘述方式來看,順敘固然會脈絡清晰,卻易流于平鋪直敘,缺乏吸引力,插敘、倒敘等均能有效地彌補順敘的不足。《祝福》在倒敘方式的基礎上引入了插敘方式,實現了故事的層層套嵌。比如,“我”回魯鎮觀看傳統祝福禮時插進了昨日巧遇祥林嫂之事;“我”準備明日離開時,聽聞四叔抱怨祥林嫂這樣的“謬種”的死訊破壞了祝福禮的氛圍;祥林嫂突然間的失蹤制造了懸念,引出她與賀老六短暫的安穩生活,以及阿毛被狼吃掉對她造成的永久傷痛;祥林嫂再次來到魯鎮受到冷遇和歧視,被四叔家打發走,流落街頭,慘死在除夕的熱鬧之中。整個故事既有主線時間的延續,又有副線情節的補充解釋,一主一副相互映襯,每個情節環環相扣。讀者閱讀時通過抽絲剝繭,逐步解讀,逐漸感受到文章在敘事方式上強大的吸引力。 在敘述視角上,魯迅先生借“我”的眼看魯鎮發生的一切,包括祥林嫂的命運,又借魯鎮人的眼看祥林嫂的一生,形成了雙重看客模式,這種敘述視角是“我”和魯鎮人“共同見證”祥林嫂的悲慘命運,“我”和魯鎮人都是祥林嫂的看客,又都對她的命運產生了影響。當祥林嫂帶著一絲希望,向“我”這樣一個識字人詢問人死后是否有魂靈時,“我”的猶豫不決、關于人死后“說不清一家人能否見面”的話語壓垮了祥林嫂,使之希望徹底地被摧毀了,增加了她的精神恐懼,同時也加速了她的死亡,可以說“我”在無形之中成為了祥林嫂之死的最終推手。魯鎮人對祥林嫂悲慘命運的鄙薄,尤其是促使她一次次講述阿毛被狼吃掉的故事,一次次揭開她內心的傷疤,不給她愈合的可能。四叔一家在祥林嫂再次回魯鎮后因對她的排斥與嫌棄而導致她流落街頭,沒有了安穩生活的希望。這種雙重視角不僅是看,還直接對人物的命運產生影響,比單一的敘述視角更多樣化,更全面客觀。而“我”在看祥林嫂的同時,也在看魯鎮人,由關注一個主要人物擴大到關注一個群體,他們大多消失在寒冬之中,有代表性地展現了人性本身以及他們的命運。當然,讀者站在第三個層面能看到作為知識分子的“我”在解答祥林嫂提出的人死后有無靈魂的問題時含糊不清,采取逃避態度,又引起了思想啟蒙者對自我淺薄和軟弱問題的反省。如果學生在寫作中能嘗試這種多元化的敘述視角,那么所寫的作文就不會顯得稚嫩了。
三、巧用點面結合的人物描寫方式
魯迅先生筆下的人物往往讓讀者感覺自己身上有人物的影子,人物身上也有自己的印記, 換句話說,魯迅先生筆下的人是“活著的”。描寫《祝福》里的祥林嫂時,其不僅應用了環境、語言、肖像描寫,還用了動作、心理以及細節描寫。例如,灰白色的云、讓人耳鳴的爆竹、幽微的火藥香及團團飛舞的雪花表現出的魯鎮熱鬧忙碌而又壓抑陰沉的氛圍,這樣的環境描寫襯托出祥林嫂命運的悲劇性。“我”回魯鎮初遇祥林嫂時,祥林嫂一手提著裝著既破又空的碗的竹籃,一手拄著下端已裂開的長竹竿,像是真正的“乞丐”。整個回憶,魯迅先生非常細致地描繪了祥林嫂的碗與長竹竿。其中,碗破了,還是空的,竹竿比她還長,不適合她,而且下端開了裂,這都表明沒有人關心憐憫她,她的處境困頓艱難。魯迅先生將這些不同層面的描寫綜合運用,自然形象地寫出了真實的祥林嫂。在多層面描寫的同時,魯迅先生還非常擅長突出個別點。在《我是怎樣做起小說來》中曾提到,要“極省儉地”描繪人物特征,要刻畫人物的“眼睛”。《祝福》里,魯迅先生對祥林嫂的眼睛進行了12次描寫,并且每次各不相同,由初到四叔家時的“順著眼”到死前我見時的“間或一輪”, 每次的眼睛描寫都暗含著人物命運的變化。在學生的寫作中,若能點面結合地描寫人物,那么人物形象自然會栩栩如生。
四、力求語言簡約凝練
在魯迅先生的文章中,作者很少直接站出來用議論抒情性的文字對所寫內容橫加點評,亦未應用多種多樣的修辭和華麗的言詞。他認為,寫文章也罷,寫小說也罷,應盡量避免“行文嘮叨”,只要意思到位,哪怕沒有陪襯都是好的。比如,中國舊戲花紙,以往是沒有多樣背景的,僅幾個人物而已,現在卻出現了多種背景。但這并不妨礙寫作目的的表達,故而魯迅先生對此描寫非常簡潔。同理,寫《祝福》時,他也盡可能地進行簡單客觀地白描,不直接哀嘆人物的悲劇命運,不引導讀者按照作者的既定觀點去看待作品,然而相比冗長的哀嘆評論,簡單明了的客觀事實卻更具強說服力,有助于讀者對作品的客觀公正解讀。
以上是筆者從《祝福》一文中得到的寫作啟示。如果對魯迅先生的作品多從寫作角度進行解讀,并與學生的寫作結合起來,使閱讀與寫作雙管齊下,不生硬地將作品的思想主題塞給學生,或許學生會慢慢走近魯迅,甚至喜愛魯迅。
作者單位:浙江省新昌縣澄潭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