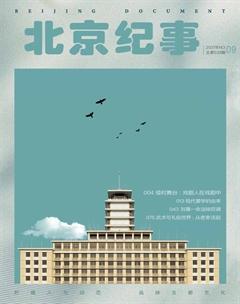二師記憶
劉賀英

北京市第二師范學校是我的母校。原是宣武區師范學校,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回民學院師范部,1960年學校遷至白廣路18號。1963年,全市師范學校調整為5所,宣武區師范學校改名為北京市第二師范學校。我就是在學校改名那年秋天入學的。
查閱《宣武區普通教育志》,里面對二師有這樣的記載:
至1966年,該校先后為北京市城近郊區培養小學教師942人,幼兒教師82人,培訓在職教師61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師范學校停止招生。1969年12月,“二師”復歸區文教衛生局領導。1970年恢復招生,增設專科班和醫士班。先后向本區各中小學輸送教師780人,校醫45人。1978年4月北京市第二師范學校改為北京師范學院分院。
1963年我從師大二附中畢業,報考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市第二師范學校,被順利錄取。當年8月20日校團委、學生會寄來的祝賀信我至今還珍藏著,翻開薄薄的信箋,那個時代特有的印刷體和字里行間洋溢的熱情依舊能打動人。
我對母校的記憶還停留在20世紀60年代。記得那時候的學校是一幢白色的四層樓,在白廣路上,靠東,門朝西。校舍主教學樓呈L形,西邊是宿舍,南邊是教室,頂層有平臺。操場被“L”半包圍在里面。食堂和琴房在操場北邊,另是一座兩層小樓。我們的教學樓是按照20世紀50年代末北京市教育局改進的教學樓設計標準建造的。資料顯示,當時的新標準中學教學樓,要求每層凈高不低于4米(以前的標準是3.5米),內中廊凈寬不少于4米,單廊凈寬不少于3米。建筑層局部5層,房間面積為6.60米×9.60米,平均每名學生占4.4平方米(以前標準是4平方米)。可見教學環境和條件還是很不錯的。我們女生宿舍在西邊三層,男生在四層,教室則在南邊一層最東頭的一間,從一年一班到三年一班,我們的教室一直沒換地兒。
今年春分那天,我在閨女的陪同下,尋覓著來到了白廣路18號,這是在白廣路南口往北不遠處的一個單位門口,我覺得這個位置大概就是以前的學校了,不過現在的這里不太像個學校,門口掛著好多塊牌子,有北京教育音像報刊總社、現代教育報社、北京教育綜合服務中心、北京市國際教育交流中心,等等。我不太敢認了,但這些單位都涉及教育,讓我又覺得找對了地方,不過辦公樓的顏色是深紅色,和記憶不符,通過觀望樓體外側,加上詢問保安,初步確定了這是座老樓。保安說,聽說這棟樓和人民大會堂是同時代的建筑,聽到這里,我有了95%的把握。征得保安的同意,時隔半個多世紀,我又踏進了母校的校門。

畢業54年后重返校園,親切、熟悉又陌生,感慨萬千。我在主教學樓門口拍了照片,然后繞向南邊最東頭,從玻璃窗外依稀分辨著我們以前的教室。現而今,教室已大都變為辦公室了,樓里面不許進,只能從外面看到模糊的一點輪廓。主樓東頭向北又接出一截,也是四層,可以從粉刷的墻立面看出新舊差異。但是50多年風風雨雨,教學樓主體絲毫未變,這一點發現已經足夠讓我驚喜和欣慰了。在“L”形主樓內側,操場、秋千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小花園。北側的小樓也還在,不知道現在的用途是什么。看著那兒,我仿佛聽到了50多年前從琴房飄出的樂音,和籃球砰砰撞擊地面的聲響,串聯起恰同學少年、懷揣夢想、激情昂揚的青春歲月。
保安來催促我們盡快離開,打破了我的神思。短短的探訪結束了,我在大門外又駐足良久。李白說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我當時也有了一絲這種感覺。建筑物的存在勾連起今夕,我們站在建筑物前的遐想也多是對當時的人與事的回憶和思念。
二師校風正派、制度嚴謹,教師個個是楷模。師范三年,我們班的班主任分別是王文珠、李忠、夏淑蘭老師,他們像家長、像同伴,關心著全班47名學生,以身作則,踐行著“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的師范生座右銘,教會我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師。二師當年的師資雄厚,融合了老北師、老西城師范的優秀教師,又延請孫敬修等老一輩教育家為我們講座授課。學校課程豐富又有深度,除了文理科的幾大基本課程及教學法外,還有心理學教育學,音體美小三門更是師范生的特色,音樂包括聲樂、器樂,體育鍛煉種類齊全,美術課活動豐富,另有下鄉勞動、社會實踐和教育實習。
軟硬件的優勢,讓學生們在校練就了扎實的基本功。那些年,二師這塊規模不大的寶地培養出了大批精英。1967年11月,因“文革”推遲了一年多的畢業分配開始了。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同學們懷揣著“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革命理想,分赴北京市遠近郊區各處,投入到基礎教育戰線的第一線。而今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都已年逾古稀,數十年在教育行業各學科領域深耕,有許多人脫穎而出,成為全國勞動模范、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特級教師、北京市特級教師、當代書畫藝術大師等。更多的則是默默奉獻于教育和教學管理事業,直到光榮退休。還有的同學因為積勞成疾,過早地離開了我們……
二師和她的學子為祖國的基礎教育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查找史志資料和網絡資源,對于這所學校的介紹卻少之又少。可能是五六十年代學校的合并改名、調整、遷址很多,許多歷史資料沒有得到妥善保存;文革時期對文教領域的破壞又相對嚴重。再加上年代久遠,我們這些畢業生埋頭工作數十年,只問業績成績,不求聞達,無暇顧及對自己、對母校的宣傳和過去資料的挖掘。2016年秋,我們班的骨干成員提出了一個倡議,要出本書記錄我們的學生時代,感恩學校和老師,銘記那革命烽火的歲月,鐫刻我們獻身教育事業的矢志不渝。經過全班同學兩年多的共同努力,寫回憶文章、投稿、編輯校對,最終由我們班最優秀的同學、全國特級教師馬芯蘭捐資印刷,制作出了一本班書,命名為《歲月》。書里,有記憶的美好、生活的坎坷,更有理想的芬芳。這本書像一部百科全書,又像一部交響詩,透過它,我們二師人的精神風貌得到了充分體現。
雖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處在當今這個瞬息萬變的信息社會,及時地回顧歷史,或許可以讓我們不忘來路,銘記初心。我想,二師給祖國的教育事業做出的貢獻,應該讓現在和未來的年輕人有所了解。所以,提筆寫下了這篇回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