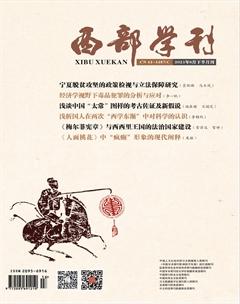論冼夫人信仰的女神崇拜情結
摘要:女神崇拜其實是原始社會母性崇拜的延續。冼夫人生活的南北朝時期,女性在家庭以及政治生活層面依然享有話語權與控制權。冼夫人雖為女性,具有陰柔之美,同時又是個能行軍打仗的首領,兼具陽剛之美。陰陽之美結合使冼夫人形象大放異彩。女性神祇更易產生讓人靠攏的宗教情感,也更易為民眾接受。冼夫人由真實的歷史人物逐漸演變為民眾頂禮膜拜的女神,這個過程帶有神話的光芒。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中,官方、民間共同起了不同的推動作用。從圣母之稱即可預知冼夫人死后從一介凡人而抬升為女神的歷史必然性。縱觀冼夫人一生的思想與事跡,她致力于將好戰與分散狀態的嶺南百越部落和合、集聚起來,對漢俚文化融合采取包容的態度。冼夫人管理嶺南地區以鮮明的“德治”思想為內核,她以化解部落族群矛盾、促進嶺南地區融合穩定為要務,體現了正面向上的文化特質:和合、包容與護佑,死后冼夫人被稱為“保護神”“和合神”。
關鍵詞:冼夫人;女神崇拜; 情結 ;文化特質
中圖分類號:C913.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16-0135-03
公元6世紀時南越俚族女首領冼夫人(512—602年),從歷史人物逐漸演變為受民眾頂禮膜拜的女神。粵西、海南、貴州、廣西甚至遠至越南、馬來西來諸地皆有冼廟供民眾朝拜緬懷。通常而言,神祇的女性性別更易于人們對其進行宗教接受。民眾對冼夫人信仰中產生的女神崇拜情結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運用女性主義神話學理論研究冼夫人信仰中的女神崇拜情結,將會還原冼夫人作為歷史人物神化的過程,讓這個過程變得清晰全面。發揚冼夫人女神文化的特質對推動當下社會精神文明建設有積極的意義。
一、女性主義神話學背景下的女神崇拜
神話學到20世紀中期進入大變革的時期,女性主義神話學作為最有影響的一個學派迅速崛起。20世紀女性主義神話學的興起,特別關注神祇的女性性別身份。女神崇拜情結是人們無意識心理的顯現形式。追根溯源,女神崇拜其實是原始社會母性崇拜的延續。母親作為生殖繁衍的載體,母性是受到膜拜的。女神崇拜熱潮的出現與女權主義運動具有一定的關聯。葉舒憲在《發現女性上帝——20世紀女性主義神話學》中指出:“男神獨尊的天神世界折射的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現實社會。早在男性神靈出現在神譜和神壇之前,是女神占據著絕對的崇拜優勢。” [1]其實不盡然,民間信仰與現實生活中的女性與男性往往呈現倒置現象,就算在男性神靈已經出現在神譜的年代,女神也依然可以和男神抗衡并取得絕對的崇拜優勢。無庸置疑,女性主義神話學是典型的女神崇拜學派。再看冼夫人生活的南北朝時期,嶺南百越之地較少受到中原父權文化的濡染與浸潤。俚族社會群體中父權未被強化,女性在家庭以及政治生活層面依然享有話語權與控制權。《隋書》記載冼夫人少女未婚時期已具有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眾,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2]冼夫人少女時期即能行軍用師,鎮服百越,這與傳統慣性設定女性為柔弱的習見是背道而馳的。成婚后的冼夫人更是縱馬馳騁,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冼夫人作為女性,在她所屬的社會的作戰、帶領軍隊、治理社會的卓越能力絲毫不遜色于男性。冼夫人丈夫馮寶的父親馮融作為南下的北方官吏,深知要管理好戰野蠻的俚族社會,必須倚仗冼家勢力,所以才有了馮冼聯姻。冼夫人作為一個女性,具有女性的陰柔之美,同時又是能行軍打仗的首領,兼具陽剛之美。將陰陽之美結合起來,使冼夫人女神形象魅力大放異彩。正是因為獨特的地域及時代因素,冼夫人作為女性具有與男性比肩的能力,她協助丈夫馮寶參政議政,馮寶去世后冼夫人更是統領嶺南六州,走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央。
從冼夫人廟的稱呼可見民眾對冼夫人信仰推崇的內在原因。除了冼夫人廟之稱外,還有別稱冼太廟、寧濟廟、柔惠廟、慈佑廟等的廟宇。冼太尊稱,強調了其作為婚后年長女性關愛、仁慈的特質。這與電白山兜丁村“娘娘廟”之稱如出一轍。所謂“娘娘”,據傳是指古代母家對出嫁了而又有功績、身份顯赫的女性的稱呼。尤其當這種出嫁女性已極為年長,并又在民眾中擁有極高的聲望時,民眾對其自然產生一種類似“母與子”的精神歸附感。此外,這些廟宇都著力強調冼夫人作為女神的柔、慈的女性特征。民眾對冼夫人的接受體現了自身的精神需求,祭祀冼夫人讓他們獲得回歸母親懷抱的寧靜柔和的精神體驗。面對男神與女神,民眾所獲得的情感體驗迥然不同。男神與強大、威嚴等詞匯相對應,民眾在精神層面上是匍匐在其腳下的渺小個體,男性神祇對信徒靈魂上的威攝力使“神—人”的關系總是遠離與敬畏的狀態。面對女神則不然,民眾在祈禱儀式中感受到的是親近、母性的光輝,心靈被軟化與蕩滌,甚至產生回歸到家庭倫常層面的溫情體驗。
二、冼夫人女神化形成的歷史必然性
神祇形象往往是民眾根據自己的精神需求創造的產物。古籍所載的許多女神形象是人們虛構與臆造的,如觀音與西王母娘娘,影響深遠的這兩個女性神話人物就是神話思維再造的產物。包括東南沿海一帶所奉祀的媽祖,也是人們在頭腦中創造的海洋女神形象。但冼夫人與這些女神不同,她是實有其人的歷史人物,并被載進了《隋書》《資治通鑒》等歷史典籍中。冼夫人如何由真實的歷史人物逐漸演變為民眾頂禮膜拜的女神,這個過程非常值得考究。這既有冼夫人自身傳奇的歷史事跡為基石,也是官方與民間依據政治需求與民眾的心理需要對冼夫人進行想象重塑的結果,一個仁慈有愛的年老女神形象顯然更切合慈悲為懷的宗教信仰邏輯[3]。
首先,冼夫人的歷史事跡帶有神話的光芒。她馬上能帶兵打仗,梁朝侯景之亂時擊破李遷仕,陳朝滅歐陽紇,隋朝時親自上陣攻破王仲宣。在冼夫人生活的每一個時代,皆建有功業;她馬下能治理政局動蕩的嶺南社會,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女性。從冼夫人對若干歷史事件的處置看,體現了睿智、和融的女性精神。她懂得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比如,在冼夫人追擊李遷仕至贑石時,與北上援臺的陳霸先會師。此時冼夫人對丈夫馮寶說:“陳都督大可畏,極得眾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冼夫人 “極得眾心”的分析,具有順應歷史發展趨勢的超前眼光,她深諳長年陷于戰亂的民眾統一的熱望,順應了這種治理訴求的統治者才會是未來朝政的掌權者。并且歷史也證實了冼夫人極具閱人的眼光,陳霸先后來稱帝開創了陳朝。隋開皇九年(589),隋滅陳,嶺南政局陷入動亂,冼夫人被嶺南諸州郡擁戴,號為圣母,保境安民,被隋命統轄六州。十一年(591年),助隋平王仲宣叛亂。自此,嶺南各州皆歸入隋版圖。冼夫人也以功封譙國夫人,開府治吏。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女性長廊中,將行軍打仗與治政理民如此兼融在一起的女性是極其罕見的。正因為冼夫人神奇的英雄事跡,冼夫人的故事在民間口耳相傳中也被逐漸神化,如冼夫人試劍石的故事中,冼夫人聽當地民眾哭訴大榭嶺有個魔王叫大榭王,他為非作歹、禍害民間,冼夫人義憤填膺之際揮動寶劍將數十米外的一塊數噸重的大石從中劈開。更有甚者,在“驅鬼燒窯”的故事中,冼夫人可驅動天兵天將以及各路妖魔鬼怪為南朝梁代建造高州舊城趕制磚瓦。顯然,在這些民間傳說中,冼夫人的英雄事跡已被渲染夸大,具有了超越歷史故事的神話光芒。
其次,在冼夫人由人而神的過程中,官方、民間共同起了不同的推動作用。準確地說,官方的敕封與推許是冼夫人信仰地位奠定的最根本、最原初的因素和力量。作為神祇的冼夫人信仰的早期含義,更多表現的是官方而非民間的信仰訴求,表征的是宏觀意義上的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內涵,而非民眾層面的利益訴求。也就是說,冼夫人信仰不像一般的神祇信仰那樣重在除厄脫苦,修渡到彼岸世界。官方賜封建廟激發了鄉民的追隨與崇拜思想,逐漸變成了民間的自發紀念行為,并在1400多年的歷史進展與推進中,沉潛為民眾的女神崇拜情結。冼夫人信仰的載體主要是遍布各地的冼廟,包括各地自發建的鄉廟。況且,在向冼夫人信仰靠攏的過程中,馮冼宗族的向心力也得以強化。并以馮冼宗族為核心,冼夫人信仰形成一個地域性甚至跨地域性的文化與宗教現象,在粵西以及海南地帶形成較有影響力的信仰文化圈。這就使冼夫人文化不再囿于家族崇拜的范圍,而是超越家族的狹隘性,冼夫人女神崇拜情結固化為集體的歷史記憶。
歷朝歷代對冼夫人不斷冊封,從“石龍太夫人” “宋康郡夫人” “譙國夫人” “誠敬夫人”到“慈佑夫人”等,隨著封賜的累加,冼夫人歷史地位不斷提升。但有一點必須指明,在冼夫人的眾多敬仰之稱中,筆者認為“圣母”之稱是最尊崇的。“夫人”還是停留在俗世層面的對女性的泛化尊稱,而“圣母”則過濾掉了這些現世因素,而只強調女神光耀披澤一方的神祇特質。“圣母”是對女性最高的推許,已經上升到宗教層面的信仰。同時還必須注意到,“圣母”尊稱是在冼夫人生前即已獲得而非死后的追封。這點頗令人深思,也即意味著冼夫人因其讓嶺南穩定和諧的卓越治理能力,生前就在民眾中獲得了極為罕有的歷史聲望,這在中國古代女性中是絕無僅有的。從圣母之稱也可預知冼夫人死后從一介凡人而抬升為女神的歷史必然性。
三、冼夫人女神文化的特質:和合、包容與護佑
從史籍所載冼夫人事跡看,冼夫人管理嶺南地區以鮮明的“德治”思想為內核,她以化解部落族群矛盾、促進嶺南地區融合穩定為要務,死后冼夫人被稱為“保護神”“和合神”,體現了正面向上的文化特質:和合、包容與護佑。
縱觀冼夫人一生的思想與事跡,她致力于將好戰與分散狀態的嶺南百越部落和合、集聚起來,對漢俚文化融合采取包容的態度。女性主義神話學認為,女神文化是和平的,以女性為中心的;男神文化是好戰的,以男性為中心的。大體上男性的象征可以認為是獨立自主,其流弊是專制獨裁;女性的象征是慈愛寬恕,其極致是民主和平。以男性從屬于女性,即是以慈愛寬恕為存心的獨立自主,反專制獨裁的民主和平[4]。《隋書》載青年時的冼夫人:“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于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余洞。”[2]注意這里的“為善”“信義”等與德行相關的詞語。晚年的冼夫人每歲時大會,將前朝賜物皆陳于庭,并教育子孫要存忠孝之念。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分裂割據,古代民族部落之間戰亂頻仍。《廣東通史》載:“俚人隨山洞而櫝(以山洞為家),各有部落,各為雄長,好相攻討(互相搶奪),也有勢力較大的部落聯盟,由酋長統治,少與中原人往來。”羅州以百越的獠人、俚人為主,由于思想不開化,排斥外來人。冼夫人的丈夫馮寶為南遷的北燕苗人后裔,身為俚族首領的冼夫人與馮寶的聯姻,就具有了非比尋常的超越婚姻之外的社會與文化意義,也表明了冼夫人及其原生家庭對漢俚文化融合的一種包容、開放與接納態度。因為馮寶所代表的來自中原先進地區的漢文化未受拒斥,所以冼夫人所在俚人部落相比于同時代別的酋長或首領所盤踞的地域,文明開化程度來得更快一些。
冼廟中,除了專門祭祀冼夫人及其馮氏親緣的廟宇外,還有一些廟宇是共同供奉冼夫人與其他神祇的而并未冠以“冼廟”之稱,這樣的廟宇就更是多不勝數了。冼夫人與其他神祇和諧相處,并無悖謬感。在茂名市茂南區的文武宮,廟宇正殿奉祀眾多神祇,有冼太夫人、關武帝、羅侯王、八仙、觀音、土主等。將冼夫人與觀音、關武帝等并置,一方面充分體現了冼夫人在后世民眾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冼夫人生前和合、包容思想的體現。
梁、陳、隋三朝,嶺南地區正是因為冼夫人的存在才有了基本的政局穩定,所以冼夫人護佑一方的神祗功能也被民眾共同認可。無論冼夫人管理高涼、進軍海南抑或平定叛亂都是施政有方的。越人野蠻好斗,冼夫人婚后協助丈夫管理高涼,約束本族,使當地政令有序;后經梁武帝御準在海南設置崖州,她率將士數千人啟程渡海在“梁沙坡”登岸。她以“平亂綏懷”“以德為懷”的宗旨進軍海島,冼夫人的軍隊所到之處匪徒望風而降。故此,每逢農歷二月初六至十二日,附近一帶民眾便定這幾天為“軍坡節”,以紀念冼夫人進軍海南的壯舉。減少戰爭的紛擾與侵害,能不動用兵力就不用兵力,冼夫人的德治思想將海島民眾和合、集聚起來。長坡冼廟對聯頌贊冼夫人曰:民融百越、國佐三朝,用極為凝練簡潔的八字道出了冼夫人促進嶺南百越民族融合的歷史功績。冼夫人對嶺南的治理施以和諧、包容的策略,懷柔和合,化解了許多矛盾與棘手問題。隋朝年間,俚帥王仲宣與酋長陳佛智叛亂謀反,冼夫人派馮盎帶兵解圍,為了安定人心,冼夫人騎駿馬,張錦傘巡撫二十余州,嶺南逐漸安定。后來,民間模仿冼夫人生前巡游的浩蕩場面而舉行冼太夫人神像巡游活動,冼夫人作為神祇的功能不斷得到強化。在民間巡游、建廟立祠等祭祀活動中,民眾表達了希冀冼夫人神靈護佑與降福的樸素宗教情感。
在社會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冼夫人信仰崇拜受眾群體持續增多。如前所述,女性神祇更易產生讓人傾向與靠攏的宗教情感,女性性別更易為民眾接受。在冼夫人傳奇事跡的基石上,官方與民間共同推動了冼夫人神化的過程,冼夫人女神化是一個必然的歷史現象。冼夫人女神文化體現了和合、包容與護佑的特質,這也是民眾的女神崇拜情結產生并固化為集體歷史記憶的重要原因,所以民間自發自愿紀念冼夫人的民俗活動特別豐富。民眾對冼夫人信仰產生的女神崇拜情結從文化學、宗教學的層面上都是極具研究價值的現象。
參考文獻:
[1] 葉舒憲. 發現女性上帝——20世紀女性主義神話學[J]. 民間文化,2001(1).
[2] 魏征.隋書 [M].北京:中華書局,1997.
[3] 曾麗容. 軍稱娘子驚飛將,國倚夫人勝筑墻——古代詩文戲曲楹聯中的冼夫人文學形象研究[J].廣西大學學報,2014(1).
[4] 郭沫若.沫若文集 [Z].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作者簡介:曾麗容(1977年—),女,漢族,廣東茂名人,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副教授,廣東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古代文學與地方文化。
(責任編輯: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