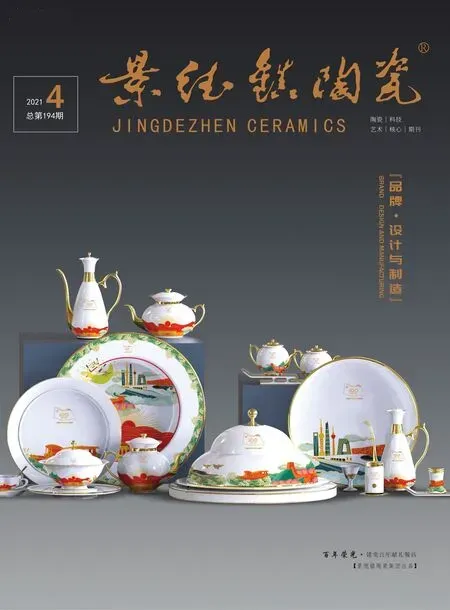古陶瓷中青銅器藝術(shù)的繼承與發(fā)展
溫寧榮(景德鎮(zhèn)陶瓷研究院)
一、陶瓷器與青銅器的產(chǎn)生
陶瓷在中國有著久遠的歷史,陶是人類掌握火的技術(shù)之后應(yīng)運而生的產(chǎn)物,最初的陶器是先民們?yōu)樯钚枰谱鞯娜沼闷骶撸綎|漢時期逐漸發(fā)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陶瓷。青銅器的產(chǎn)生得益于制陶的發(fā)展,人類最早使用的銅器是用天然銅鍛造的小型工具和裝飾品,當銅加上適量的錫后,熔點降低,硬度提高,這種呈青灰色的合金被稱為是錫青銅、青銅。
中國的青銅時代,大約從公元前21世紀開始,到公元前5世紀為止,經(jīng)歷了1500多年的歷史。最初的青銅器表現(xiàn)出了對陶瓷器的借鑒,當青銅器藝術(shù)日漸壯大,瓷器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兩者在相互借鑒中不斷發(fā)展,在創(chuàng)新中日趨完善。
二、古陶瓷與青銅器的相互影響
1、禮器思想
“禮”的概念在史前時期的陶器上就已見萌芽,對禮的重視總是表現(xiàn)在將最珍貴的材料,最精湛的技藝,最真切的情感融入禮器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譽為古代巔峰之作的蛋殼黑陶杯,它頭重腳輕,壁薄易碎,出土不見居址,多在大型墓葬中,而且位置也常常單獨放在顯要之處,似乎完全是為了滿足少數(shù)人的墓葬需要而制作的禮器美術(shù)作品。
青銅器作為陶器之后出現(xiàn)的新材料,它的開采、冶煉與使用必然掌握在擁有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權(quán)力宗族手中,成為他們用以維護和彰顯其統(tǒng)治力量的政治物品——兵器與禮器。此時,蛋殼黑陶杯所承載的禮器涵義便從陶器轉(zhuǎn)移到了青銅器上,商周許多出土的青銅器在形狀、裝飾和銘文上都驗證了它作為禮器的屬性。
當珍貴的青銅材料無法滿足社會需求時,人們便開始用陶瓷材料去仿制青銅禮器進行祭祀、隨葬,河北易縣燕下都第16號大型戰(zhàn)國墓中出土的大量仿青銅器的陶明器就是很好的例子。隨著陶瓷發(fā)展日趨成熟繁榮,高超的制瓷技藝又使禮器的內(nèi)涵逐漸回到陶瓷制品上,在中國陶瓷發(fā)展的鼎盛時期,宋徽宗曾頒詔以古銅禮器為范本纂輯《博古圖》,后來發(fā)現(xiàn)出土的許多宋代青瓷在形制和紋飾上都與之非常接近,應(yīng)是仿照青銅禮器燒造的陶瓷禮器。

2、日用造型
陶器最初的造型簡單質(zhì)樸,多是盛、煮器皿,隨著技藝的提高,造型逐漸繁復(fù)起來,有壺、缶、盂、鼎、甄、甕、壇、罐、尊等。青銅器首先采取了對當時陶器外形的直接模仿,使其直接擁有了陶器的造型特征,比如商代早中期青銅封頂盉的造型就是對龍山文化時期的陶盉造型進行的模仿。
青銅器工藝成熟后,統(tǒng)治階級開始關(guān)注生活細節(jié),日用品便成了他們財富與地位的象征,青銅器的功能也從作為隨葬祭祀轉(zhuǎn)換成滿足生活需求。這一轉(zhuǎn)變極大程度地推動了青銅器對陶瓷日用器皿的廣泛模仿,使青銅器的內(nèi)涵與造型逐漸豐富起來,直到商代以后,青銅器的形制才逐漸擺脫陶器對其的影響。
青銅器的成熟和繁榮也促進了陶瓷業(yè)的發(fā)展。東漢時期,原始青瓷胎質(zhì)細膩,比灰陶美觀,比青銅器新穎易制,迅速成為碗、盤、碟等日用器皿的常見品種,于是,出現(xiàn)了大量仿青銅器造型的陶瓷器皿。陶瓷與青銅器雖然呈現(xiàn)出此消彼長的態(tài)勢,但在陶瓷發(fā)展歷程中,青銅器元素的運用從沒停下腳步。宋代南方的龍泉窯成就了青瓷空前絕后的一個高峰,燒制了很多仿青銅器的青瓷禮器和陳設(shè)用品。宋代北方著名的汝、哥、官、定、鈞窯也出現(xiàn)了大量仿商、周、漢青銅器的陶瓷造型,其中汝窯多仿古青銅器,哥窯多仿青銅器,官窯也多數(shù)是由青銅器造型發(fā)展起來的。
3、紋樣裝飾
青銅器在制作初創(chuàng)階段繼承和模仿了已有的陶器紋飾,后期陶瓷器也將青銅器衍生的各種紋樣布局納入了自身的裝飾系統(tǒng)中,兩者在互相借鑒中,對原有功能的紋樣進行接納與修改,逐漸形成了自身的新紋樣藝術(shù)形式。
原始陶器多采用生活中常見的自然紋理,如繩紋、籃紋、幾何裝飾紋等進行模仿與變形,早期的青銅器從陶器紋飾中吸取靈感,甚至直接挪用。比如商代陶制封頂盉,器壁薄巧,形制復(fù)雜,在制作過程中,只能將其分解為頂蓋、頸腹、足幾個部分后,再依靠外力進行粘貼、組合,這種成型工藝上的局限性逐漸演化成了陶器上的凸玄紋裝飾帶。而青銅封頂盉運用陶范內(nèi)澆鑄、整體成型的工藝,卻也復(fù)制了這一玄紋裝飾帶,并作為純裝飾的形式納入到了青銅器的紋飾中。
無獨有偶,陶器在借鑒青銅器的過程中,裝飾特征同樣也被復(fù)制了下來,商代許多陶器的腹部、肩部和圈足都存在青銅器上常見的饕餮紋、夔龍紋、花瓣紋、云雷紋、連環(huán)紋等,尤其對比一些同期的饕餮紋陶器與饕餮紋青銅器,可以發(fā)現(xiàn)形制、紋飾幾乎完全相同。如,大英博物館藏有一件商代銅壺,它的裝飾紋飾呈垂直分布,其紋飾位置與外范的垂直接縫完全吻合,純粹是成型技術(shù)造成的痕跡紋樣布局。而安陽出土的兩件商代白陶壺,不光在器形上模仿了這種銅壺,在紋樣上也模仿了這種無實際功用的垂直裝飾形式。
三、結(jié)語
陶瓷藝術(shù)與青銅器藝術(shù)在相互影響中,經(jīng)歷了一個由借鑒到融合再到創(chuàng)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始終伴隨著一個以華夏之風對多種文化元素借鑒、融合、改造和創(chuàng)新的包容態(tài)度。從文化內(nèi)涵來看,文化的轉(zhuǎn)變豐富了陶瓷的內(nèi)涵,促進了陶瓷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從器型與裝飾來看,兩者生產(chǎn)技術(shù)與審美經(jīng)驗的相互繼承與發(fā)展,再次促進了陶瓷新紋樣與新風格的產(chǎn)生。對青銅器與陶瓷文化的深入研究,能使我們更好地吸收青銅器文化元素,這不是簡單的仿制,而是創(chuàng)造;這不是普通的仿古,而是標新;這也不是刻板的需求,而是功能與審美的再次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