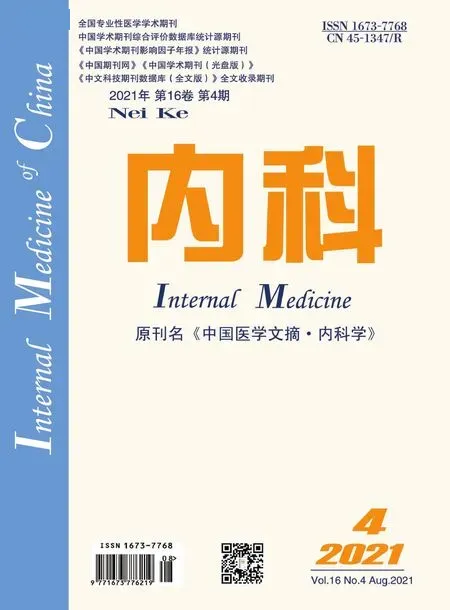腸道微生物與人體健康及飲食關系的研究進展▲
李莎 李倩 于海威 呂建楠
南寧市第四人民醫院&廣西艾滋病臨床治療中心&廣西醫科大學 附屬南寧市傳染病醫院,廣西南寧市 530023
【提要】 人體腸道微生物群是一個復雜的群落,由細菌、古生菌、真菌、病毒和原生動物組成。宿主從出生到死亡,其腸道微生物群的構成不斷變化并深刻影響著宿主的免疫系統與代謝。成年后人體腸道微生物群不會發生自發性顯著波動,但生存環境、地理因素、飲食習慣及抗生素治療等會對其產生一定的影響,而腸道微生物群的改變可能會引發肥胖、心血管疾病、中樞神經疾病、癌癥等問題。本文就腸道微生物與人體健康以及飲食的關系等進行了綜述,旨為預防疾病的發生和診治疾病提供新的思路。
1 腸道微生物及其檢測方法
人類腸道微生物多達100多萬億,它們與宿主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深刻影響著宿主的免疫系統與代謝[1-2]。腸道微生物可產生人體生理所需的維生素及其他代謝產物,對宿主健康有益的微生物被稱為“益生菌”;當腸道微生物群落的組成發生變化時,其功能可能會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到人體健康,這種情況被稱為腸道微生物群失調,可能會引發人體消化系統、神經系統、呼吸系統及血管系統的疾病[3]。不同地區、不同年齡段人體的腸道微生物群存在差異可能與地理環境及飲食差異有關,兒童腸道微生物群比嬰兒具有更高的穩定性和更低的個體差異,老年人的腸道微生物群的個體差異明顯大于年輕人[4-5]。老年人腸道內的擬桿菌、雙歧桿菌和腸桿菌的濃度降低,梭菌的濃度升高,腸道微生物群的組成與飲食和生活環境存在內在聯系,飲食干預可幫助老年人維持腸道微生物群在正常水平[6]。飲食干預除可使用益生菌以外,臨床上也常使用益生元。益生元是指一些不被宿主消化吸收但能夠選擇性地促進體內有益菌代謝和增殖,從而改善宿主健康的有機物質。目前常用動物模型來幫助識別腸道微生物及其功能,但動物與人體腸道微生物系統的同一性如何尚不十分清楚,通常使用16S核糖體RNA基因測序或全基因組測序等方法對腸道微生物群所含菌種進行定量檢測,并由此推測腸道微生物菌群的功能,通過代謝組學方法檢測糞便和血清獲得腸道微生物群的代謝產物[7-9]。
2 腸道微生物群的意義
腸道微生物群具備分解、發酵胃腸道不可消化物質的能力,例如膳食纖維和內源性腸道黏液。腸道微生物通過發酵獲得營養物質的同時,會產生諸如短鏈脂肪酸(SCFAs)和氣體等發酵產物,短鏈脂肪酸主要有乙酸、丙酸和丁酸等。丁酸是人類單核細胞的主要能量來源,不僅可誘導單核細胞凋亡,還可激活對葡萄糖和能量穩定有益的腸道糖異生反應[10-11];丁酸是上皮細胞不可或缺的物質,上皮細胞能通過β氧化來消耗大量的氧,從而在腸道內形成維持氧平衡的低氧狀態以防止腸道微生物失調[12]。丙酸被轉移到肝臟后,可通過與腸道脂肪酸受體的相互作用來調節糖異生反應和飽腹感信號[11]。乙酸是腸道內最多的短鏈脂肪酸,是其他細菌生長所必需的代謝產物,它能到達外周組織并參與膽固醇的代謝和脂肪生成,并對攝食中樞產生影響[13]。丁酸和丙酸可能還與腸道激素的分泌存在聯系,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小鼠的食欲和食物攝入量[14]。
腸道微生物酶參與初級膽汁酸的代謝,初級膽汁酸從膽囊釋放到十二指腸能促進膳食脂類和親脂性維生素的吸收,可在小腸和結腸處被微生物群轉化為次級膽汁酸(如脫氧膽酸和石膽酸)[15-16]。參與上述這些反應的酶由腸道微生物基因組編碼,因此糞便中的膽汁酸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腸道微生物群組成的影響[17]。不同宿主體內的初級膽汁酸和次級膽汁酸構成受到腸道微生物群的影響,而它們又在機體中充當信號分子并與相應受體結合,因此不同的微生物群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膽汁信號,并決定受體的激活程度,從而影響宿主的代謝;如果沒有微生物的參與,宿主膽汁酸的構成會發生嚴重變化,引起多種胃腸道、代謝和炎癥性疾病[17-18]。
3 腸道微生物群與疾病
3.1 肥胖 關于超重和肥胖人群的研究結果顯示,超重和肥胖人群的腸道微生物多樣性較低[19-22]。一項無菌小鼠接受糞便移植的實驗結果顯示,接受肥胖人員糞便移植小鼠的體重增長大于接受健康人員糞便移植的小鼠;克里斯滕森氏菌屬(Christensenella)在超重人群中很少見,而給小鼠注射克里斯滕森氏菌屬可以防止其體重增加[23]。克里斯滕森氏菌屬和其他如艾克曼菌(Akkermansia)等微生物與內臟脂肪沉積的減少有關[24]。研究表明,人類體重的增加與體內腸道微生物多樣性減少有關,而不健康的低膳食纖維飲食會加劇這種關系[25]。研究[26]發現,增加脂肪酸代謝來抑制無菌動物食源性肥胖的主要途徑有2條,分別是腸道上皮空腹誘發的脂肪因子水平升高和AMP活化蛋白激酶活性的增強。Karlsson等[27]報道,腸道菌群在肥胖和葡萄糖代謝中起關鍵作用,肥胖和2型糖尿病患者的腸道菌群組成發生了明顯的改變。Turnbaugh等[28]報道,與接受瘦弱小鼠糞便微生物移植相比,接受肥胖小鼠糞便移植的無菌小鼠的體脂含量和胰島素抵抗明顯增加。Opstelten等[29]報道,炎癥性腸病、銀屑病關節炎、1型糖尿病、肥胖、2型糖尿病和動脈硬化患者的腸道菌群多樣性較健康人群低;吸煙會進一步加劇克羅恩病患者腸道微生物的種類和數量的減少。但Zhao等[30]報道,大量增加膳食纖維會暫時減少機體腸道菌群多樣性,因為利用纖維素繁殖的微生物較多,它們繁殖時會導致腸道菌群組分發生變化,發生競爭性相互作用最終導致腸道菌群種類和數量的減少。腸道菌群在人體中的功能作用已通過糞便菌群移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證實,例如腸道艱難梭狀芽胞桿菌感染患者可以通過糞便移植進行治療,糞便移植可以作為一種潛在的治療肥胖和代謝綜合征患者的方法[31-33]。
3.2 心血管疾病 一些研究結果[34-35]顯示,腸道微生物能通過影響細胞因子的產生以及影響炎癥細胞的分化來調節炎癥;在動脈粥樣硬化斑塊中發現有細菌DNA,而這些細菌存在于患者的腸道中,提示腸道菌群可能是斑塊內細菌的來源之一,可能會影響斑塊的穩定性和宿主的心血管疾病發生率。Lam等[36]通過構建相應實驗模型探討了腸道菌群與心肌梗死嚴重程度之間的關系。一些研究結果[37-38]顯示,血液中高濃度的微生物依賴代謝物(trimethylamine N-oxide,TMAO)與動脈粥樣硬化風險增加有關,腸道微生物在動脈粥樣硬化發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與傳統飼養的載脂蛋白缺陷小鼠相比,無載脂蛋白缺陷小鼠的脂多糖水平更低,系統性炎癥及動脈粥樣硬化更少。艾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是人類腸道微生物群中最豐富的菌種,具有抗炎功能,在基因敲除和飲食誘導的糖尿病小鼠體內的艾克曼菌水平與其體重、炎癥指數、胰島素抵抗和糖耐量呈負相關;接受益生元飼養的小鼠,不僅體內的艾克曼菌豐度顯著提高,而且脂肪質量、胰島素抵抗及肝臟脂肪還明顯降低,艾克曼菌可降低載脂蛋白缺陷小鼠發生動脈粥樣硬化的風險[39]。
3.3 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機體的腸道與中樞神經系統之間存在相互作用,構成了具有一系列完整生理功能的“腸腦軸”[40]。腸道微生物群是腸道-大腦軸的關鍵因素,中樞神經系統可通過代謝系統和內分泌途徑以及釋放細胞因子和肽等信號分子來影響腸道微生物群;微生物群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影響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如釋放分子進入循環最終到達中樞神經系統并激活神經細胞上的特定受體。早期生活壓力能夠促使成人腸道菌群組成紊亂,但可通過使用益生菌予以治療即是例證[41]。Jiang等[42]報道,與正常人群比較,重度抑郁癥患者糞便樣本中的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和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的含量顯著增加,而厚壁菌門(Firmicutes)的含量顯著降低,而這些變化與患者抑郁癥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接受抑郁患者糞便微生物移植(FMT)的小鼠,會通過糖皮質激素信號誘導產生抑郁和焦慮行為。孤獨癥譜系障礙(ASD)患者常出現胃腸道并發癥,病因尚不清楚,但似乎與其過度使用抗生素導致腸道菌群發生改變有關。Adams等[43]報道,ASD患者胃腸道癥狀的嚴重程度與其腸道內的雙歧桿菌和乳酸菌等密切相關;Coello等[44]報道,雙相情感障礙患者體內出現黃酮分枝桿菌 (Flavonifractor Bacterium)、放線菌門和紅蝽菌科(Coriobacteria)水平升高的現象,可能會導致患者出現過度氧化應激和炎癥。Scheperjans等[45]報道,帕金森病(PD)患者糞便中的普雷沃氏菌科(Prevotellaceae)的豐度僅為正常人的32.4%,而患者腸桿菌科的相對豐度與其姿勢不穩定和步態困難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多發性硬化癥(MS)是一種慢性、炎癥性、中樞神經系統脫髓鞘疾病,患者腸道菌群門和屬水平會發生改變,如甲烷短桿菌(Methanobrevibacter)和艾克曼菌(Akkermansia)增加,丁酸弧菌(Butyricimonas)減少,治療后患者體內的普氏菌(Prevotella)和蘇氏菌(Sutterella)豐度增加[46-47]。
3.4 癌癥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共生細菌是影響人體健康的關鍵因素,與病變的發生密切相關,嚴重時甚至引發癌癥[48-49]。動物實驗結果[50]顯示,腸道微生物及其種類異常可能會導致肺、皮膚、乳腺等器官組織的癌變。腸道微生物群可通過以下三種主要機制引發癌變:(1)改變細胞增殖和死亡的平衡;(2)調節免疫系統功能;(3)影響宿主攝入的食物、藥物及體內產物的代謝。人類腸道微生物群在癌癥的發生、發展及癌癥治療中發揮著關鍵作用[51]。致癌微生物包括導致胃癌的幽門螺桿菌和EB病毒等,腸道微生物群除了有腫瘤誘導作用外,也具有抗癌活性,如微生物來源的短鏈脂肪酸能夠抑制宿主的腫瘤細胞組蛋白去乙酰化酶從而發揮抗腫瘤作用,這種作用在結腸癌和淋巴瘤中均有發現[52]。一些共生細菌可在聯合治療中發揮其益生菌的活性,避免腸道失調并增強宿主的免疫防御機制,如干酪乳桿菌(Lactobacillus casei)可以通過激活宿主免疫細胞[NK細胞和樹突狀細胞(DCs)]的JNK通路觸發腫瘤凋亡而抑制癌細胞或癌前細胞[53];梭狀芽孢桿菌(Clostridium saccharogumia)、遲緩埃格特菌(Eggerthella lenta)和布勞特氏菌(Blautia producta)可將異黃酮轉化為生物活性化合物,而植物雌激素對乳腺癌的保護作用有賴于腸道微生物的存在[54]。不同飲食成分的共同作用可能會產生一種對腫瘤生長起促進或抑制作用的體內環境,但特定的飲食成分是否會改變微生物群并對腫瘤產生影響目前仍不十分清楚;研究結果顯示,飲食的劇烈變化會明顯影響腸道微生物群并導致細胞異常增殖(癌癥標志物)[55]。
4 飲食對腸道微生物群的影響
文獻[56]報道,在改變飲食后的幾天內,人體腸道微生物群就會發生顯著改變,導致腸道微生物群發生顯著性改變的時間僅需5 d;微生物群對飲食干預產生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彈性的,可以通過調整飲食恢復原始的群落組成。某些食物或飲食模式會影響腸道中不同種類細菌的豐度,進而影響機體健康。如蔗糖素、阿斯巴甜和糖精已經被證明會破壞腸道微生物群的平衡和多樣性[57];與沒有進食三氯蔗糖的小鼠相比,連續服用三氯蔗糖的小鼠腸道內的擬桿菌、梭菌和總需氧細菌的比例明顯增高,其糞便的pH值也明顯增高[58];給予三氯蔗糖6個月的小鼠的腸道細菌促炎基因表達增加、糞便代謝紊亂[59]。微生物群可通過代謝產物如短鏈脂肪酸等對臨床治療某些疾病產生益處,纖維攝入減少會導致短鏈脂肪酸的產生減少進而改變腸道微生物的新陳代謝,而腸道微生物為了存活會利用非最優營養物質維持生命,這會導致潛在有害代謝產物的產生[30,60-61]。高脂飲食會對腸道黏膜的滲透性和代謝功能產生不利影響,但可以通過給予菊粉(inulin)膳食來預防,攝入膳食纖維有益于人體健康[62]。
益生菌是活的微生物,一般主要是指雙歧桿菌和乳酸菌,可以制成多種產品,如食品、膳食補充劑或藥物等,可以通過直接作用于宿主而不依賴于微生物群而影響宿主健康,例如益生菌能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臟代謝參數,但益生菌補充劑的類型、劑量或干預時間等與療效的關系目前尚不十分清楚;益生菌治療的新興領域包括嘗試用新的微生物治療,或將其組合應用,或將益生菌和益生元(合生元)聯合使用等[63-65]。
5 小 結
近年來,腸道微生物在人體健康與疾病中的重要性逐漸被重視。人體腸道微生物群在童年時期相對穩定,成年后可能會因受環境因素、飲食習慣、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而發生改變,腸道微生物群失衡時可能會引發各類疾病;而通過調整膳食結構可改善人體健康,同時可通過檢測腸道微生物或其代謝物來評價人體的健康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