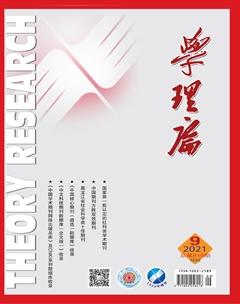從馬克思人學視角解讀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
謝曉玲
摘 要: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人呈現出不同的發展狀態,而現實生活中人的生存狀態又關乎社會發展方式的合理性。進入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深刻回答黨和國家的發展理念和現實問題,為研究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供了新的社會歷史條件。通過解讀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思想要義,分析其與馬克思人學思想的共通性,并加以理論聯系實際,才能深刻理解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理論淵源和實踐基礎,把握其人民共創、共享、共建及人的全面發展的核心特征,探究以人民為中心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實踐論的價值意蘊與價值追求。
關鍵詞:人學;以人民為中心;人民共創;人民共享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21)09-0034-03
黨的十九大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的地位。隨即,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學習和研究新思想的浪潮。而探索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思考其出現的社會歷史必然性,并為其找到理論的支撐點是我們作為新一代青年學生應當具有的思想品格。以馬克思人學視角解讀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挖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人的主體地位和價值,也是馬克思人學思想在中國的新發展。
一、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的基本觀點
馬克思在其中學階段就明確表明自己的觀點:為人類的幸福而工作。此后,馬克思終其一生為人的解放而奮斗,雖然馬克思并沒有專門論述人的著作,但在其許多經典著作中都蘊含著豐富的人學思想。因此,在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過程中,黨的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促進其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首先是人的本質理論。關于人的認識,是要回答人是什么的問題,就要正確把握人的本質問題。“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139“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也就意味著想要理解人,就必須從現實的社會環境入手。因為人在社會環境中,可以把自己造就成自己想要成為的人。
其次是人的存在理論。人的存在理論涉及人以什么樣的狀態來存在的問題,馬克思在該理論的論述中引入了“現實的人”這一概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因此,馬克思從現實活動中的人出發,關注現實生活中人的生存狀態、關注現實的人在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現實的人是作為主體性狀態的存在。
最后是人的發展理論,即關于人的存在價值和發展目標的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中最高的層面,涉及社會的發展條件和方式是否具有人的合理性,社會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是人為的,也應該是為人的。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論述人的發展經歷了人的依賴、物的依賴和全面發展的三種歷史形態,在《共產黨宣言》中論述人的發展的最高理想狀態:“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422
二、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特征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高度體現黨治國理政的價值取向,深刻回答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社會發展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向世人展示中國的發展理念和發展道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特征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人民共創是基點
所謂人民共創就是社會發展的主體是人民,社會建設必須依靠人的力量、智慧和創造性精神。“共創”強調的是全體人民一起發揮人的創造精神,不是只依靠一部分的人來為社會建設出力,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成果必定是惠及全體人民,只有在全體人民共創的基礎上,發展才不會偏離人。其次,人民共創體現的是人的主體性力量。在新時代,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主體作用,就表現在社會建設的能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人的腦力、體力和心理作用的發揮,人的理想和信仰的追求等方面。當前,我國的經濟正處于轉型時期,如何實現經濟的穩中求進,如何更好轉變發展方式,使經濟的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緊密結合,這些問題都需要激發人的創造力,展現人的主體力量。
(二)人民共享是應有之義
社會的發展匯聚了每一個勞動者的辛勤付出,理所應當的是,發展的成果將由人民共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2]共享與共同富裕在理論上是一致的,其核心是堅持人民是社會發展的核心,要增強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三)人民共建是最佳途徑
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發展,得靠全體人民的共同實踐才行。現在我們都在講中國夢,一個關于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能凝聚人心和力量,更有“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指引奮斗方向,這些遠大的夢想和目標就是全體人民共同參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來的動力。人是在社會實踐中獲得發展的。只有在勞動、社會實踐中才體現人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都因此得到發展。在新時代的社會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是人形成全面發展的大舞臺,人必須在實踐中展示自己的才能,證明自己的才能。
(四)全面發展是奮斗目標
人的發展問題始終是社會發展的首要問題,社會只有關注人,解決人的問題,才能改變社會。而全面發展涉及人的很多方面,在現代科技如此發達的時代,人的全面發展依然有重申的必要性,誠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所說,“這是最美好的時代,這是最糟糕的時代”,美好是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人因此獲得極大的進步;糟糕是因為市場經濟下,人卻或多或少地依附于物和技術。強調人的全面發展就要摒棄這種對外物的依附心理。談及全面發展,我們需要區分其與自由發展、充分發展的區別,“全面發展是從廣泛性上談人的發展,它與人的片面發展相對,指人的各方面的才能和能力的協調發展;自由發展是從自主性上談人的發展,它指的是人自覺自愿地發展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的力量;充分發展則是從程度上談人的發展,人的才能和能力的發展有個程度問題,人總是向著更高的程度發展自己的才能。在人的發展中,馬克思最突出強調的是‘全面發展,全面發展內含了人的自由發展和充分發展。”[3]人所追求的全面發展是自由而充分的發展,從社會上講,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關系以及生態等社會環境提供人全面發展所必須要素的完整性、高質量性;從個人層面上講,是人的生理機能、心理素質和個性的全面發展和充分表現。
三、以人民為中心的人學闡釋
(一)人是目的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內含了“人是目的”的思想,在哲學上“人是目的”的思想被認為是康德最先提出來的。“人是目的”即,任何人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都應該尊重人,使自己成為人,也使得他人成為人。當然,康德是出于他的純粹理性哲學,認為人是一個理性存在物,所以才具有目的性。“這種以理性自身為目的的目的,就具有絕對價值。它自身就是目的,而不以其他任何對象為目的;它自身就具有價值,而不因其他條件而具有價值,它是一切作為手段或工具的目的的價值根據。”[4]人是一切價值的尺度,就像單純的自然事物,離開理性的人就失去了價值,因為只有為人的、屬于人的事物才是有價值的。因此,康德從價值命題中論述“人是目的”,是說明人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價值和作用,社會發展的一切都應該是為了人的生存和發展。
德國古典哲學家費希特、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對于康德的“人是目的”持不同的觀點。費爾巴哈堅持人不能是自然界的目的的觀點,認為人是人和社會的目的,而不能是自然界的目的。費希特認為人是社會的目的,社會應該發展人的才能,一切為了人的發展,為人提供實現人、完善人所需要的一切,使得人成為理性的人,不能違反人是目的的理性原則。黑格爾認為人不僅是目的還是作為手段的存在,當人是目的時,人是作為類的存在。作為類存在的人是無限發展著的。把人當作手段時,人是作為個人存在。但是不管是作為目的還是手段,都不存在貶低人的意思。但是,德國古典哲學中所研究的人是抽象的人(為了對抗超越自然的精神力量),不是具體的個別的人,只是承認了人的地位卻沒有對具體、個別的人進行更深入的認識;是靜態的人,不是動態的人,不是在社會上現實生活著的人,這樣的人屬于觀念中存在的人,脫離了現實的實踐生活。總的來說,“人是目的”的思想在近代資產階級中發出了吶喊:為著實現人的目的和價值,社會應該滿足人生存和發展的各種要求,使得人成為人。但是“人是目的”的哲學思想在近代資產階級中是虛偽的,因為資產階級不會把一切人都當作目的,被當作目的的只是作為統治階級而存在的那一部分人。
馬克思在批判繼承德國古典哲學關于人的認識的思想上,研究現實活動中的人,特別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通過異化勞動來批判舊社會中的人的存在方式,批判異化了的人和社會,認為人不能是他人生存的工具,人應該成為自己并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質。因此“人是目的”的思想就演變成現實社會中的人的目的,人都是處在一定的、現實的社會關系之中,也就是“人是目的”的思想在現實的社會關系中是人的本質的體現。在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有著更為現實的目的,給予人和社會應有的人文關懷,是從新時代人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出發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使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在理論上深化了“人是目的”的思想。
(二)人是什么樣的目的
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看,人是自然發展到目前階段的最高級產物,但是自然的目的是無限的。我們要認清楚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價值,才能更好地和自然和諧相處。現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理念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生態文明建設上的具體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意味著我們從根本上轉變以前以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方式,認識到自然與人類是息息相關的,這種關系滲透著生命的延續,不能以自然生命的損耗來維持人的發展和延續。但這并不是說不要發展,從長遠來說,我們更應該倡導的是綠色發展,要意識到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的關系,人類要像對待自己的生命一樣對待自然。
從人與社會的關系上看,人是社會發展的目的,又是社會發展所依靠的手段。社會進行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是為了滿足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這種滿足程度又表明社會發展的程度和完善性,而離開了人這一目的,社會的一切發展活動都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面臨的是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困境,人是社會發展的目的和人能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目的。但人作為目的還是手段并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囿于社會發展的狀況,我們不可能一下子都能達成人的目的,在走向目的的過程中,人還得作為手段。如果人只是目的,人就根本無法達到目的、成為目的;而人只是手段的話,人就失去人之為人的價值,變成了工具,變成了自然和社會的奴仆。因此,人必須作為手段去實現一切,實現作為目的、作為客體和主體的價值。
四、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三重意蘊
(一)以人民為中心的本體論意義
一方面體現在發展中人的尺度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經常把人民的問題掛在嘴邊,一直著重強調人民主體地位在社會建設中的重要性,人民群眾在社會建設中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是進行各項工作的重心。把人民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這是對人民的尊重,是把人民群眾作為社會本體的表現。在馬克思人學思想上,本體論講的是人的主體性地位,人成為哲學的中心,成為智者的聚焦點并不是偶然的,因為望向星空的目光終究要回到人類本身來認識自己。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毫無疑問地將人的主體地位充分展現出來,表明在社會所有發展問題中,人才是中心和目的,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如果只重視物質的尺度而看不到人的尺度,只是看到物質資料的積累和增加而看不到物背后的人的生活狀況,那么最終的發展結果會與人的存在價值分離,導致人的異化和人的片面發展。
另一方面體現在社會發展中人的性質問題。馬克思是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現實的人指的是在現實的具體的社會關系中不斷發展的人,不是抽象思維中的不變的人。不斷發展意味著人所體現出的性質也是不斷完滿的過程。作為主體地位的人的需要是會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不同而呈現出階段性的變化的,這種變化相對于前一階段肯定更具完善性。在更高級的階段中,社會所體現出的人的性質也更具完整性和完善性,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越來越靠近真正自由自覺的狀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引領新時代的社會建設,所達成的發展結果必定是人越來越實現其自身的完整與完善,人的性質在社會中愈加豐富有內涵,也就是人的性質之完滿。
(二)以人民為中心的認識論意義
在哲學上,哲學家對人的認識是從抽象到具體、從思維的存在到現實的存在,人不再是斯芬克斯之謎(被認為是人認識自己、思考自身的開始)。馬克思人學思想蘊藏著豐富的關于人的知識,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理論淵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黨的歷代領導集體的治國育人思想,西方社會發展理論和經驗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我們對社會發展方式的認知,為社會發展進一步關注人的存在問題做出了積極的引導。
當我們理解現實中的自然界時,首先應當是把它作為人的生活屬地來理解,因為離開了人,自然界對我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那么當我們改造自然界,進行人類社會建設時,就應當以實現人的價值和滿足人的需要作為行動的導向,而不能脫離了人的實際需要盲目構建我們的生活世界。反思現實社會的發展過程,發展的結果雖取得建設性成就,但也出現了關于人的困境的問題。例如人的生存環境被破壞、人在社會中的價值感和幸福感的降低等問題,這些都屬于人的問題。但也正是這些問題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要以怎樣的發展方式才能在整體上增加對人的關懷。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置于全部發展問題的中心,使發展能圍繞人的問題而展開,從而解決人的問題,體現深刻的人文情懷,它要求在思考和解決問題時要運用人的尺度,把人當作目的和歸宿。
(三)以人民為中心的實踐論意義
誠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就說明,理論要走出自己概念的、抽象的、理想的圈子,與現實世界發生聯系,以克服自己的內在缺陷,實現理論的徹底性;同樣,現實世界需要理論的指導和制約,以達成生活的理性并做出實際行動改變自己。理論在另一種層面上也就是物質力量。“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現今的中國,無論是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偉大社會實踐,還是一個小企業的發展、個人的成長,都必須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過程中體現人的主體作用,使人跟現實世界發生能動的聯系,發揮人在社會發展中的能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在實踐中把人的身體機能和心理素質表現出來,使社會中的人形成并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信仰。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張步仁,馬杏苗.馬克思主義人學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4]羅國杰,宋希仁.西方倫理思想史(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