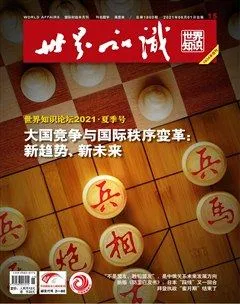歐洲與美國的關系不大可能“回到過去”
胡春春
拜登甫一就職,立即在“美國回來了”旗號下著手修補美歐關系,重振跨大西洋聯盟。“回來”的許諾來自于拜登在2020年大選期間的口號“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不久前也被用在所謂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議”(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中,即美國誓言率盟友加強對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以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但問題在于,美國能否“回來”?美國能夠回到此前什么狀態呢?其對歐洲開出的“新支票”能否兌現?
不妨假設美國確已如愿“回來”了,在美歐關系方面,回來后的狀態能與歷史上哪一時期類比?回到冷戰時的狀態?美國是冷戰時期的西方領袖,這對美國來說可能是最理想的狀態。但現在那種由共同敵人塑造的和諧主從關系、東西方陣營經濟上的涇渭分明已成為歷史。或者回到冷戰結束后西方處于權力頂峰的克林頓時期?但大家都知道,這一時期的“歷史終結論”已被證偽。再或回到小布什時期、尤其是其第一任期的狀態?這肯定不是美國所希望的,因為當時美國和法、德代表的歐洲在海灣戰爭問題上存在明顯分歧,雙方關系處于歷史低點。這樣看來,拜登政府希望通過上述口號促使歐洲和外界回想起奧巴馬時期美歐之間的熱絡狀態,但是美國從奧巴馬時期已經開始進行戰略收縮和轉移,重心逐漸從跨大西洋轉向亞太——現在叫“印太”。實際上,“美國回來了”是最能打動歐洲人的,拜登治下的美國愿重返所謂“多邊主義”道路以贏回盟友信任,為此可以擱置經濟、技術、外交爭端或主動讓步,同時也提醒歐洲,美國仍是西方或者“自由民主世界”領袖,美國能夠、也仍愿為盟友提供安全保護傘。
從歷史上看,“往回看”顯然不能為未來提供更為美好的愿景。拜登更多訴諸情感紐帶的“口號”恐怕不能完全付諸現實。那么當前美歐之間的現實是什么?
首先,歐洲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對外關系問題的根源在于國內,而美國國內社會已高度分裂。特朗普只是美國問題的癥候,病情很難在可見的短期內自愈。拜登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扭轉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優先”取向,可以從6月15日美歐峰會成果上看出端倪:關于新冠疫苗技術專利,雙方僅“鼓勵自愿共享知識和技術”,德國依然反對美國關于放棄疫苗技術專利的呼吁;雙方的大飛機補貼爭端擱置五年,并沒有最終解決,在鋼鋁關稅問題上的分歧也需進一步討論;德美分歧最大的“北溪-2”天然氣管線爭端甚至在聯合聲明中沒有提及。歐洲也清楚,誰也不能保證特朗普或者“特朗普主義”不會卷土重來。
其次,美國國內已就對華政策形成共識,所以不遺余力地宣講“中國威脅”“中國挑戰”,把中國視為“系統性競爭對手”成為美希望重塑美歐共識的權宜之計。但從德國國際和安全事務研究所2020年2月發布的《美中戰略對抗》研究報告可以看出,歐洲決定擺脫這種“兩極爭端必選一邊”的思維,希望在“戰略自主”框架下構建歐洲對華關系。歐洲清楚,美全球戰略重心已從跨大西洋轉向“印太”地區。歐洲人關切的是:美對歐政策調整是不是在對華“戰略競爭”框架下進行的?歐洲是不是已淪入“戰略從屬”地位?
歐洲在過去幾年中也發生了明顯變化,最大的變化來自于英國脫歐,這使美國失去了在歐洲內部事務中的代理人,歐洲擺脫了“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利益紐帶。另一變化涉及歐洲對美國和自身制度的認知。歐洲智庫近期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歐洲人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崩壞”,美國很難通過換個總統就重回“世界領袖”位置。由此,歐洲人對美信任度大幅下降,甚至不相信美能在安全問題上繼續保護歐洲。歐洲人對自己的制度則越來越持肯定態度,更傾向于“到柏林去”(指聽取德國的意見),并在歐洲框架內尋找解決歐洲問題的答案。此外,絕大多數歐洲人認為中國有可能在十年內取代美國成為“最強國”,因而主張歐洲在中美競爭中保持中立。
從歐洲的角度看,歐美關系很難回到過去。在歐洲主權和“戰略自主”意識崛起的框架內,未來歐美關系會逐漸走出“仆主關系”狀態,形成某種相對平等的新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