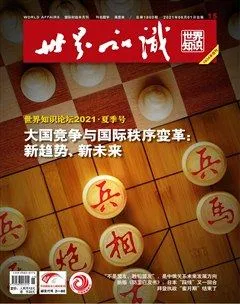中國與東盟要能共同自主決定地區議程
郭延軍
與特朗普時期相比,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改變了“零和博弈”基本策略,雖然采取的是全面競爭戰略,但合作也在慢慢恢復。
“新常態”能夠更準確、全面地概括中美關系當前的發展態勢,一個主要表現就是中美關系將進入一個較長時期的戰略相持階段,并可能呈現出三種具體形態:一是全面競爭。從美國出臺的一些報告不難看出,美已發起所謂“全路徑”(全政府、全社會、全文明、全方位、全世界)對華打壓。二是選擇性合作。過去中美合作領域覆蓋面寬,相關邏輯主要是基于絕對收益考慮。現在無論是對合作領域的選擇,還是對合作收益的考慮,都發生了明顯變化,更多表現為基于責任和成本分擔的選擇性合作,比如在氣候變化領域以及在中國周邊地區打擊毒品犯罪方面,合作邏輯則更關注相對收益。三是有限對抗。盡管美對華政策工具豐富,但對涉及主權等中國核心利益的政策工具的使用仍算謹慎。
美對華戰略折射到中國周邊地區,將對地緣政治和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第三方力量的選擇亦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美博弈的結果。中美博弈使得中國周邊地區出現了兩個“中間地帶”:一個是美國的盟友體系。個別國家如澳大利亞已經選邊站,更多國家處在矛盾和焦慮中,極力避免在中美之間做選擇。對于這些國家,中國不必抱太高期望,應盡量以經濟和市場手段維護正常合作。另一個是東盟,相關國家成為大國爭相拉攏的對象。但東盟明確表示不會選邊站。雖然東盟已接受“印太”概念,但并未放棄平衡外交,正努力淡化“印太戰略”的地緣政治色彩。《東盟的印太展望》文件被東盟明確定義為“參與亞太和印度洋地區事務”的指導性文件,反映出東盟力避亞太合作全面“印太化”的考量。
新加坡前高級外交官、著名學者馬凱碩認為,東盟是“上帝送給中國的一份厚禮”。在中美博弈加劇背景下,東盟作為“中間地帶”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中國應以綜合手段充分爭取。
第一,與東盟共促多極化。國際上有一些人擔心中美形成所謂兩極對抗格局,但我們認為,多極化仍有強大生命力,未來可能會形成以綜合實力為基礎、制度性權力為核心的世界秩序。積極主動地推動多極化進程,塑造地區秩序,對中國具有重要意義,也可為中國與東盟合作創造更大空間。過去東盟通過為大國提供合作平臺,把制度性權力發揮到極致,為緩沖大國競爭作出重要貢獻。中國應繼續支持東盟,努力將其塑造成一個地區制度性權力的中心,牽制美對華戰略圍堵。
第二,深耕地區治理。一般而言,中國在周邊地區的治理有兩種主要模式:地區一體化治理模式和議題治理模式。兩種模式互有區別,又互有交叉,相互促進。在眾多東亞一體化合作架構中,都規定了優先合作領域和議題,在上海合作組織這種議題治理模式中,也逐步加入了地區一體化的考慮。無論哪種模式,一個明顯趨勢是,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地區治理的成效更為顯著,而且地區國家對于共同利益的共識和追求可以讓各國更為理性和冷靜地處理分歧。因此,一種“去美國化”的地區治理模式應得到更多重視。經濟上,堅持以互利合作為抓手,鞏固中國與東盟經濟合作的“壓艙石”效應。安全上,從地區危機管理的視角去討論安全熱點問題,形成真正符合本地區國家共同利益的制度安排和規范認同。
第三,堅持“過程導向”,維護亞太合作框架。“過程導向”是東亞合作的成功經驗之一,漸進性、靈活性、協商一致以及照顧舒適度等原則在維護地區合作進程、緩解大國競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年是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伙伴關系30周年,回望雙方合作歷程,不難發現過程之于結果的重要性。當前,美對華戰略強調“結果導向”,根本目的是阻斷中國和平發展進程。“印太戰略”作為美遏華重要工具,對堅持“過程導向”的亞太合作框架造成沖擊,亞太框架面臨“印太化”危險。從這個角度講,中國與東盟應進行更為密切的溝通和協調,維護《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既有成果,共同自主決定地區議程,避免亞太合作走向“印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