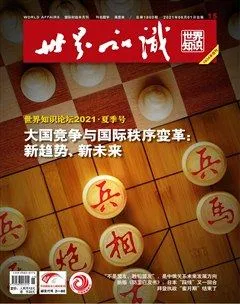上海合作組織在內(nèi)外雙重挑戰(zhàn)下煥發(fā)新動(dòng)能
楊成
2021年4月26日至28日,“上海合作組織國(guó)際投資貿(mào)易博覽會(huì)暨上海合作組織地方經(jīng)貿(mào)合作青島論壇”在青島膠州召開(kāi),來(lái)自30多個(gè)國(guó)家和地區(qū)的嘉賓和展商參會(huì)。
2021年是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0周年。上合組織從成立伊始就具備政治、經(jīng)濟(jì)、安全等多輪驅(qū)動(dòng)的復(fù)合型合作框架,內(nèi)部形成了中俄“雙引擎”共同牽引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上合組織的誕生和運(yùn)作是中國(guó)參與和引領(lǐng)地區(qū)治理的重要實(shí)踐。
經(jīng)過(guò)20年的發(fā)展,上合組織在歐亞地區(qū)事務(wù)中發(fā)揮著日趨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幾個(gè)方面:一是在“上海精神”指引下,提供了一種不同于西方主導(dǎo)的全球治理模式。上合組織強(qiáng)調(diào)國(guó)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并以此為前提和首要條件促成成員國(guó)“共同利益”的生成和拓展,從而在事實(shí)上踐行了國(guó)際關(guān)系民主化和國(guó)家間關(guān)系新型化的原則。二是在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和外部環(huán)境兩種復(fù)雜性之間不斷發(fā)生互動(dòng)或共振的情況下,協(xié)商一致推進(jìn)彼此合作。內(nèi)部復(fù)雜性不僅指成員國(guó)相差甚大的經(jīng)濟(jì)規(guī)模,還涉及成員國(guó)區(qū)別明顯的文明形態(tài)和政體類(lèi)型等因素。外部復(fù)雜性是指上合組織成立20年來(lái)國(guó)際格局和地區(qū)形勢(shì)均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盡管如此,上合組織還是做到了巧妙運(yùn)作,實(shí)現(xiàn)了多領(lǐng)域合作齊頭并進(jìn)的新局面。三是歐亞地區(qū)的和平、穩(wěn)定與發(fā)展日益離不開(kāi)上合組織。上合組織成立的初衷是尋求解決成員國(guó)之間歷史遺留的邊界問(wèn)題,此后始終把保持地區(qū)和平穩(wěn)定作為要旨。上合組織成立之初,分裂主義、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等“三股勢(shì)力”在中亞十分猖獗,后來(lái)美國(guó)在阿富汗等地發(fā)動(dòng)的反恐戰(zhàn)爭(zhēng)加劇了相關(guān)復(fù)雜性,給中亞地區(qū)安全帶來(lái)嚴(yán)峻挑戰(zhàn)。毫不夸張地講,如果沒(méi)有上合組織及其順利發(fā)展,中亞地區(qū)就不可能有今天總體和平、緩和穩(wěn)定的大好局面。
盡管政治和安全合作一直是上合組織的優(yōu)先方向,多邊經(jīng)濟(jì)合作議程整體上推進(jìn)相對(duì)緩慢,但這并不意味著成員國(guó)之間雙邊和小多邊的合作無(wú)所作為。目前,無(wú)論是在投資、貿(mào)易還是發(fā)展援助等領(lǐng)域,中國(guó)與上合組織成員國(guó)的合作處于持續(xù)增長(zhǎng)態(tài)勢(shì),中國(guó)也在與域內(nèi)國(guó)家共同推進(jìn)“一帶一路”建設(shè)。從此意義上講,上合組織經(jīng)濟(jì)合作正在不斷煥發(fā)出新的生機(jī)。
位于青島膠州的中國(guó)-上海合作組織地方經(jīng)貿(mào)合作示范區(qū)聯(lián)運(yùn)中心。
舉個(gè)例子,哈薩克斯坦學(xué)界曾經(jīng)對(duì)“一帶一路”框架內(nèi)的中哈經(jīng)濟(jì)合作抱有疑慮,擔(dān)憂(yōu)淪為中國(guó)的資源附庸。而現(xiàn)在僅“中歐班列”過(guò)境一項(xiàng)每年便給哈帶去直接經(jīng)濟(jì)收益超5億美元,且長(zhǎng)遠(yuǎn)趨勢(shì)是不斷增長(zhǎng)。哈總理府的數(shù)據(jù)顯示,2020年過(guò)境哈的“中歐班列”集裝箱運(yùn)量達(dá)51.75萬(wàn)標(biāo)箱,同比增長(zhǎng)65%。更不用說(shuō),通過(guò)中哈一系列大項(xiàng)目合作,哈在實(shí)現(xiàn)產(chǎn)業(yè)發(fā)展多元化、擺脫對(duì)油氣資源開(kāi)發(fā)的過(guò)度依賴(lài)方面已經(jīng)取得重大進(jìn)展。哈方日益意識(shí)到,與中國(guó)加強(qiáng)經(jīng)濟(jì)合作對(duì)其發(fā)展大有裨益,因而更加堅(jiān)定不移地推進(jìn)兩國(guó)永久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guān)系建設(shè)。類(lèi)似現(xiàn)象在中國(guó)與其他上合組織成員國(guó)的雙邊合作中都可以觀察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新冠疫情給上合組織成員國(guó)帶來(lái)巨大沖擊,但上合組織的跨境電商貿(mào)易仍在加速發(fā)展,其他領(lǐng)域務(wù)實(shí)合作也以新的形態(tài)不斷加強(qiáng),創(chuàng)造出巨大發(fā)展紅利。
20年來(lái),國(guó)際上不乏看衰上合組織的觀點(diǎn)和意見(jiàn)。一些成員國(guó)的智庫(kù)專(zhuān)家也傾向于認(rèn)為,上合組織在首次擴(kuò)員后已進(jìn)入“休眠期”。我認(rèn)為這種論斷過(guò)于悲觀,低估了上合組織的制度韌性,也沒(méi)有看到有利于上合組織發(fā)展的新條件正在形成。首先,國(guó)際秩序重構(gòu)和全球體系轉(zhuǎn)型進(jìn)程的加速效應(yīng)帶來(lái)巨大不確定性,顯著提升了地區(qū)性國(guó)際組織的存在價(jià)值,為上合組織發(fā)展提供了重要外部機(jī)遇。其次,全球和主要地區(qū)主要大國(guó)相繼提出歐亞地區(qū)一體化方案并形成彼此競(jìng)爭(zhēng)格局,中亞國(guó)家之間也重新出現(xiàn)地區(qū)整合態(tài)勢(shì),這些都意味著上合組織可以商討出新的發(fā)展議程。第三,上合組織吸收印度、巴基斯坦成為全權(quán)成員后,內(nèi)部權(quán)力架構(gòu)已經(jīng)改變,固然給組織發(fā)展帶來(lái)不少潛在挑戰(zhàn)(包括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新老成員之間的關(guān)系、責(zé)任和能力的矛盾,等等),但也意味著上合組織參與處理地區(qū)熱點(diǎn)問(wèn)題的空間進(jìn)一步擴(kuò)大,比如在美軍撤離后的阿富汗形勢(shì)問(wèn)題上,完全可以有所作為。
盡管上合組織在安全、經(jīng)濟(jì)、文化等領(lǐng)域的合作仍不平衡,也面臨所有國(guó)際組織在其發(fā)展周期中不可避免的“中段陷阱”挑戰(zhàn),即新興國(guó)際組織完成規(guī)章制度等初創(chuàng)階段建設(shè)后,在推進(jìn)實(shí)質(zhì)合作時(shí)因無(wú)法或難以“協(xié)商一致”而效率降低。在利益協(xié)同方面,隨著合作的深入開(kāi)展,也可能面臨后續(xù)動(dòng)力不足的問(wèn)題。但也正因?yàn)榇耍驹诘诙€(gè)20年的關(guān)鍵節(jié)點(diǎn)上,上合組織的轉(zhuǎn)型才變得更為迫切和必要,需要通過(guò)新的議程設(shè)置進(jìn)一步推進(jìn)和優(yōu)化務(wù)實(shí)合作,唯此才能在混亂失序的國(guó)際秩序中為維護(hù)全球和地區(qū)治理質(zhì)量提供動(dòng)力,同時(shí)避免不少?lài)?guó)際和地區(qū)組織因不能與時(shí)俱進(jìn)而陷入“空轉(zhuǎn)”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