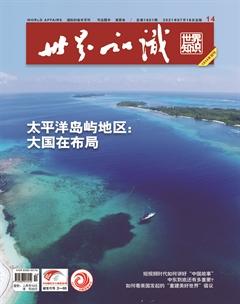《新大西洋憲章》:華而不實的空洞“致敬”
孫成昊?張蓓
1941年8月13日,為了協(xié)調(diào)反法西斯戰(zhàn)略,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停泊于北大西洋阿金夏灣的美國“奧古斯塔”號巡洋艦上舉行會晤,并簽署聯(lián)合宣言《大西洋憲章》。《大西洋憲章》的簽署和發(fā)布,推動了世界反法西斯聯(lián)盟的建立,為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建立奠定基礎(chǔ)。從這個意義上看,《大西洋憲章》引領(lǐng)了世界政治、世界觀念的進步,對國際關(guān)系有重要意義。
時隔80年后,2021年6月10日,美國總統(tǒng)拜登與英國首相約翰遜在英國康沃爾郡進行會晤,簽署了《新大西洋憲章》。拜登和約翰遜都將這份文件稱為是“80年前簽署的具有里程碑意義協(xié)議的重新振興”。
但新舊版本的《大西洋憲章》有著天壤之別。面臨迥然相異的時代背景,美英決策者未能與時俱進。《新大西洋憲章》只是滿足兩國自身政治需求的產(chǎn)物,并不能推動國際社會進步,注定難以在歷史上留下印跡。
美英各有所需
相比較而言,美英在G7峰會前達成的《新大西洋憲章》,與80年前發(fā)布的《大西洋憲章》有云泥之別。如今,美國與英國都已失去當年在國際體系中所具有的絕對實力與道德合法性,這次空洞的“致敬”均為美英各自政治私利所驅(qū)動。
對美國而言,一方面,《新大西洋憲章》的簽署和發(fā)布是拜登執(zhí)政后擺脫“特朗普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干擾的又一次政策宣示。拜登希望以此重振美國全球領(lǐng)導(dǎo)力,確認“民主價值觀”,并推動“中產(chǎn)階級外交”。新憲章強調(diào)了雙方將捍衛(wèi)“民主和開放社會”的原則、價值觀和制度,致力于維持國際合作的機構(gòu)、法律和規(guī)范,承諾繼續(xù)為21世紀建設(shè)包容、公平、氣候友好、可持續(xù)、基于規(guī)則的全球經(jīng)濟。這些主張都否定了特朗普任內(nèi)“美國優(yōu)先”下的保護主義、本土主義,同時與美國前總統(tǒng)、80年前《大西洋憲章》的簽署者羅斯福的政策主張一脈相承。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深知拉住歐洲以及推動全球戰(zhàn)略仍需英國的密切合作,并希望以此為抓手發(fā)揮對其他盟友及伙伴的引領(lǐng)作用。拜登執(zhí)政后,迅速切換對中國及俄羅斯“大國競爭”的方式方法。拜登政府企圖利用與一些國家長期建立的文化和政治聯(lián)系,通過對民主、人權(quán)等西方價值觀的“再確認”,打造所謂“民主對威權(quán)”的陣營式對抗,以贏得這場“競爭”,這一點在拜登6月訪歐之行中可見一斑。盡管英國不再像1941年時那樣是美國的決定性盟友,也不是“印太大國”,但仍是在國際事務(wù)上與美國立場最為接近的盟友之一。正如在價值觀領(lǐng)域,英國方面提出的“民主十國”提議,為拜登政府發(fā)起召開“全球民主峰會”的倡議提供了靈感。因此,即使美英不具備聯(lián)手為全球“民主國家”設(shè)定議程的能力,但仍可以通過合作,引領(lǐng)和鼓勵其他國家在“大國競爭”中貢獻力量。
對英國而言,《新大西洋憲章》的簽署,是對英美“特殊關(guān)系”的確認,大大滿足了英國的面子。盡管英美在二戰(zhàn)中締結(jié)、冷戰(zhàn)中發(fā)展的“特殊關(guān)系”仍有牢固紐帶——英美在情報、安全等領(lǐng)域的合作是其他盟友無法企及的,但這種“特殊關(guān)系”是極不對稱的。單從英美“特殊關(guān)系”需要每一位美國新總統(tǒng)確認這一點來看,英國的不安全感可想而知。拜登執(zhí)政前對約翰遜評價不高,但仍將上任后首訪選定英國,并簽署《新大西洋憲章》,這無疑是約翰遜政府的重大外交成果。此外,英國也希望借《新大西洋憲章》簽署的東風(fēng),乘“美國歸來”之勢,充實“全球英國”的里子。《新大西洋憲章》確認了英美在價值觀和國際秩序上作為緊密核心的存在,這與英國政府致力于打造“全球英國”的目標相一致。因此,英國政府將積極策應(yīng)美國的戰(zhàn)略改變,成為美國的“麻煩解決者”和“責(zé)任分擔者”。
2021年6月10日,美國總統(tǒng)拜登到英國訪問并參加G7峰會。峰會前,拜登和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舉行會晤。
遠不能代表跨大西洋兩岸的共同愿景
對于美英達成的《新大西洋憲章》,西方戰(zhàn)略界普遍表示關(guān)注,認為新舊憲章的出爐背景頗為相似:1941年,美英達成《大西洋憲章》,是因為兩國面臨法西斯主義的挑戰(zhàn);而在當前,兩國同樣面臨一場艱難的挑戰(zhàn)——新冠疫情的“世界戰(zhàn)役”。然而,對比兩個憲章的時代背景與主角角色之變,《新大西洋憲章》除了確認美英特殊關(guān)系以及兩國共同堅持的價值觀原則外,并沒有推動國際社會進步的實際內(nèi)容。
從時代背景看,舊版憲章更像是一份強化反法西斯力量的行動宣言。憲章簽署時美國尚未參戰(zhàn),其主要目標是讓美國民眾清楚參戰(zhàn)是為了什么,以及提出重建二戰(zhàn)后世界和平與秩序的政策依據(jù)。而新版憲章的主旨并非提出全球抗疫的具體原則和政策主張,僅僅是對美英共同價值觀的再確認,主要目標仍然是夯實兩國“特殊關(guān)系”和重振西方所堅持的準則,維護西方主導(dǎo)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然而,當前的國際格局較80年前已經(jīng)發(fā)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隨著全球化和多極化日益深入,大國力量對比及互動呈現(xiàn)新特征,氣候變化、傳染病、核擴散等跨國威脅呼吁更為務(wù)實的大國協(xié)調(diào)及國際合作,而不是建立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的“朋友圈”。
再從美英當前的角色定位看,兩國企圖發(fā)揮引領(lǐng)西方世界的野心也面臨巨大掣肘。美國的綜合實力已不像20世紀40年代一樣處于全球主宰地位。近年來,美國的戰(zhàn)略資源從歐洲、中東轉(zhuǎn)向亞洲的趨勢,導(dǎo)致傳統(tǒng)歐洲盟友對美國的期待與依賴日益下降。因此,即使拜登在訪歐之行中不斷強調(diào)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性,法德等歐洲大國領(lǐng)導(dǎo)人也繼續(xù)表態(tài),強調(diào)要與美國修復(fù)關(guān)系,但這并不意味著歐洲國家在所有問題上與美國步調(diào)一致,歐洲不會因為拜登執(zhí)政而放棄謀求“戰(zhàn)略自主”。同時,美國國內(nèi)的政治極化、兩黨惡斗尤其是共和黨的反民主傾向,讓歐洲盟友心存疑慮:即使拜登執(zhí)政下的美國重返西方軌道,會不會也只是一次“回光返照”?
英國面臨的掣肘也再明顯不過。英國在80年前能夠代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如今脫歐后的英國僅能代表自己,連其歐洲盟友都拒絕被代表。“大國競爭”的時代背景已使歐洲國家更加確信,“歐洲才是前途所在”,抑制新冠疫情的蔓延也將使歐洲國家的權(quán)力日漸集聚到歐盟機構(gòu)之下。脫歐后的英國與歐盟漸行漸遠,已成為歐洲的“孤家寡人”。因此,《新大西洋憲章》簽署的意義也被牢牢限定為英美的雙邊宣言,遠不能代表跨大西洋兩岸的共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