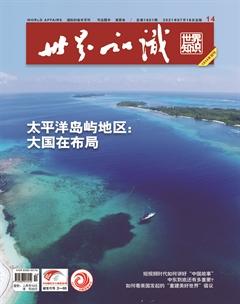應對氣候變化,非洲的立場和難點是什么
王一晨
2021年是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關鍵的一年”,以氣候變化為主題的國際雙多邊活動接連舉行。4月22日至23日,美國總統拜登舉辦其上任后的首次領導人氣候峰會,中、日、英、俄、聯合國、歐盟等近40國及國際組織領導人以視頻形式出席會議。會上,各國就進一步擴大減排、積極應對氣候變化達成重要共識。南非、尼日利亞、肯尼亞、剛果(金)、加蓬五個非洲國家領導人也受邀出席了峰會,呼吁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資金、技術、能力建設等方面的支持。
“貢獻”甚微,深受其害
非洲是世界上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碳排放量僅占全球排放總量的4%,且長期處于較低水平,與近年全球整體碳排放量顯著持續增長形成鮮明對比。雖然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貢獻”甚微,但由于地理因素以及經濟落后,非洲缺乏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比其他地區更加脆弱且易蒙受嚴重影響。《2019年非洲氣候狀態》報告指出,非洲大陸正在面臨因氣候變化所引發的一系列嚴重挑戰。一是海平面上升及海岸侵蝕。非洲多處海域海平面上升速度達到每年五毫米,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西非幾內亞灣及東南非印度洋西岸海域情況最為嚴重。二是極端天氣頻襲。近年來暴雨、臺風、干旱、洪水等自然災害在非洲大陸此起彼伏,造成大量人員傷亡或無家可歸。三是糧食安全風險提高。炎熱干旱所導致的糧食減產已成為非洲農業面臨的主要風險。四是媒介傳播疾病增加。氣候變化所導致非洲的高溫高濕環境大量滋生昆蟲,瘧疾、黃熱病等蟲媒傳染病的傳播進一步肆虐加劇。在2019年聯合國大會上,非洲48國領導人提及“氣候變化”一詞高達212次,可見非洲各國亟需國際社會援助解決氣候變化問題。2020年以來,氣候變化對非洲大陸影響日趨嚴峻,非洲經歷了洪水泛濫、蝗蟲侵襲、干旱加劇,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則令非洲因氣候變化所產生的長期性社會經濟問題進一步凸顯。
施策立法,減少排放
長期以來,非洲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氣候變化治理進程,幾乎全部非洲國家都加入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90%以上的國家簽署了《巴黎協定》。2006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發起“內羅畢框架”以促進非洲清潔能源發展;2007年,第八屆非盟首腦會議首次將氣候變化列為重要議題;2008年底,非洲各國環境部長通過《阿爾及爾宣言》;2009年初,非洲各國簽署《非洲應對氣候變化進程內羅畢宣言》,全面闡述非洲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
南非、尼日利亞、肯尼亞等南、西、東三大撒哈拉以南非洲次區域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態度積極,不僅相繼出臺氣候變化專門性國家政策和行動方案,還在此次領導人氣候峰會上再次強調了非洲國家到2030年減排32%的承諾。南非作為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基礎四國”(其他三國為巴西、印度和中國)之一,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國家氣候變化應對策略》,2011年通過了《國家氣候變化應對政策》,其中設定了短中長三個時期目標。2019年6月,南非正式實施碳稅法以控制國內溫室氣體排放。尼日利亞是參與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最早的非洲國家之一,政府相繼出臺了《國家氣候變化政策和應對戰略》等專門性國家政策戰略。肯尼亞作為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所在地,一直在非洲應對氣候變化領域成績突出。近年來,肯政府制定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戰略》的綱領性指導文件以及《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行動計劃》的具體行動指南。
發展低碳經濟,推動清潔能源轉型升級
走低碳發展道路,已成為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選擇。長期以來,非洲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受制于電力因素。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顯示,2019年非洲仍約有六億人用不上電。為在妥善應對氣候變化的前提下緩解電力赤字等發展問題,非洲各國加緊發展低碳經濟,推動清潔能源轉型升級。早在2015年,非盟就通過了《2063年議程》,提出將化石能源在總能源產量中的比例降低至少20%,將可再生能源在總能源產量中的份額提高至少10%,從而提升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2021年2月,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大力倡導升級基礎設施建設以提高國家新能源發電水平,從而轉變當下該國大量燃燒煤炭的能源結構。尼日利亞積極推廣清潔能源爐灶。在此次領導人氣候峰會上,肯尼亞總統肯雅塔表示:“清潔能源已經占肯總電力供應的90%,我們計劃到2030年將這一比例提高到100%。”
隨著全球逐步邁入清潔能源時代,各國對于煤炭、石油等傳統資源的需求逐步下降,但與此同時,為發展升級清潔能源技術,全球對于銅、鋰、鎳、鈷、稀土等關鍵礦物資源的需求卻與日俱增。國際能源署曾多次指出,隨著更多國家大力推動清潔能源轉型升級,獲取其所必須的關鍵礦產資源的難度也將越來越大。世界銀行發布報告稱,當下銅、鋁等關鍵礦產資源的利用率遠遠不能滿足全球可再生能源技術和儲能的需要。非洲礦產資源十分豐富,其礦產儲備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二。豐富的自然資源稟賦不僅為非洲實現自身清潔能源轉型升級提供良好條件,也令其在全球清潔能源技術競爭中占得先機。
2018年3月8日,索馬里多盧難民營的人們正在等待食物和水。2017年,嚴重的干旱曾席卷索馬里等東非國家,這些地方糧食安全受到了威脅。
應對氣變,挑戰重重
近年來,盡管非洲各國積極參與全球氣候變化治理進程,但仍在能力建設、制度執行、發展需求等領域面臨諸多挑戰,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恐將長期處于被動地位,承受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較大卻又只能仰仗國際社會的支持參與。
第一、非洲中小國家缺乏主動作為的能力基礎。除少數制造業水平相對較高的國家外,絕大多數非洲國家雖擁有大量可再生能源,具有發展清潔能源的比較優勢,但均囿于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等因素,難以擺脫傳統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在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時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制定較為寬泛的綱領性、宣示性政策文件而無力采取有效舉措,在極大程度上仍需依靠發達國家提供的資金技術支持。
第二、非洲大國落實氣候變化政策執行力有限。雖然南非、尼日利亞、肯尼亞等工業化程度較高的非洲大國均積極推進國內氣候變化相關政策立法,但政策“制定易、落地難”一向是非洲國家長久以來的通病。一方面,非洲國家缺乏穩定的政治結構,社會治理能力普遍較低,導致制度執行缺乏有效保障。另一方面,非洲大國面臨發展赤字,對西方發達國家仍存在一定戒備心理,擔心過于積極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發達國家承諾的援助又不到位,則最終很可能會損害自身發展能力,掉入發達國家設下的“氣候陷阱”。長期以來,歐美發達國家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將氣候問題轉嫁給廣大發展中國家,讓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承擔過多所謂“減排義務”。但事實恰恰相反,非洲大多數國家本身就處于“碳中和”甚至“負碳排放”狀態。今年3月,歐洲議會通過了“碳邊境調節機制”議案,將對歐盟進口商品征收碳稅。歐盟是非洲的主要貿易伙伴之一,也是非洲國家水泥、石油等產品的重要出口地。征收碳邊境關稅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非洲的出口成本,使得本就高度依賴原材料出口的非洲國家舉步維艱。非洲國家多次指責歐盟借征收碳關稅制造“貿易壁壘”。
第三、滿足發展需求仍是非洲目前第一要務。據統計,2000至2019年期間,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前30的國家中,美、日、德、法、英等傳統西方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均處于下降趨勢。而非洲眾多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從農業向制造業轉型的關鍵時期,非洲大陸自貿區正式啟動也刺激各國亟需提升本國制造業水平。如南非作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前20位中唯一的非洲國家,其排放量在英、法等傳統發達國家之上,且仍處于增長態勢。因此,為實現國內工業化從而大幅增加溫室氣體排放的情形很可能將在非洲大范圍出現。
眾所周知,單憑非洲一己之力是無法扭轉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在此次氣候峰會上,非洲國家領導人紛紛強調了對于“氣候融資”的急迫需求。非洲國家不僅需要發達國家承諾減排,更需要國際社會幫助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韌性和能力,為清潔能源轉型升級提供亟需的技術和資金援助。
一方面,歐美承諾的氣候變化援助資金需盡快到位。2012年通過的《坎昆協議》顯示,發達國家應在2020年前每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融資”,但據相關報告指出,這些數字遠未達到應有的水平。加上當前非洲經濟受到新冠疫情的沖擊,歐美等發達國家需真正落實對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融資、綠色能源領域的援助。
另一方面,中非綠色產業合作潛力巨大。習近平主席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指出,“中方將秉持‘授人以漁理念,通過多種形式的南南務實合作,盡己所能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能力。”“綠色發展”是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八大行動”之一,也是中非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中非環境合作中心已于2020年啟動,大批綠色環保和清潔能源合作項目已在非不斷落地。中國可利用既有合作平臺,對標非洲實際需求,進一步開發中非在可再生能源技術以及綠色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