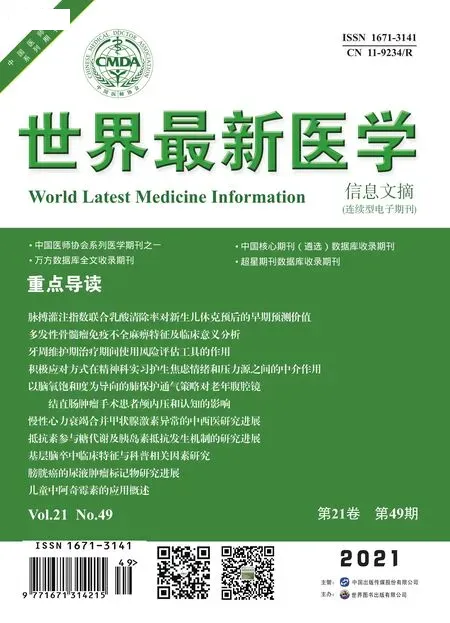針灸結合言語療法治療語言發育遲緩患兒的效果觀察
孫元華,吳曉靜
(漯河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第三附屬醫院兒科,河南 漯河 46200)
0 引言
語言發育遲緩是小兒發育性疾病,基于發育缺陷出現語言表達能力與理解能力缺陷[1]。現代臨床還未明確小兒語言發育遲緩的具體原因及發病機制,但綜合大量臨床實踐來看,與患兒腦組織感知功能異常之間存在密切關聯。除西醫病因之外,在中醫視角認為語言發育遲緩是五遲中的一種,與五臟發育情況均存在一定關聯[2]。為此,中醫范疇對語言發育遲緩的治療以整體治療及辨證施治為基礎原則。本次研究中,通過對80例語言發育遲緩患兒的分組調查,分析了針灸結合語言訓練治療方案的應用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抽取2017年6月至2020年6月住院治療語言發育遲緩患兒80例行對比調查,參考隨機抽樣法分組,將言語訓練療法40例患兒納入對照組,在此基礎上聯合針灸治療的40例患兒納入觀察組。對照組男女23/17例;3~6歲,均值(5.14±0.14)歲;出生體重 2.2~4.5kg,均值(3.64±1.05)kg。觀察組男女22/18例;3~6歲,均值(5.25±0.21)歲;出生體重2.4~4.4kg,均值(3.57±1.12)kg。納入標準:經系統檢查確診語言發育遲緩;調查前獲取患兒家長同意。排除標準:存在家族遺傳史;伴隨嚴重智力障礙與聽力障礙者。兩組患兒行年齡與性別等資料對比無差異性,符合對比調查選樣標準。
1.2 方法
對照組:語言訓練,具體如下:
(1)利用聲音等刺激聽覺,用手觸摸等觸覺性刺激,促使患兒可關注并隨活動事物持續追視,可應用玩具球等作為吸引工具。
(2)進行分類游戲,了解事物的屬性與特征及用途,逐漸構建事物類別觀念,包括依據顏色與大小等原則完成分組等。
(3)采用手勢符號訓練,帶領患兒到床旁說睡覺,并做睡覺的手勢符號,通過反復訓練加深患兒理解。也可在吃飯與穿衣服等行為中完成訓練。
(4)開展詞匯量擴充訓練,應用不同類型玩具與圖片做分類訓練,促使患兒逐漸形成動物概念分化。
(5)開展表達訓練,促使患兒模仿無法自然發出的音。
所有訓練均以一對一方式開展,30分/次,1次/天,治療3個月。
觀察組:針灸聯合語言訓練治療,具體如下:
(1)語言訓練方法與對照組一致。
(2)針灸取百會穴、四神聰、語言區、顳三針為主要穴位。對穴位對應皮膚消毒,采用一次性毫針平刺,留針30min,1次/天,治療3個月。
1.3 觀察指標
(1)以漢語版S-S評價法判斷語言發育遲緩治療效果。
(2)結合蓋澤爾發育量表評估患兒發育商,包括適應性行為與大運動行為及語言行為等5個功能區評價。采用韋氏智力量表評估患兒智商,涉及到知識與領域及詞匯等多項內容。
1.4 統計學處理
2 結果
2.1 組間患兒療效指標對比
觀察組中1例患兒治療無效,28例患兒達到顯效標準,11例患兒達到有效標準;對照組中6例患兒治療無效,22例患兒達到顯效標準,12例患兒達到有效標準,組間治療有效率對比有差異性(P<0.05)。
2.2 組間患兒發育商及總智商評分
治療前兩組患兒發育商與總質量測試結果無差異性(P>0.05);不同方案治療后觀察組患兒發育商評分(71.15±2.05)分,總智商評分(62.58±2.17)分,均大于對照組患兒的(55.24±2.16)分與(54.26±2.31)分,組間對比有差異性(P<0.05)。見表1。
表1 組間患兒發育商及總智商評分[(±s),分]

表1 組間患兒發育商及總智商評分[(±s),分]
組別 例數 發育商評分總智商評分治療前 治療后 治療前 治療后觀察組 40 34.26±3.52 71.15±2.05 45.26±2.31 62.58±2.17對照組 40 34.85±3.16 55.24±2.16 45.81±2.05 54.26±2.31 t-0.789 33.790 1.126 16.603 P-0.433 <0.01 0.263 <0.01
3 討論
發育遲緩多發生在3歲到7歲之間的兒童中,以語言發育遲緩發生率相對較高。持續語言發育遲緩可造成語言障礙,進而影響到患兒終身發展[3]。存在語言障礙的兒童除影響到其正常語言表達能力以及理解能力之外,還可對其社會適應能力與認知能力等造成一定影響[4]。兒童發生語言發育遲緩,可受到多種因素影響,但其具體發病機制當前還不清楚[5]。據大量臨床實踐以及有關調查結果,可總結出智力發展遲緩與特發性語言障礙等對于兒童語言發育遲緩的發生具有重要影響[6]。以智力發育遲緩因素為例,受到多種因素影響致使兒童大腦受到損傷,進而發展成為智力發育缺陷,對比同齡兒童其智力水平明顯較低。同時此類兒童還可存在一定適應性障礙現象,其常見原因為早產所造成的發育遲緩。以特發性語言發育障礙因素為例,也被稱之為是單純性語言障礙,具體為語言功能或能力發育遲緩,但其他方面發育正常,同時還需排除聽力障礙與自閉癥以及智力低下等癥狀。行為障礙可出現無法聽從指令或無法自主表達感受等表現。詞匯量發展與語言表達能力對于語言發育遲緩具有重要影響,而其具體引發原因可能為受到語言環境影響。語言發育遲緩,基于沒有明確癥狀以及病因,導致多數家長對于此病癥了解不足。且兒童發育遲緩在早期并不會出現明顯表現,致使多數家長不會在第一時間帶領患兒到醫院就診,為此可出現延誤最佳治療時機情況。林成認為對于兒童語言發育遲緩,早期診斷及有效干預對于改善預后具有重要作用。
大量臨床實踐證實多種疾病在早期發病階段可出現語言發育遲緩癥狀。以孤獨癥為例,語言發育遲緩與孤獨癥在臨床表現上具有一定相似性,為此在診斷及治療期間需做好有效鑒別工作[7]。孤獨癥多表現為社會交往障礙與語言交流障礙,以及刻板重復性行為等。存在自閉癥譜系障礙的兒童,也可表現為語言發育遲緩。以單純性語言發育遲緩為例,此類患兒的運動功能等與其他同齡正常兒童之間并無明顯差異,僅單純表現為語言表達能力缺陷。以智力發育遲緩為例,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導致患兒大腦受損致使其智力發育緩慢,對比同齡兒童可表現為智力水平下降,同時會伴隨語言發育遲緩表現。基于語言發育遲緩的引發原因不同,其治療方案也有所差異,需結合患兒具體癥狀以及病因做到針對性干預。
3歲以前是兒童發育的重要階段,在此階段中神經通路與條件反射的建立發育,代謝較強有效的刺激干預能夠促進腦功能代償適應[8]。尤其在2歲到3歲之間是語言發育的重要階段,同時也是行為塑造與特殊教育的關鍵階段。在此階段若能及時發現患兒存在語言發育遲緩問題,并給予針對性干預可有效提升治療效果。對于學齡前兒童語言發育遲緩的干預需采用有效手段進行語言功能鍛煉,逐漸培養患兒語言表達能力及理解能力。在具體治療方案選擇中,以語言訓練干預方式為主,同時可配合藥物治療與物理治療以及中醫治療等多種手段。
通過本次調查發現,不同方案治療后觀察組患兒發育商評分(71.15±2.05)分,總智商評分(62.58±2.17)分,均大于對照組患兒的(55.24±2.16)分與(54.26±2.31)分,組間對比有差異性。此結果充分證實了,在常規語言訓練干預方式基礎上加強針灸治療,可進一步提升綜合療效,包括促進患兒智商及發育上的提升。語言訓練方式可廣泛應用到多種類型語言發育遲緩患兒治療中。對于語言發育遲緩患兒早期給予一對一認知語言訓練,例如記憶鍛煉與聽覺鍛煉以及聽知覺鍛煉等。通過早期有效干預可通過改善語言環境以及增加患兒詞匯量等,來提升其語言表達能力以及日常交流能力。語言表達訓練通過聽說讀寫各種方式刺激激發大腦語言功能,促使其能夠實現重組,對于生理學水平的調整是借助于語言學以及聲學刺激反饋所實現的。基于語言訓練的原理以及其作用發揮,認為其能夠有效改善患兒語言發育遲緩癥狀,同時還可調整構音障礙問題。除此之外,在語言表達能力訓練期間,還可糾正與強化患兒自身不良行為,逐漸培養其社會適應能力,提升與他人之間的語言表達以及社會交往功能。
除語言訓練之外,中醫治療手段在小兒語言發育遲緩治療中也可發揮出顯著作用。在中醫范疇內認為小兒語言發育遲緩與五臟發育情況具有密切關聯。認為腦腎肺等發育情況均可影響到兒童的語言表達能力。在中醫學中經絡學作為主要構成部分存在經絡,學理論認為人體是統一且密不可分的整體而經絡關聯所有組成部分將各器官進行連接。若五臟六腑發育情況可影響到小兒語言發育遲緩,則可通過刺激對應經絡穴位,達到疏經通絡調理氣血的作用,最終發揮出治療語言發育遲緩的效果。取適當穴位針灸,可改善患兒五臟失和與氣血虛虧等情況,促進語言功能及智力水平的恢復。在針灸治療過程中,配合科學的語言訓練,通過雙向作用發揮,可進一步提升小兒語言發育遲緩治療效果。
綜上所述,語言發育遲緩患兒常規以語言訓練干預方式為主,而在此基礎上聯合應用適當穴位針灸,可進一步提升臨床療效,可促進發育商及總智商評分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