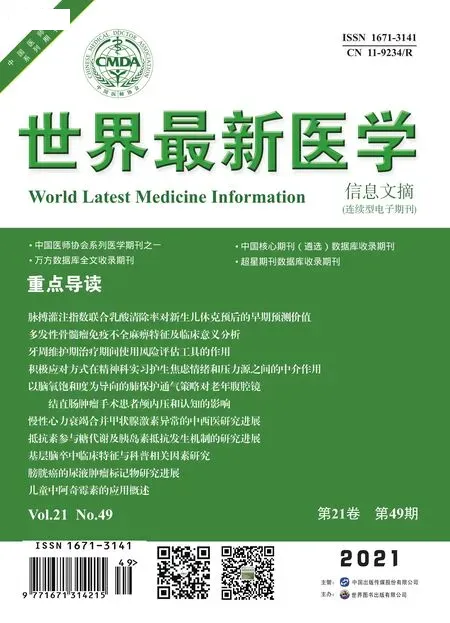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血管炎的診療體會1例
武昊,范曉勇,張明坤,劉元欽,黃傳江,喬珊,成亞嶺,和海榮,邱慧陽,劉廣存(通信作者*)
(1.山東大學,山東省千佛山醫院,山東 濟南 250014;2.山東第一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山東省千佛山醫院),山東 濟南 250014)
0 引言
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血管炎(primary angiiti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PACNS),是一種局限于大腦、腦膜或脊髓的血管炎。目前發病機制仍不明確,可能與細菌、病毒感染、自身免疫等因素有關。任何年齡均可發病,男女比例大約2:1,平均發病年齡約為50歲[1]。PACNS的臨床表現是多種多樣的,通常是非特異性的,有廣泛的鑒別診斷,包括惡性腫瘤、感染和其他結締組織疾病。頭痛是其最常見的癥狀,常伴有惡心和嘔吐,也可能發生認知狀態改變、行為改變和視覺障礙。還有一些少見的癥狀,比如癲癇、共濟失調、昏迷,體重下降、發熱等癥狀[2]。因其非特異性的體征和癥狀,并呈現多樣的實驗室和影像學表現,需要廣泛的檢查,以排除各種不同的鑒別診斷。PACNS作為臨床上重要的診斷挑戰之一,腦活檢仍然是其診斷的金標準。我們報告一例以腦卒中為首發表現、經腦活檢成功診斷的PACNS病例。
1 病例
患者為47歲男性,因“左側肢體活動不靈4天”收入山東第一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患者4天前無明顯誘因出現左側肢體活動不靈,伴有輕度頭痛。外院行CT見“缺血梗塞灶”(圖1),診斷為“腦梗死”,給予輸液治療,未見明顯緩解,現轉入我院。既往身體健康。神經系統查體:中年男性,神志清,精神可,語言流利,查體合作。顱神經檢查未見異常。左側肢體肌力III級,右側肢體肌力V級,四肢肌張力正常,腱反射無亢進,左側巴氏征(+),右側巴氏征(-),腦膜刺激征 (-)。

圖1 可見右側額顳枕葉不均勻密度影(外院誤診為缺血梗塞灶)
患者血細胞分析淋巴細胞百分比0.078(0.2-0.5);男性腫瘤全項、紅細胞沉降率、降鈣素原、免疫球蛋白定量測定、單純皰疹病毒抗體、巨細胞病毒抗體、凝血常規、肝功及腎功均正常。行腰椎穿刺術,壓力為200mmH2O,腦脊液化驗結果:白細胞:35×106/L;IgG:120mg/L(0-34mg/L);蛋白:74.5mg/dL(15-45mg/dL);其余腦脊液檢查均正常。
顱腦MRI:右側額顳枕頂葉、雙側基底節、丘腦及放射冠區見多發斑點狀、小片狀長T2異常信號,T2-FLAIR呈高信號,考慮肉芽腫性病變可能,腫瘤待排除(圖2)。

圖2 右側額顳頂枕葉T2-FLAIR呈散在高信號
根據患者病史、MRI及實驗室檢查,初步懷疑腫瘤或炎癥病變。考慮到治療方案的差異,決定行腦活檢術給予確診。征得患者及家屬同意后,行腦活檢術,病理回報(圖3):送檢組織為大腦皮質及白質,皮質及白質內可見多灶性梗死,局部散在少量吞噬細胞;梗死灶周圍腦組織水腫,微囊變及膠質細胞增生;軟腦膜及腦實質內中、小血管壁多量淋巴細胞浸潤,血管周圍出血、水腫;考慮為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血管炎。

圖3 HE染色×100
結合患者病史、實驗室檢查、MRI及病理結果,診斷為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血管炎。給予甲潑尼龍琥珀酸鈉80mg,BID,靜滴,并逐漸減量,患者于11天后出院,出院后每日口服甲潑尼龍片20mg。患者于接受激素治療25天后復查MRI(圖4),病灶明顯減少,癥狀明顯好轉。我們使用改良Rankin量表(mRS)評估患者的恢復情況:0-無神經體征或癥狀;1-無明顯殘疾,但有癥狀;2-輕微殘疾(能夠獨立處理自己的事務,但不能完全恢復以前的活動);3 -中度殘疾(能獨立行走,但無法自理);4-中度殘疾(無法照顧自己的身體或無法獨立行走);5-嚴重殘疾(需要持續護理和照顧,臥床不起,失禁);6-死亡。臨床定義良好結果為mRS≤2。我們報道的這名患者剛入院時mRS=4,輪椅入院,在攙扶下可以勉強維持站立;經過25天的系統治療后,患者mRS=2分,日常生活可以獨立完成,可以獨立行走。

圖4 右側顳頂葉T2-FLAIR呈點狀高信號
2 討論
PACNS是一種罕見的疾病,發病率為每年2.4/100萬例,一般為緩慢起病,可有緩解和復發,也可呈進行性加重。此病常無特異性癥狀或體征,臨床表現與受累血管及病理分型有關。頭痛為最常見的首發癥狀,其他常見的癥狀有感覺障礙、意識障礙、偏癱、偏盲等。PACNS預后差,及時治療可改善預后,所以及時的確診有助于更早的治療,從而改善預后。血清學檢查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排除其他相關疾病。部分PACNS患者可見紅細胞沉降率、C反應蛋白輕度升高。CSF結果雖然對PACNS不具有特異性,但可用于鑒別感染和惡性疾病。在PACNS患者行腰椎穿刺,顱內壓通常無明顯升高,常表現為無菌性腦膜炎。腦脊液分析顯示80%~90%的患者有異常,典型的PACNS患者表現為輕度淋巴細胞增多或蛋白水平升高[3]。更罕見的是寡克隆條帶或IgG升高[2]。MRI是診斷PACNS最敏感的影像學檢查,常見的表現為皮層下白質、深部灰質、深部白質、皮層呈T2-FLAIR高信號。腫瘤樣病變也很少見,僅在5%~15%的患者中可見[4],腫塊病變在MRI上與惡性腫瘤很難區分,因此必須通過活檢證實。DSA可提高顱內血管炎的診斷率,其典型表現是動脈交替性的狹窄和擴張,也就是常說的“串珠樣改變”,但會有40%的PACNS患者DSA 表現正常[5]。腦活檢是診斷PACNS的金標準,對排除感染性疾病和惡性腫瘤至關重要。在考慮診斷PACNS之前,應仔細排除其他疾病,因為用于PACNS的免疫抑制治療可能會加重感染性疾病或淋巴瘤。可逆性血管收縮綜合征(reversible cerebral vasocon-strictionsyndrome,RCVS)是最重要的鑒別診斷之一,RCVS發生在女性患者中明顯較多,平均發病年齡為42歲。患者經常表現為突發的頭痛或反復發作的霹靂性頭痛。在使用血管活性藥物、偏頭痛、高血壓、子癇或產后期間的患者中更為常見。PACNS患者更容易出現缺血性卒中和腦出血,RCVS更容易引起蛛網膜下腔出血和血管源性水腫[6]。RCVS與 PACNS相鑒別的關鍵點是在沒有并發腦出血的情況下,RCVS患者腦脊液化驗中白細胞及蛋白一般正常,并且RCVS活檢無異常發現。PACNS的治療非常具有挑戰性,沒有隨機對照試驗來指導,目前的證據僅僅是基于回顧性研究和專家意見。指南推薦PACNS的治療方案是糖皮質激素聯合免疫抑制劑[7]。PACNS總體預后較差,早期診斷并開始治療可明顯改善預后。
本病例中患者以卒中為首要表現入院,僅行CT檢查易診斷為腦梗死,外院根據CT及臨床體征誤診為腦梗死,并按照腦梗死行輸液治療,患者無明顯改善。我們注意到了患者CT中右側額顳枕葉不均勻密度影,并立即行MRI檢查,發現患者右側額顳頂枕葉散在多發病灶,初步懷疑患者為顱內炎癥性病變。為了證實我們的診斷,我們行腰椎穿刺術化驗腦脊液,并完善了男性腫瘤全項、紅細胞沉降率、降鈣素原、免疫球蛋白、單純皰疹病毒抗體、巨細胞病毒抗體等血液學檢查,結果顯示血液學檢查均正常,患者腰椎穿刺示顱內壓力為200mmH2O,腦脊液白細胞:35×106/L,患者腦脊液中白細胞的輕度升高更加證實了我們的判斷,但我們卻沒有意識到腦脊液中蛋白和IgG均明顯升高的意義,這使我們忽視了對PACNS的鑒別診斷。所以我們并沒有行腦血管造影,而是直接行腦活檢明確病變性質。Al Share等人斷言,多達25%的腦活檢可能是假陰性[8],在我們的病例中,患者通過腦活檢成功得出了PACNS的診斷,患者通過應用甲潑尼龍琥珀酸鈉,恢復良好,復查MRI治療效果顯著。
3 結論
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血管炎具有非常高的診斷難度,此病沒有特異的臨床表現,頭痛為最常見的癥狀,卒中比較少見,發生卒中時需要與腦梗死相鑒別,若磁共振檢查示腫瘤樣病變需要與腦腫瘤鑒別,當考慮為炎癥性病變時,應行腰椎穿刺,腦脊液中淋巴細胞、蛋白或IgG的升高均會提示我們PACNS的可能性。腦組織活檢是診斷PACNS的金標準,高度懷疑PACNS應盡早行腦活檢術,以便早期進行明確的治療。但在活檢之前,應先行腦血管造影,腦血管造影可以進一步確定我們的診斷,并且創傷更小,還可以明確具體的病變血管,提高腦活檢的陽性率。總之,PACNS是臨床上的一個重要的診斷挑戰,因其在治療上與缺血性疾病、腫瘤、炎癥性疾病上具有差異,在懷疑本病時應謹慎的鑒別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