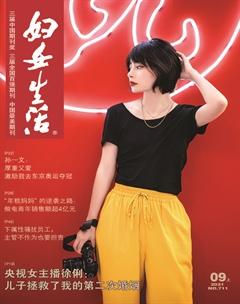三對革命伉儷是怎樣教育自己孩子的
走進(jìn)甘祖昌、谷文昌、焦裕祿的家庭生活,會發(fā)現(xiàn)一個(gè)共同點(diǎn),即對子女和親人“不近人情”,對老百姓卻“溫潤人心”。甘祖昌與龔全珍、谷文昌與史英萍、焦裕祿與徐俊雅這三對革命伉儷以紅色家風(fēng)、清白家風(fēng),彰顯了“先大家后小家,為大家舍小家”的家國情懷。
三對革命伉儷是怎樣教育自己孩子的
“把光榮傳統(tǒng)留給后代”
1953年,甘祖昌與龔全珍在新疆喜結(jié)連理。之后的33個(gè)春秋,龔全珍陪伴在甘祖昌身邊,一起經(jīng)歷了從“開國將軍”到“農(nóng)村老表”的轉(zhuǎn)變,也共同挑起了“老紅軍的擔(dān)子”。甘祖昌為鄉(xiāng)村集體生產(chǎn)和群眾生活日夜操勞,龔全珍則獻(xiàn)身于鄉(xiāng)村教育事業(yè)。用他們兒女的話來說:“爸爸是農(nóng)業(yè)社的爸爸,媽媽是學(xué)生們的媽媽。”
1957年,甘祖昌、龔全珍攜全家從新疆回到家鄉(xiāng)江西省蓮花縣坊樓公社沿背村務(wù)農(nóng)。甘祖昌堅(jiān)決拒絕組織上給他家蓋房子,而是和弟弟們擠住在老祖屋里。夫妻二人還無私地拿出工資支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助鄉(xiāng)村設(shè)施建設(shè)、幫助有困難的鄉(xiāng)親。僅鄉(xiāng)政府有據(jù)可查的捐助,金額就達(dá)8.5萬元。
有人問甘祖昌:“你把錢都用到大家的事情上去了,這當(dāng)然好,可也得為子女想一想,你什么也不留給他們嗎?”甘祖昌回答:“我們要把光榮傳統(tǒng)留給后代。”
他們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一家人剛從新疆回到老家的第三天清早,天還未大亮?xí)r,沿背村的屋場上就出現(xiàn)了“一大五小”的撿糞隊(duì)。除了每天清早撿糞,甘祖昌還給五個(gè)小孩布置了寒暑假割草任務(wù):12歲以上的孩子,割草240斤;10歲到12歲的孩子,割草120斤;8歲的孩子,也要割五六十斤。
1962年,弟弟們和甘祖昌分了家。當(dāng)時(shí),龔全珍吃住在學(xué)校,只有每周六晚上回家一趟;甘祖昌則忙著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早出晚歸地不著家。家里除了大兒子上初中住校、小女兒因無人照看而送給三叔家代養(yǎng)以外,還有剛剛小學(xué)畢業(yè)的小兒子、8歲的大女兒、6歲的二女兒和4歲的三女兒。沒有大人在家怎么辦?13歲的小兒子人小志氣大,帶頭承擔(dān)起家務(wù),他一個(gè)人擇菜、洗菜、炒菜,還割豬草、剁豬食,三姐妹則幫助哥哥燒飯、喂雞。
1966年,小兒子讀書離開家后,家務(wù)接力棒傳到妹妹手中。到了年底,三姐妹掙了1000多工分。當(dāng)?shù)弥@些工分只夠吃飯、不夠買衣服和繳學(xué)費(fèi)時(shí),大女兒認(rèn)真地叮囑兩個(gè)妹妹:“以后放假咱們更要多干活,多掙工分。”社員聽到她的話后,哈哈大笑:“你們的爸爸媽媽都有工資,還供不起你們?還用自己掙工分?”大女兒認(rèn)真地回答:“我們不用他們供養(yǎng),我們要自己供養(yǎng)自己!”
就這樣,甘祖昌和龔全珍將生產(chǎn)勞動上艱苦奮斗、生活作風(fēng)上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tǒng),作為家風(fēng)傳給了孩子們。
“不帶私心搞革命”
1952年,同是南下干部的谷文昌和史英萍在福建省東山縣結(jié)婚。從此,作為夫妻加戰(zhàn)友,史英萍和谷文昌風(fēng)雨同舟、比翼雙飛。谷文昌不僅在日記本上寫下“不帶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為人民”的赤子心聲,更用實(shí)踐行動譜寫了公仆精神;史英萍則是克服右手殘疾帶來的不便,擔(dān)起了撫育子女成長的重任。
一次,二女兒觀看電影《上甘嶺》,回家興奮地向家人講述電影情節(jié)。谷文昌冷不丁地問一句:“誰給你買的票?”二女兒回答:“收票的叔叔知道我是你的女兒,就放我進(jìn)去了。”
谷文昌很生氣:“縣委書記的孩子就可以搞特殊嗎?縣委書記的孩子更應(yīng)該按規(guī)矩買票!”他當(dāng)即拿出錢,讓二女兒去補(bǔ)票。這不僅是補(bǔ)一張電影票,補(bǔ)的還是“公私分明”的價(jià)值觀。
植樹造林,治理東山島的風(fēng)沙,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是谷文昌的夙愿。谷文昌剛提出種樹想法時(shí),老百姓眾說紛紜,認(rèn)為“這個(gè)縣長要做白日夢”,因?yàn)椤皷|山要能種活樹,那水就不往低處流了”。
此前,國民黨政府派的一個(gè)縣長也做過“種樹夢”,但終因政權(quán)腐敗,一棵樹也沒有種活。如今,共產(chǎn)黨人擔(dān)任的縣長能種活樹嗎?谷文昌先是帶領(lǐng)全家人嘗試種樹,然后跟林業(yè)站的同志們反復(fù)考察和調(diào)研,進(jìn)行小規(guī)模種植試驗(yàn),終于找到了適合東山沙土的樹種——木麻黃,并發(fā)現(xiàn)了種植木麻黃的最佳時(shí)機(jī)和方法。經(jīng)過堅(jiān)持不懈的努力,到20世紀(jì)60年代,38公里的東山島海岸線上筑起了一道“綠色長城”,全島412座山頭穿上“綠衣裝”。
作為南下干部的史英萍,在1952年就被定為行政18級,論工作能力、工作表現(xiàn)和文化程度也毫不遜色,可每次縣領(lǐng)導(dǎo)班子要給她提職、提級,都被谷文昌攔住。僅僅因?yàn)樗枪任牟钠拮樱诼殑?wù)和工資上竟然長達(dá)32年都沒有提升過。直到1984年,谷文昌去世后的第三年,史英萍才按照政策提升為行政17級。
對此,史英萍無怨無悔。谷文昌去世后的一周內(nèi),史英萍就按照“老谷生前的交代”,拆了家里的電話,連同自行車一并上交給縣里。
“不要隨隨便便向組織上提要求”
1950年,徐俊雅結(jié)識了焦裕祿。徐俊雅全力支持焦裕祿工作,與他一起到大連起重機(jī)廠實(shí)習(xí),還與他一起奔赴受災(zāi)縣蘭考,接受“除三害”的嚴(yán)峻考驗(yàn)。
不能不勞而獲,要靠自己本事生活,是焦家家風(fēng)第一條。焦裕祿大女兒初中畢業(yè)后,蘭考縣的一些單位送來招工通知書,有小學(xué)教師,有郵局話務(wù)員。大女兒很想去,但焦裕祿不同意。他對相關(guān)單位的同志說:“她長這么大,還沒有參加過體力勞動,一定要找個(gè)又臟又累的活讓她干,補(bǔ)上勞動這一課。”最終,大女兒來到蘭考縣食品加工廠上班。在焦裕祿的“特殊關(guān)照”下,她被分配到最苦、最累的醬菜組,以至于一段時(shí)間里她認(rèn)為父親不喜歡自己。直到一天早上,焦裕祿陪她一起挑醬油擔(dān)子,沿街叫賣,還親身示范,教她挑擔(dān)子要領(lǐng),她才真正領(lǐng)會到父親希望她吃苦耐勞、靠自己本事生活的良苦用心。
1964年,焦裕祿臨終時(shí)對大女兒說:“我死后沒有什么可以留給你的,只有家里的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他還把唯一值錢的一塊二手羅馬牌手表送給了她,并叮囑道:“你戴上它,上班不要遲到。”
“工作上向先進(jìn)看齊,生活條件跟差的比”,是焦裕祿給孩子們的最多教導(dǎo)。在孩子們眼中,焦裕祿是慈愛的父親,也是“摳門”的家長。1963年,5歲的二兒子嫌豆面饃太硬不好吃而隨手扔在地上,這也就有了那個(gè)廣為人知的“一塊豆面饃”的故事。長大后的二兒子在蘭考工作多年,像父親一樣訪貧問苦,為百姓解決實(shí)際問題。
在焦裕祿逝世后的40多年漫長歲月里,徐俊雅牢記焦裕祿“生活上要艱苦一些,不要隨隨便便向組織上提要求”的最后叮囑,再苦再難都不向組織伸手,不僅承擔(dān)起贍養(yǎng)兩位老母親、撫育六個(gè)年幼子女的家庭重任,而且肩負(fù)起焦裕祿精神的傳承責(zé)任,對當(dāng)年焦裕祿救活的孩子張繼焦也負(fù)責(zé)到底。
(摘自2021年3月30日《解放日報(bào)》 作者:崔海英)
【編輯:陳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