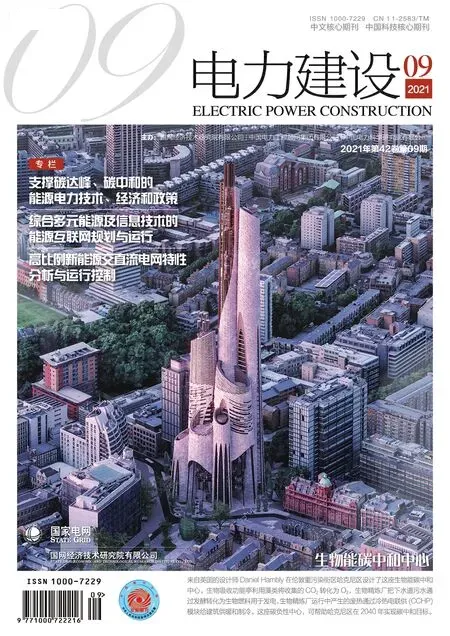計及無功裕度的配電網兩階段無功優化調度策略
胡戎,邱曉燕,張志榮
(智能電網四川省重點實驗室(四川大學),成都市 610065)
0 引 言
我國目前正不斷加大現代配電網的建設力度,使其能夠滿足各類可再生能源、儲能裝置、電動汽車等多元化負荷發展和接入需求,構建低碳環保、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1-2]。然而隨著電網中可再生分布式電源(renewable distributed generation,RDG)的滲透率不斷提高,其出力的間歇性和隨機性給配電網優化控制運行帶來的影響也逐漸增大,使得有必要充分挖掘多類型無功設備調節潛力,從“源-網-荷-儲”多維度研究配電網無功優化問題[3-4]。
由于配電網處于系統末端,點多面廣、接線復雜、數據龐大,基于目前高比例RDG分散接入、電網可調資源不斷增多的局面,文獻[5]利用斯皮爾曼相關系數分析了RDG之間的出力相關性系數對無功優化的影響,為調度人員提供參考依據;文獻[6]考慮了RDG無功支撐和開關重構,結合風光典型場景數據,利用魯棒優化對配電網進行兩階段無功優化,既考慮了系統運行狀態時變特性,又考慮了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文獻[7]從負荷均衡分布的角度考慮負荷需求響應和不確定性,協調日前優化和實時調控,降低光伏和負荷預測誤差的影響,充分挖掘無功設備調節的潛力;文獻[8]采取“靜態優化-離散變量優化-連續變量優化”多階段優化方法,在限制電容器組(capacitor bank,CB)和有載調壓變壓器(on load tap changer,OLTC)投切次數以兼顧經濟效益和設備使用壽命的同時,協調RDG和靜止無功補償裝置(static var compensator,SVC)的無功調節能力;文獻[9]通過預測日前市場價格,在電力市場環境下利用隨機模型預測控制對主動配電網進行動態有功/無功聯合優化調度,充分挖掘“源-網-荷-儲”互動潛力,提高了電網應對高比例RDG接入后“源-荷”端不確定性的能力;文獻[10]通過“松弛-聚類-校正”三步實現動態無功優化解耦,確定電容器組實際投入容量后再通過DG、SVC進行二次靜態無功優化,充分考慮了各無功控制設備的無功出力特性。
上述文獻對適應配電網運行態勢時變性和RDG接入后的波動性都進行了相關研究,但目前大量可調資源接入配電網情況下的無功優化研究存在的問題有:1)針對多元化可調資源接入配電網的無功優化研究不夠全面,隨著配電網中SVC、風光等具備動態無功補償能力的裝置投入量增加,結合快慢時間常數各異的無功調節裝置進行協同優化才能夠適應配電網“多目標”、“多維度”的有功-無功綜合優化;2)針對間歇性和波動性的可再生能源滲透率提高帶來的功率平衡問題需要在優化過程中描述其不確定性和相關性,降低多重不確定性對系統供電的影響;3)在日前調度環節僅考慮電壓幅值處于約束范圍內,不利于保障短期或實時調度計劃具備充足的備用容量來控制無功,需要合理規劃系統的動態無功儲備。
綜上問題與分析,本文針對高比例可再生資源接入配電網的無功優化問題,充分考慮風光出力不確定性和相關性的影響,基于Copula理論生成風機和光伏典型日出力場景;然后根據無功補償裝置響應速度的不同,在保障連續補償裝置動態無功裕度的基礎上優先調節離散變量,同時對配電網中所有可調資源進行整體控制,實現配電網日前調度階段的有功-無功協調優化;接著,利用連續無功補償裝置和儲能快速響應可再生能源波動產生的功率需求,實現配電網日內無功優化,進而在2個時間層面上分階段達到不同調節速率無功補償裝置間的時序配合和差異化管理的目的;最后,借助擴展ε約束法和GRUOBI建立的求解兩階段優化模型,驗證所提策略的經濟性和可靠性。
1 不確定性建模
特性迥異的RDG和負荷接入配電網后,系統調度人員在進行調度決策時需要應對源-荷不確定性對配電網供電可靠性造成的顯著影響。由于同一地區的風能和太陽能往往呈現一定程度的相關性[11],如果忽視其不確定性和相關性勢必會對配電網的運行造成一定的影響。Copula函數通過聯合分布模型較好地刻畫了變量間的非線性相關性[12],因此,本文基于Copula理論建立新能源發電單元模型。
1.1 風光概率場景構建

(1)
(2)


(3)

對每個時段的聯合概率分布函數進行采樣,并根據采樣結果和風光的聯合概率分布函數反變換得到每個時段的采樣風機和光伏出力。由于采樣數X較大,不利于計算,因此采用模糊c均值聚類法[14]對X組采樣結果進行聚類,最終生成考慮風光相關性和隨機性的S個典型日場景曲線,并計算各場景出現的概率。
1.2 負荷模型
現有文獻通過核密度估計、擬合方法獲得了負荷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數,本文采用正態分布描述負荷的隨機波動性[15]。
(4)
式中:PL、QL分別為負荷有功功率、無功功率;σL、μL為負荷有功功率的標準差和期望值;φL為負荷的功率因數角。考慮到負荷功率因數通常在0.9~1.0之間變化,變化范圍較小,且無功與有功正相關,本文假定負荷功率因數恒定。
2 計及無功裕度的兩階段協調優化策略
2.1 第一階段有功-無功優化調度模型及求解方法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在電網的滲透率愈高,解決其不確定性帶來的過電壓和功率阻塞等問題的需求就愈發迫切[16]。因此,在配電網中,日前長時間尺度無功調度過程在保證電壓偏差盡可能小的同時,需要增強短時或實時調度期間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此時優先協調配電網中的離散無功補償裝置能夠為連續無功補償裝置在日內優化階段應對風光不確定性引起的電壓波動預留更多的動態無功裕度。綜上,第一階段優化調度模型將離散設備調節的經濟指標納入成本中,以系統的運行成本最小、節點電壓偏差最小以及無功裕度最優為目標函數,綜合優化長時間尺度下快慢無功設備的控制方式,實現配電網有功-無功優化。
2.1.1 目標函數
1)運行成本F11最小。
(5)
(6)

2)電壓偏差F12最小。
(7)

3)無功裕度最優。
風光在向電網輸出有功的同時也能夠提供一定的無功余量,可與SVC一起作為配電網中的連續無功調節裝置。為了避免過度調用動態無功資源進而削弱系統應對波動和突發故障的能力,在第一階段調度過程中盡可能保證其無功裕度更大,定義目標函數F13為:
(8)

綜合上述3個子目標,總目標函數F1為:
minF1=min(F11,F12,F13)
(9)
2.1.2 約束條件
1)潮流約束。
(10)
(11)

2)系統運行安全約束。
(12)
式中:Ui,max、Ui,min分別為節點i的電壓上、下限;Iij,max、Iij,min分別為支路i→j流過的電流最大、最小值。
3)配電網與主網交互功率約束。
(13)

4)CB運行約束。
CB作為離散型無功補償裝置,出于延長使用壽命的考慮對其每日操作次數進行限制[18]。約束條件為:
(14)

5)OLTC運行約束。

(15)

6)SVC運行約束。
(16)

7)ESS運行約束[20]。
(17)
(18)

8)風電/光伏機組運行約束。
為了避免棄風棄光現象,本文風光有功功率均認為全部消納,即:
(19)

(20)
此外,本文按工程應用要求認為風電機組在運行過程中還應該滿足接入點處功率因數的要求,則對風電機組,有:
(21)
式中:PL,j,t、QL,j,t分別為節點j處有功、無功負荷。
2.1.3 求解方法
所建立的有功-無功協調優化模型屬于非線性混合整數模型。為了避免人工智能算法提前早熟的現象,選用二階錐松弛將其轉換為線性混合整數凸函數后,可以調用成熟的商業軟件CPLEX、GUROBI等進行求解,具體轉換過程見附錄A。由于第一階段為多目標優化模型,考慮到加權法對混合整數模型處理效果不理想,利用文獻[21]提到的擴展ε約束法,結合GUROBI對歸一化后的多目標函數求解可以得到有效的帕累托前沿和帕累托最優解集,具體步驟如下:
1)計算支付表。

2)計算3個子目標的跨度值。
(22)

3)轉換目標函數。
以F11為主目標,F12、F13為約束目標,利用擴展ε約束法將多目標問題轉換為單目標優化問題,描述如下:
(23)
約束條件除式(10)—(21)外,還包括:
(24)
式中:e2、e3均為中間變量;r2、r3為F12、F13的跨度值;q2、q3分別為r2、r3的等間距間隔數;m2、m3為新增約束條件的松弛變量;a為一常數,取值范圍[21]為10-6~10-3。
所得的單目標優化問題利用GUROBI直接進行求解,得到帕累托最優解集后進一步采用灰色關聯投影求取最優折衷解[21]。第一階段求解步驟如圖1所示。
2.2 第二階段無功優化調度模型及求解方法
考慮到風光不確定性對電壓穩定性的影響,為了兼顧配電系統的電壓安全以及連續無功裝置的可控性,第二階段的日內優化控制根據第一層離散無功裝置的投切結果,將變壓器檔位和電容器組數固定,在相鄰投切間隔內根據實時的風光功率波動與電壓調整的需要優化動態無功補償裝置,此時以將各節點電壓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作為目標函數:
(25)
式中:M為相鄰投切間隔。

圖1 第一階段有功-無功優化調度模型求解流程Fig.1 Solution method of optimal active-reactive power dispatch model in the first stage
約束條件為式(10)—(13)、式(16)—(21)。
此時,OLTC、CB作為常量將不再進行調節,而是利用SVC和風機/光伏的無功輸出能力進行動態無功電壓優化控制,儲能仍然作為可控有功源參與優化。此階段既避免了離散設備的頻繁調節,保證系統快速響應無功變化,又最大化利用了系統內的可調資源,實現了動作時間常數不同的無功補償設備在不同時間尺度上的協同優化。
第二階段建立的非線性非凸優化模型仍然可以采用二階錐松弛轉換為線性凸函數,此時即為單目標線性優化,可直接調用GUROBI進行求解。
3 算例分析
3.1 算例系統說明
以改進的IEEE 33節點系統為例且保持原有線路參數不變[22],如附圖B1所示。其中,OLTC等效為變電站節點,變比調節區間為[0.95,1.05],共11個檔位,分接頭每日允許的最大動作次數為5次。CB單位容量為25 kV·A,共安裝10組,每日允許的最大動作次數為5次;SVC調節范圍分別為-100~400 kV·A、-100~600 kV·A;風電機組接入容量為1 000 kW,光伏機組接入容量為800 kW;儲能電池額定容量為1 200 kW·h,最大充放電功率為300 kW,充電效率為93.87%;節點電壓的變化范圍為[0.95,1.05] pu,根節點的電壓設為1 pu。變電站關口的無功上、下限分別為4 MV·A和0 MV·A,有功上、下限分別為8 MW和0.5 MW。支路最大電流為400 A;電壓基準值為12.66 kV,功率基準值1 MV·A。
為了獲取新能源出力,本文選取如附圖B2所示的寧夏某地2017年全年風光出力實測數據,基于風光出力具有負相關互補性的事實利用Frank函數進行Copula相關性擬合,得到風光聯合概率分布函數。按照上文所述步驟聚類縮減為4個典型場景,如圖2所示。

圖2 考慮風光相關性的場景生成結果Fig.2 Scene generation results considering correlation
從圖2中可以看出,每個時段的風光出力均具有相反或一致的變化趨勢,表現出了一定的正相關或負相關性。場景1和場景2風速處于平均水平,但場景1的光照強度更大;場景3光照強度較大但風速最為平穩;場景4風速水平相對較高但光照強度相對最弱。可見場景縮減結果表征了當地不同氣候環境下風光出力變化特性,涵蓋了全年風光變化趨勢,同時體現出兩者的相關性和不確定性,有利于電網后續的優化運行。
3.2 結果分析
3.2.1 第一階段優化情況
第一階段重點分析計及無功裕度后有功-無功協調優化方案在經濟性和安全性上的性能,選取不考慮儲能有功調節能力,僅做無功優化的方案為方案1,本文采取的有功無功協調優化方案為方案2,電價信息和負荷預測數據見附表B1和圖B3。2種方案的折衷解對比如表1所示,節點電壓對比如圖3所示。

表1 折衷解對比Table 1 Comparison of compromise solutions

圖3 節點電壓對比Fig.3 Comparison of node voltages
由圖3和表1分析有功無功協調優化的優越性,方案1雖然能夠一定程度上調節電壓偏差,保障電網安全運行,但在18:00—22:00,風光出力水平均較低,負荷處于高峰時段,節點2的電壓最高達到了1.044 pu。由此可知,僅考慮無功優化仍有可能出現電壓越限的情況。方案2的節點電壓最高值為1.034 pu,全天電壓總偏差由4.840 8 pu降至4.547 3 pu,且儲能系統的有功出力能夠提供一定的電壓支撐,在風光出力較小的時段,電壓幅值相較方案1有所提升,證明了充分調動配電網中的有功無功可調資源對電壓的優化效果更為明顯。
表1還表明了在協調優化下的總電壓偏差降低了6.1%,無功裕度指標更優,而從經濟性角度來看,計及無功裕度的有功無功協調優化由于儲能的參與會增加一定的控制成本,但是能夠均衡潮流分布,同時保證更富余的動態無功儲備,因此雖然在運行成本上,本文所提方案改善不明顯,但總體而言所獲效益更優。2種方案下的優化結果對比如圖4所示。
由圖4分析離散無功補償設備動作和儲能充放電情況,鑒于在日前優化調度階段對離散無功補償裝置投切次數進行了限制,CB和OLTC在實現無功就近補償、滿足負荷需求的同時,還要承擔連續無功補償設備為日內優化調度階段預留的無功補償能力,因此,在有功無功協調優化的方案下,OLTC投切檔位較高。儲能裝置在風光出力較大的時段進行充電,此時負荷相對處于低谷階段,系統多余的無功由儲能裝置消納,防止電壓水平過高;18:00—22:00時段,電價較高且負荷處于高峰時段,為了保障系統的安全運行,儲能向系統注入一定量的有功功率,實現削峰填谷,保障節點電壓始終處于約束范圍內,也避免了離散無功補償裝置的頻繁動作。因此,在僅考慮無功優化的方案中,CB和OLTC動作次數分別增加了5次和3次,才能更好地應對新能源波動和負荷需求。同時,圖4(a)表明方案2中主網注入的有功功率總體較方案1更少,證明了有功無功協調優化能夠通過調節儲能的有功出力減少從主網的購電量,在風光波動的情況下具有靈活抑制從主網注入功率波動的能力,消納可再生能源的能力和對主網的友好性有所提升。

圖4 優化結果對比Fig.4 Comparison of optimization results
連續設備無功出力對比如圖5所示。由圖5分析連續設備的無功出力,當目標函數中計及動態無功裕度時,連續無功補償裝置大部分時間的投入都會更少,且變化趨勢也較為平穩。由于RDG的無功調節極限取決于有功出力,對于14節點處的光伏機組,其夜間無功裕度充足,白天則主要集中輸出有功,能夠與風電形成互補,為了避免無功長距離流動,計及連續無功補償裝置的無功裕度后也會盡可能先調用附近的電容器補償支路末端無功,證明了在動態無功裕度指標的作用下動態無功儲備增多,有利于維持電壓穩定性。根據各類無功補償裝置響應速度的不同,由離散設備承擔基礎的無功支撐,在日前優化階段盡量避免動態無功的浪費,SVC則實時應對風光等不確定性因素產生的無功缺額,能夠實現無功電壓調控設備的協調配合。

圖5 連續設備無功出力對比Fig.5 Comparison of continuous reactive power outputs of compensation devices
3.2.2 第二階段優化情況
第二階段重點分析利用動態無功容量應對系統功率波動的能力以及儲能充放電特性。該階段根據短期風光預測數據,在離散無功補償裝置投切動作間隙利用連續無功調節裝置和儲能應對風光波動。此時電容器組數和變壓器投切檔位固定,根據第一階段的優化結果,以06:00—18:00時間段為例進行分析,時間間隔為15 min,風光出力和負荷預測數據見附圖B4。
典型節點電壓對比如圖6所示。從圖6可知,所選取的典型節點電壓均未越限,證明了在離散無功設備的調整間隙利用連續無功裝置平衡配網功率足以保障電壓處于合理范圍內,既避免了離散無功設備的頻繁動作,又保障了系統安全經濟性。

圖6 典型節點電壓Fig.6 Voltages at typical nodes
儲能充放電情況如圖7所示。由圖7進一步分析儲能的充放電特性,08:00—16:00時段,風光出力波動性強,且總輸出功率高于負荷有功功率,此時儲能系統充電,各動態無功裝置補償量也會相應減少,防止功率倒送;在16:00—18:00時段,負荷有功功率始終高于風光出力,儲能放電從而填補功率缺額。總體上儲能的動作依然呈現出在負荷低谷期充電、負荷高峰期放電的趨勢,能夠吸收有功功率保障風光的消納,實現有功平衡,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節點電壓。

圖7 儲能充放電情況Fig.7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of energy storages
3.2.3 計及風光相關性的優化效果分析
為了進一步證明考慮相關性后能夠降低風光不確定性給系統帶來的影響,利用文獻[23]提到的條件風險價值(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CvaR)量化新能源接入配電網造成的風險。此處的風險主要由風光不確定性引起,采取的計算公式為:
(26)
式中:α為置信水平,α越大,決策者對風險的厭惡水平越高;FCVaR和FCVaR分別代表條件風險價值和風險價值。
分別在90%、95%、99%的置信水平下計算考慮風光相關性和不考慮風光相關性下配電網經濟成本條件風險價值,其對比如表2所示。

表2 條件風險價值對比Table 2 Comparison of CvaR
數據顯示,風光出力的不確定性和相關性特性會給配電網的安全運行帶來一定的風險。在不計及風光相關性的情況下,風險水平隨著置信水平的增加而增大,且較計及相關性下的風險水平分別高出12.4%、10.6%、9.6%,這是由于同一地區風光出力所具有的互補性較為明顯,考慮風光單元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后有利于在優化過程中緩解不確定性和波動性,進而提高安全經濟效益。
4 結 論
1)利用Copula函數描述風光相關性可以緩解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系統后由于間歇性、波動性帶來的風險,在此基礎上對配電網進行優化控制更符合實際。
2)計及無功裕度的配電網協調優化調度策略能夠適應現代配電網的發展需要,充分利用配電網中的可調資源保障系統安全經濟運行。
3)在第一階段主要由離散設備和儲能承擔配電網中基礎的功率支撐,第二階段連續無功補償裝置能夠實時補償風光波動產生的無功缺額,實現了動作時間常數不同的無功補償設備差異化管理,同時儲能作為可控有功源也能夠提供一定的電壓支撐。
本文未考慮計及無功裕度下的無功分區問題,將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進一步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