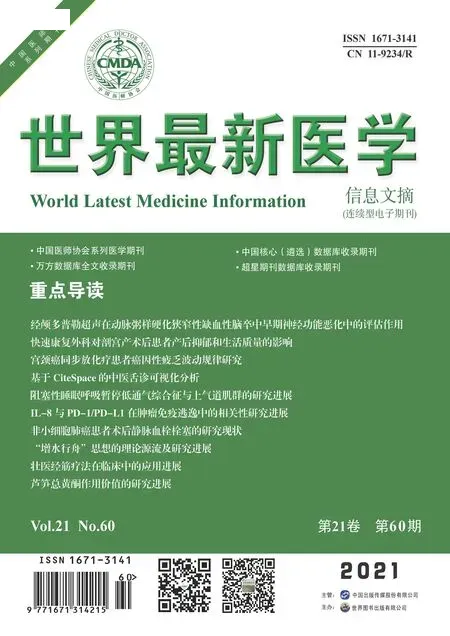宮頸癌同步放化療患者癌因性疲乏波動規律研究
焦培娟,趙越
(新疆醫科大學護理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00)
0 引言
宮頸癌是危害全球女性健康的主要惡性腫瘤之一,好發于宮頸外口原始鱗-柱交接處與生理性鱗柱交接部所形成的移行帶區。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宮頸癌篩查技術的普及和人乳頭瘤病毒(HPV)預防疫苗的廣泛接種,在2005~2015 年間全球宮頸癌發病率下降了近26%[1],但2018 年最新《全球癌癥報告》中數據顯示,宮頸癌年齡標準化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高達13.1/10 萬人口和6.9/10 萬人口,仍居高不下,二者在女性惡性腫瘤中均居第四位。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的國家之間,宮頸癌發病率和死亡率存在很大差距,收入水平較低的地區宮頸癌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收入水平較高地區的1.75 和2.93倍[2]。中國擁有世界約五分之一的人口,我國宮頸癌新發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別占全球的18.8%和9.5%[3]。
宮頸癌患者有很多痛苦的伴隨癥狀,如疼痛、焦慮、抑郁、胃腸道功能紊亂等[4-6]。造成這些癥狀的原因不僅是由于惡性腫瘤本質特征,還有腫瘤的治療手段如宮頸癌的手術治療、輔助化療、單純放療、同步放化療等。其中疲乏作為最常見的副反應之一,一直以來備受研究者的關注。與普通人群所經歷的疲乏感不同,癌癥患者的疲乏感被稱為癌因性疲乏(Cancer-Related Fatigue,CRF),其疲乏程度更重,時間更久,不能通過睡眠和休息緩解[7]。美國國家癌癥綜合網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認為CRF 是癌癥患者的一種主觀感受,主要表現為身心俱疲,興致缺乏,認知能力下降,無法承擔原有的工作和生活職責,且疲乏程度和近期活動量不符,而與癌癥及其治療密切相關,持續時間長,即使經充足的睡眠和休息也無法緩解,影響患者的日常功能[8]。
CRF 是接受放療、化療以及同步放化療的癌癥患者常見的癥狀,可以發生在疾病過程的任何階段[9]。研究顯示化療和放療患者CRF 發生率約為80%和90%[10]。同時,CRF 并不會隨著治療的結束而消失,約有37%患者在治療結束后仍會感到疲乏,常可持續數月或數年[11]。在疾病過程中,患者CRF 的水平并非固定不變,化療患者CRF 的嚴重程度呈周期性波動,疲乏感自治療開始逐漸增加,治療結束后2~5 天疲乏達到高峰,隨后疲乏感逐漸降低,在下一化療周期開始之前達到最低點,但仍高于基線水平,之后每個化療周期的疲乏波動模式都相同,患者的疲乏程度隨著化療周期的推移呈階梯式上升。放療患者的疲乏感在整個治療期間都在不斷增加,治療結束后兩周內疲乏程度有所減輕,但仍高于治療前水平[12]。CRF 不會隨著治療的結束而消失,它會持續數月或者數年,研究顯示治療結束后有37%患者仍會感到疲乏,時間長者可達5 年以上[13]。
宮頸癌患者以同步放化療為主要治療治療方案,手術、放療、化療、生物治療等均宮頸癌的治療方式。手術治療適合于早期宮頸癌患者(Ⅰ~Ⅱa),手術治療有較為嚴格的適應證,要求患者無嚴重的內科、外科合并癥。手術治療可以一次性清除腫瘤病灶,患者恢復時間較短,可以幫助年輕患者保留卵巢及陰道的正常功能。放射療法是治療子宮頸癌的主要方法之一,自宮腔內鐳元素治療開始,已經延續了一個世紀,世界范圍內宮頸癌放療患者超過80%。放射治療的療效穩定,各個分期均可使用。以順鉑為基礎的同步放化療臨床實驗報道自1999 年開始出現,研究以前瞻性的大樣本的隨機對照為主,可以使患者的死亡風險下降30%~50%,極大的提高患者的生存率。相較于單純放療,加入順鉑的同步放化療方案更能夠提高患者的生存率,這一觀點已有大量的臨床實驗結果支持。以往關于CRF 在治療期間波動水平的研究局限于單純放療或單純化療,且單獨研究宮頸癌患者的研究較少,故此研究旨在描述宮頸癌同步放化療患者治療期間CRF 的波動水平,為臨床護理工作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1.1.1 可得總體
某三甲醫院放療病區住院治療的宮頸癌患者,治療方案為同步放化療。
1.1.2 抽樣方法
方便抽樣
1.2 研究對象的納入和排除方法
1.2.1 納入標準
(1)患者知情同意,且自愿加入;
(2)經病理診斷為宮頸癌,病理類型為鱗狀細胞癌,即將開始同步放化療者;
(3)年齡在18~70 歲之間;
(4)觀察時間限定為體外照射25 次期間,包括一次同步化療;
(5)無明顯聽力、視力障礙,有正常的認知溝通能力,語言表達清楚。
1.2.2 排除標準
(1)既往3 周內接受過貧血治療患者;
(2)已參與其他心理,行為或認知研究者;
(3)有精神史者;
1.2.3 終止實驗標準。
(1)后續實驗過程不配合者;
(2)調查過程期間發生病情變化或重大生活事件,無法繼續參與者;
(3)骨髓抑制需要實施保護性隔離者;
(4)治療期間經輸血治療貧血的患者;
(5)要求退出者。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設計類型
描述性研究。
2003年11月25日,在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40周年暨創新“楓橋經驗”大會上,時任中央綜治委主任羅干作了重要講話。中共浙江省委于2004年5月和2006年4月先后作出了建設“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決定,強調要推廣和創新“楓橋經驗”。2008年11月24日,紀念“楓橋經驗”45周年大會召開,周永康、孟建柱等中央領導專程視察楓橋,給予新時期“楓橋經驗”高度評價。
1.2.2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有兩部分,一般資料問卷和Piper 疲乏量表修訂版。
(1)一般資料問卷
包括兩個部分:社會人口學和疾病相關資料問卷。參考相關文獻,并經過臨床護理專家和課題小組指導完善。社會人口學資料問卷包括姓名、年齡、職業、婚姻、照護者等,疾病相關資料包括分期、診斷時間、手術史、血紅蛋白值等,共有22 個條目。
(2)Piper 疲乏量表修訂版(The Revised Piper Fatigue Scale,RPFS)
此量表由美國學者Piper 制定,是最早用來評估CRF 的多維度自評量表,它有22 個計分條目和5 附加條目。22 個計分條目中,6 條測量行為疲乏,5 條測量情感疲乏,5 條測量感知疲乏,6 條測量認知疲乏。5 個開放性問題中有一個調查疲乏持續時間,4 個開放性問題幫助研究者收集更加全面的疲乏資料,有產生疲乏原因、減輕疲乏的措施及疲乏的相關癥狀。本研究只收集22 個計分條目。
該量表采用視覺模擬評分法,0 表示無疲乏癥狀,10 表示極度疲乏。總量表計分方法與各維度一致,均為各條目總分與條目數的比值,比值越大疲乏程度越嚴重,得分<3 分為輕度疲乏,3~6 分表示中度疲乏、>6 分則表示有嚴重疲乏。修訂后總量表Cronbach’s Alpha 為0.966,感知、情感、認知、行為疲乏四個維的Cronbach’s Alpha 分別是0.959、0.954、0.926、0.920。
RPFS 被翻譯成瑞典、希臘、中國版本,已被應用在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骨髓移植等患者當中,經檢驗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香港學者So 以及內地學者徐波對RPFS 做了翻譯及回譯,報告的香港版的Cronbach’s Alpha 在0.83~0.93 之間,總量表為0.98。本研究采用香港學者翻譯的RFPS。
1.3 數據收集
本研究納入的宮頸癌同步放化療患者接受的治療方案為25 次體外照射,累加劑量達為DT50Gy/25f,每天1 次,共進行5 周,4 次腔內照射,在體外照射進行一周后給予一次TP 方案化療(紫杉醇+奈達鉑)。由于腔內照射并不適用所有患者,如全子宮切除、體質虛弱者,也存在醫生根據治療效果增加體外照射或腔內照射次數的情況,為保證治療過程的同質性,所以本研究將觀察時間限定定為體外照射25 次期間,包括一次同步化療。在放療開始之前用一般資料問卷和RPFS 收集資料,開始治療后每完成5 次體外照射時,以及整個放療療程結束后48h 內,用RPFS 測量患者CRF 的嚴重程度,每位研究對象共測量6 個時間點,即治療開始之前(T1),放療5 次結束(T2),放療10 次結束(T3),放療15 次結束(T4),放療20次結束(T5),放療25 次結束(T6)。
2 結果
選取某三甲醫院腫瘤放療病區行同步放化療的宮頸癌患者51 例,社會人口學資料及六次測量時間點CRF 得分如下。
2.1 社會人口學資料
見表1。

表1 研究對象社會人口學資料(N=51)
2.2 疾病特征資料
見表2。

表2 研究對象疾病特征資料(N=51)
2.3 CRF 的變化趨勢
首先使用檢驗法對兩組六個時間點的疲乏總分及各個維度得分進行正態性檢驗,結果顯示都不服從正態分布,故選擇用中位數(M)和四分位間距(IQR)進行統計描述,具體數值見表3。

表3 時間點疲乏得分M(IQR)
3 討論
T1 測量點時治療尚未開始,射線和藥物暫時沒有對人體產生影響,故此時的疲乏處于輕度水平,5 次體外放射治療后,患者的疲乏程度仍處于輕度水平,可能是由于此時治療處于體外照射階段,而射線治療要求是達到有效的治療結局的同時,還要盡可能避免并發癥的出現(13),且放射劑量是隨著次數的增加而逐漸累積的,故放療初期患者的疲乏水平較低。
根據表2 的結果,結合圖1,可以發現在測量點T3 時,CRF 的程度達到最大值,此時患者的疲乏感最嚴重。研究對象所接受的同步放化療方案中的化療,是在放療第二周開始時進行,化療療程共進行3 天,T3 測量點處于化療后的2~5天,導致患者出現如下副反應:中性粒細胞血小板減少[14]、貧血等骨髓[15,16]抑制表現;消化道反應如食欲不振、惡心嘔吐、口腔潰瘍及腹痛腹瀉等,夜間尤甚[17];心理因素如焦慮、抑郁,部分患者睡眠質量差[18]。以上癥狀都與CRF 相關,導致患者此時疲乏感最為嚴重,與Schwartz 等的研究一致[12]。

圖1
隨著時間的推移化療副反應逐漸減輕,但是放療仍在持續,且劑量不斷累加,對人體的影響依然存在,故CRF 嚴重程度雖有下降但并未消失,25 次體外放療結束后的疲乏水平高于基線。
同步放化療治療時間較長,患者并發癥較多,CRF 的持續存在影響了患者的生活質量以及堅持治療的意愿[10]。作為醫務工作者在臨床護理工作當中要注意患者的癥狀變化,提前告知即將進行的治療會出現的不適癥狀,幫助患者提前做好應對準備,疲乏癥狀出現時及時提供相應的護理措施,CRF在化療后的嚴重程度達到最高峰,此后緩慢下降,本研究并未跟蹤調查治療結束后的數據,Kirchheiner 等[19]的研究表示,治療結束后CRF 會持續存在至治療結束后3 個月。
患者在長期治療過程中,日常生活中的活動受到限制,特別是在工作和休閑活動,故此在對患者的日常活動進行細致的規劃,并提供外界支持,有研究表示患者對CRF 的困擾不僅局限于治療后3 個月內,治療結束后的幾年里此項困擾會持續存在且有升高趨勢[20],故患者治療結束并不是護理工作的終點,還應提供相應的延續性支持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