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德爾塔到拉姆達,揭開病毒變種的面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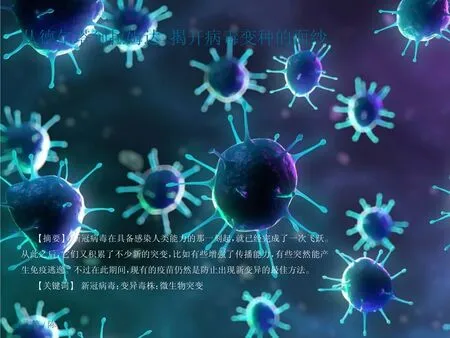
曾經,如果讓研究人員預測哪一種新冠變異毒株會造成嚴峻后果,他們的首個猜測對象決不會是德爾塔(Delta)變異株。但該變種自2020年12月首次在印度出現以來,這種高傳染性的變異株已成為新冠病毒的主要流行毒株。要知道,近期美國新冠肺炎病例中的90%以上均是感染了這種毒株。相較于早期的毒株,德爾塔具有更加強大的進化優勢。
美國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進化生物學家沃恩·庫珀(Vaughn Cooper)對此表示:“德爾塔的增長速度在這次的新冠大流行中是絕無僅有的。”
當德爾塔毒株持續在全球不斷造成感染的時候,又一種新興的拉姆達毒株走向臺前。許多人不經發出感慨:這樣的日子何時是個頭?病毒是否會無休止地突變?下面,就讓我們來揭開病毒變種的神秘面紗,為何病毒會產生突變?它們又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
理查德的三角瓶——認識微生物突變能力
1988年,為了理解進化的機制,31歲的生物學家理查德·倫斯基(Richard Lenski)在美國加州做了一項著名的實驗。他想知道,為了提高自身的屬性,微生物的進化能有多快?又會多有效?
他將常見的大腸桿菌分裝到12個不同的三角瓶里,每個三角瓶里都有同樣的培養液,并且都置于37度的環境下進行培養。每日,理查德都會從三角瓶里提取一些經過復制的細菌,放到新的三角瓶里。此外,他還不斷儲存細菌樣本,以便用于后續研究。
每天,三角瓶里的大腸桿菌都會產生六代全新的大腸桿菌。如果清晨的大腸桿菌還是剛出生的嬰兒,那么在一天將盡時,它們已然成為了曾曾曾祖輩。理查德和他的團隊一研究就是33年,收獲了7萬多代不同的大腸桿菌。與最初放入三角瓶的大腸桿菌相比,最新生成的大腸桿菌復制速度增長了70%。但即便不同的大腸桿菌群體學會使用不同的生物學通路來提升自己的屬性,但在七萬代后,它們看似達到了極限,大部分新生成的大腸桿菌群體之間,復制速度只差幾個百分點,非常接近。
理查德因為這項研究榮獲“麥克阿瑟天才獎”,他的發現也徹底改變了人們對微生物突變能力的認知。該研究的3個重要發現,對于今日的我們依舊有重要的啟發。
首先,隨著時間的不斷推進,突變產生的效益會逐漸減少——大部分會給細菌帶來生存優勢的突變,都在較早期發生。
第二,細菌將永遠不會停下進化的腳步。即便是在七萬代后,它們也在發生突變,追求更加完美的自己。盡管,這一進化的速度在后期可能已經大幅變緩。“我曾想過它們會停止進化,”理查德說道,“但看起來,對自身的修補存在無限種可能。如果真的有進化的極限的話,在實驗周期里,我們是不可能看到的。即便是在地質學上的時間尺度,我們可能也看不到。”

第三個重要發現更是關鍵。2003年,理查德來到實驗室,發現一個三角瓶里的培養液變得十分渾濁,這表明細菌出現了爆發式增長。在通常情況下,細菌絕不應該增長得如此之快。
經過研究,理查德發現這批大腸桿菌進化出了一種特殊的能力——普通大腸桿菌只能消化葡萄糖,而這批大腸桿菌卻習得了如何將檸檬酸鹽作為額外的能量來源。這種突變極其罕見,在30多年的研究期間,從未有另一種大腸桿菌能重復這種突變。
“為什么這樣罕見的突變可以發生,而再也沒有重現?”理查德說道,“一種可能性是這種突變本身很罕見,僅在整個實驗周期里出現一次。但另一種可能是,也許大腸桿菌先需要一系列其它變化,建立一個特殊的遺傳背景,然后一個普通的突變就能帶來全新的功能。”理查德認為他觀察到的也許是兩者的結合,大腸桿菌先需要積累特定的突變,再出現一個罕見而關鍵的新突變,讓整個種群的能力產生飛躍。
羅伯托的預言
阿爾法變種、貝塔變種、伽馬變種、德爾塔變種、拉姆達變種……每隔一段時間,新冠病毒就會積累出關鍵的突變,產生新的變種。新冠病毒的進化極限在哪里?它們未來又會出現哪些變化?
羅伯托·博里奧尼(Roberto Burioni)是世界知名病毒學家。他曾設想過新冠病毒的終極版本——一種具有最大化的傳播力,在全球占據統治地位,其它變種在它面前不值一提,僅在局部地區存在有限的影響力的毒株。
這種具有統治性的新冠變種,存在3種不同的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對人類來說最為樂觀——病毒再如何進化,也無法讓疫苗徹底失效。就如現存的許多可控傳染性疾病一樣,類似麻疹、脊髓灰質炎、天花等病毒,就在疫苗的控制范圍內。

在羅伯特提出的第二種可能性里,新冠變種會對疫苗帶來的免疫力產生“部分逃逸”。但這種免疫逃逸需要病毒付出一定的代價。比如貝塔與伽馬變種病毒,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免疫逃逸,但它們的傳播力都不如阿爾法或是德爾塔變種。
在20世紀90年代,HIV病毒曾面臨著相同的命運。當時,一種叫作M184V的突變使其對抗病毒藥物拉米夫定(lamivudine)產生了耐受性。表面上看,這是抗艾戰場上的一項倒退。然而醫生們卻發現,帶有M184V突變的感染者,體內的病毒載量更低,表明這一突變“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自身的復制效率也有所降低。因此在耐藥病毒株出現后,患者們依舊會服用拉米夫定。在某種意義上,人們選擇了M184V變種,以降低病毒的復制率。
最令人擔憂的就是羅伯特預言的第三種可能——病毒積累的突變最終突破了免疫屏障,且自身的傳染性或毒性沒有受到明顯影響。不過,這也意味著新冠病毒還需要經歷一次進化飛躍,我們都知道這種飛躍發生的可能性非常低。
一些科學家們認為,如果又要保持免疫逃逸功能,又要維持傳染力,新冠病毒會受到生物學上的諸多限制。比如為了降低中和抗體的結合能力,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結構會發生改變,而這可能會影響病毒結合人類細胞受體的能力。
“這當然會有限制,”美國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傳染病專家克里斯汀·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博士說道:“但我們不知道具體的限制在哪里。根本性的問題在于,病毒對這些突變的耐受性有多高。如果刺突蛋白出現了大量突變,這些刺突蛋白是否還能行使功能,協助病毒進入細胞?”
從某些方面看,結論也許并不樂觀。冠狀病毒一直以來就可以結合許多不同動物的ACE-2受體。一項近期的研究也支持了這樣的擔憂。
為了了解刺突蛋白的突變會如何影響其與ACE-2受體的結合能力,一支團隊對刺突蛋白的受體結合域的每一個氨基酸進行了突變,觀察其對刺突蛋白功能的影響。
結果表明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上,有大把可以耐受的位點,使其出現免疫逃逸的同時,維持對細胞的入侵能力。
精密復雜的免疫系統,抵御微生物入侵
雖然文章前面提到了許多病毒發展的可能性,但未來或許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悲觀。要知道,人類的免疫系統是相當復雜而又精密的,在數千年間成功抵御過無數微生物的入侵。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仿若眼前。當時,研究人員觀察到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相比老年人,它對于年輕人來說,危害好像更大。全球范圍內,每5名因為H1N1去世的感染者中,就有4名的年齡在65周歲以下。相比之下,通常的流感死亡病例中,70%到90%都是老年人。
部分人認為,這些在H1N1流感中不大受影響的老年人,在幾十年前可能曾遇到過類似的病毒株,這意味著,他們的免疫系統經受過“提前訓練”。在遇到H1N1時,免疫系統還記得幾十年前的戰斗經驗,因此可以抗擊該類毒株。
不管新冠病毒發生何種突變,它們本質上還是新冠病毒。目前的研究發現,無論是曾感染新冠的個體還是接種疫苗的個體,體內的抗體都能對多種冠狀病毒產生抵抗力,這甚至包括了2003年出現的SARS冠狀病毒。
“這兩種病毒在進化上的距離很遠,”進化生物學家泰勒·斯塔(Tyler Starr)博士說道:“同一種病毒能結合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能給我們帶來一定的信心。”斯塔博士想表達的是,如果連不那么相像的SARS病毒都能抑制,更何況是長相非常接近的新冠變種呢?
事實上,我們的身體在疫苗接種后,產生的是多克隆抗體。它不是一種,而是一大群不同的抗體。當其中一些抗體在新冠變種面前失效,我們總可以期望另外一些抗體能夠發揮功效。想要徹底對免疫系統發生逃逸,是一件不大可能發生的事情。
而且,中和抗體并不是抵抗力的全部。一些科學家指出,目前許多研究都提到中和抗體,只是因為任何一間實驗室都能做相關的實驗。
在疫苗的作用下,我們的身體還會產生記憶B細胞,記住先前遇到過的病原體,在再次遇見時會作出快速反應。


而T細胞則會追蹤和清除那些被感染的細胞——即便新冠變種會發生免疫逃逸,感染細胞,這些感染的細胞也很難逃脫T細胞的清理。在這一點上,新冠病毒再怎么突變也幾乎無濟于事。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接種疫苗的人還是可能會感染新冠病毒,但他們出現重癥或死亡的概率很低。斯塔博士提到,隨著時間推移,感染最終只會造成輕癥,或是無癥狀。盡管他不清楚這會需要多久。
疫苗會失效嗎?
此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免疫力能持續多久。針對新冠病毒,免疫力能持續5年以上嗎?對于爆發只有一年多的全新病毒,沒有人知道答案。我們只知道感染SARS病毒的一些個體,在近20年后,體內的T細胞還能識別SARS病毒。
許多人都在關心,新的新冠變種是否使得疫苗失效了。美國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New York University's Langone Medical Center)的微生物學家納撒尼爾·蘭道(Nathaniel Landau)認為,我們有著相對簡單的對抗德爾塔的方法,即對疫苗稍加改進,以使其更有效地對抗這種變體。“如果確實出現了一種具有比當前更易逃脫抗體的變異毒株,那就真的需要針對該毒株注射疫苗加強針了。”
不過在此期間,現有的疫苗仍然是防止出現新變異的最佳方法。美國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病毒學家梅胡爾·蘇塔爾(Mehul Suthar)表示:“顯而易見,在這些病毒存在的情況下,并不是說我們戰勝了德爾塔,就戰勝了新冠大流行,還將有其他的變異毒株不斷涌現。”
蘇塔爾還補充道,如果接種疫苗的人數過少、病毒的傳播無法加以控制,“那就將會出現感染、變異和傳播的無限循環。”
關于未來
與理查德的實驗不同,疫苗是三角瓶與新冠疫情之間的根本性區別。在理查德的三角瓶里,條件是一成不變的。但在真實世界中,我們正用盡全力來改變疫情。而疫苗在全球的生產與分配不均,則讓問題變得相當復雜——時至今日,世界上只有約四分之一的人口完整接種了疫苗。
因此,未來新冠變種究竟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身在何時,又身處何地。對于已經接種了疫苗的個體,所需擔心的或許是變種的免疫逃逸能力。但要知道,世界上還有數十億人沒有接種過疫苗,他們更需要擔心傳染性增強的問題。可以想象,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全世界的不同地區,會有不同的新冠變種,代表著不同的預言場景。
在理查德的三角瓶里,大腸桿菌在足夠長的時間里、穩定的環境下出現了進化飛躍。與理查德的實驗不同的是,新冠病毒培養的條件并不是在三角瓶中,而是在數千萬,乃至數億的人類群體中。因此,人類不會給它這樣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