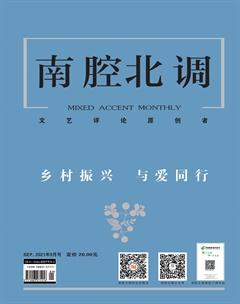寫作者需要強大的胃和靈活的頭腦
張翼 智啊威
有關智啊威的信息大多如下:1991年出生于河南周口。有小說刊發于《天涯》《山花》《作品》《青年作家》《廣州文藝》等刊物。出版有短篇小說集《解放動物園》。現居開封。如此格式化的信息,與智啊威充滿了奇幻意象的小說反差很大。我的心中一直有疑問,是什么使一位90后作家執著地一再以文字“返鄉”,又是什么使他的“鄉村”里總游走著那么多神奇的生物:仿佛人一樣的黑豬、盤旋著可以啄人骨肉的麻雀、能長成山羊那么大的公雞,還有為什么他偏愛使用兒童視角?這樣的“鄉村”是否會給積淀著豐厚鄉村寫作經驗的河南文學乃至中國文學帶來變化?種種疑問,促成了這次以筆談為主的“訪談”,希望能以此展開作家經驗、情感與記憶的皺褶。
以代際劃分人群不免粗糙,但也必須承認,不同階段的時代生活,的確程度不同地影響了特定人群包含行為方式、審美趣味乃至思維模式在內的“情感結構”,而受時代影響的“情感結構”又會反過來塑造時代。就代際而言,這次訪談或許也可以作為一個樣本,呈現70后、90后兩代“文學青年”文學觀念、閱讀經驗的重疊與錯位。
張翼(以下簡稱張):啊威,你好!在讀者的印象中,90后作家總是傾心城市生活,擅長描寫內向的個人情緒。當然,這也很可能是人們對90后作家的刻板印象。你不是那么“90后”,你的小說大多關聯著“鄉村”,能談談你為什么總是寫“鄉村”嗎?
智啊威(以下簡稱威):我十幾歲離開鄉村來到城市,多年下來,發現自己成了故鄉的異鄉人,城市的游蕩者。這種無根的狀態一度令我焦慮,而寫作是一種慰藉和救贖。我試圖通過文字和故事一次次返鄉。這種返鄉是精神、記憶以及感覺上的返鄉,因為真正的那個鄉村已經逝去。但很多時候,我發現,通過文字構建的故鄉(鄉村),比記憶中的故鄉更飽滿、生動,比當下故鄉更荒誕和真實。
我頻繁書寫故鄉,是在恢復某種珍貴的、逝去的記憶和感覺,它們看似一文不值,但于我而言極為珍貴。我把那些逝去的人、動物、街景、田野落實到文字上,仿佛它們就不會再次死去。
張:每一個作家都有搭建屬于自己的文學空間的野心。在你的《尋父記》《去羊莊捉鶴》《鳥類報告》《少年在天上飛》《破碎的祖父》《雪落在羊莊的額頭上》《空蕩蕩的田野》《鳳凰頭》等小說里,“小羊莊”或者有時候也被叫做“羊莊”的村落反復出現。“羊莊”是不是就是你想要搭建的文學空間?
這個虛構的文學空間,某些局部異常真實,應該就是豫東的某個村莊,傍著汾河,有點兒臟,也有點兒亂,它繼承中國農村的傷感歷史,生活資源匱乏、精神生活粗陋,也面臨著各種現實問題,比如空心化,成年人多在外打工,留在村子里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隨著老人去世、孩子求學,村子里的人越來越少。但這個羊莊又總是反經驗的、反常識的,因此很抽象。這個村子里發生著魔幻之事,黑豬有著人的神態舉止,人也有可能幻化成動物。《尋父記》的結尾處,趴在窗邊望向“我”的黑豬,是動物還是失蹤了的父親,成了一個謎。《去羊莊捉鶴》的象征意味更濃,“羊莊”一直是鄉鄰們寄托希望之處,因為那里有仙鶴,傳說人們吃了仙鶴就再也不會饑餓。可是眾人做好了所有準備卻發現,“羊莊”根本不存在。
可以說你的“羊莊”已經輪廓初現,但并不穩定。你對自己的“羊莊”滿意嗎?你是用寫實的方法去處理它,還是用象征與隱喻的方法呈現它?你在《去羊莊捉鶴》的結尾處寫了這么一句話“關于羊莊,大家仿佛無比熟悉,又極其陌生……”這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你對“鄉村”的感覺嗎?或者說,你想借助文字讓讀者這樣理解“鄉村”嗎?
威:寫作之初,我有意構建一個自己的文學故鄉:羊莊。它既是現實的,又是抽象的;既是具體的,又是概括的。那是豫東平原上的一個村子,也可以說是一個王國。在這里,人和動物的邊界模糊不清,生和死被混為一談。可以說,羊莊里的一切,都是一種隱喻和象征,因為我并不沉迷故事,而是想寫出故事背后的張力來。關于這個文學故鄉,現在還只是一個符號,不夠生動,隨著寫作的展開,我會把它塑造成一個人們的生存之地、死亡之地、遺忘之地、拋棄之地、尋找之地的交織體。
張:在你的小說里,鄉村是空間,孩子是主角。《雪落在羊莊的額頭上》寫孩子們失學的現實境遇,《少年在天上飛》寫孩子的奇思妙想。即便在寫成人的鄉村世界時,孩子也出沒其中。孩子或是其中的主人公之一,或者成為故事的敘述者。除了以現在時態寫孩子之外,你的小說更常用過去時態寫童年記憶,比如《在河水的嗓子里》描寫了20年前三娃的溺亡事故。雖然你還很年輕,距離孩子的狀態并不遙遠,但如此執著、密集地寫孩子,還是很讓人吃驚的。
同時,這些孩子總是非常孤獨的。要么是父母不在身邊的留守兒童,要么是失去親人的孤兒,也有些是被小伙伴們邊緣化的小孩兒。《空蕩蕩的田野》里有一個細節,小武一個人帶著公雞走在田地里,“那只公雞長大了,像一只山羊那么大,羽毛像鳳凰一樣艷,跟在小武屁股后面。”長大了、毛色鮮亮的公雞,越發顯得小武的“小”與“弱”。記不清是哪個作家說過的,作家的寫作終其一生都是在敘述自己的童年。你筆下的孩子是不是你過往經驗的折射?孩子在你的小說中,是不是也具有某些特定的象征意義?是什么讓你的主人公不愿意“長大”?在你看來,“孩子”與“鄉村”的關系是什么?
威:在《解放動物園》這部小說集里,我寫了很多孩子的孤獨、死亡和游蕩,剖析他們的絕望和渴望,而現在正在寫的這部小說集,我用了很多篇幅在書寫老人的生存問題和死亡問題。無論是孩子還是老人,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同時也是最柔弱的。就目前而言,我渴望潛入他們的內心世界之中去寫作。這些不是過往經驗的折射,而是一種寫作上的冒險和關懷。
張:鄉土是中國新文學最敏感的神經,也因此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但是中國的鄉村書寫是以故事為主、偏重寫實的。你的鄉村書寫是超現實的,其突出的特征就是小說中那些奇幻的動物意象。它們往往出奇地強大,特別是比鄉村里的“人”要體型大、力量強、速度快,人與動物的對峙往往是以人的失敗告終。
威:動物強大,是一種反常識的書寫。人類奴役動物,隨意宰殺動物,折磨動物……這些仿佛天經地義,而這種天經地義背后,是人生而為人的優越性使然。我在寫作時,消解了人自我賦予的強大和權力,把人放回到動物的行列中(因為人本身就是動物的一種),跟動物去搏斗和糾纏,然后失敗。人的失敗,在這里是一種警醒和提示。我的小說集的名字是“解放動物園”,但我知道,解放動物的道路還很遙遠,但尊重動物是一條生命的道路,可以一點一點地去建立。尊重動物的生命,就是尊重萬物生命的一個開始和前提。
張:你的寫作是從寫詩歌開始的,這是不是你的小說寫得偏意象化、偏象征化的原因呢?你怎么理解小說的特點?又怎么處理寫小說和寫詩之間的不同?除了寫作經驗之外,還有什么因素促使你小說特征的生成?
威:我從詩歌轉行去寫小說,詩歌對我寫小說的啟發和滋養巨大,詩歌的語言、隱喻、象征、詞語和意象的打破重組,最終達到一種朦朧而精確的書寫,這些方式和方向,放到小說家腦子里,就是一種新啟發。寫作,觀念要開闊,模糊文體之間的邊界,回歸到文學中來。評論家對小說的定義是方便理論家言說,而寫作者要做的,是打破別人對小說的定義,寫出真誠的、新鮮的小說來。至于特征,最好雜交,不留痕跡,與詩歌、報告文學、隨筆等文體去雜交,這需要作者具有一個強大的胃和靈活的頭腦。這是我的寫作渴望達到的一個方向,而現在,我還是一個新手,剛上路,走得搖搖晃晃,但好在方向明確,內心堅定不移。
張:你用“動物”、用“孩子”、用“詩”寫出了一個與以往不大一樣的鄉村。鄉村在變,鄉村的經驗也在變,鄉村的寫法也一定會有變化,期待你的新作!
作者張翼單位:河南省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