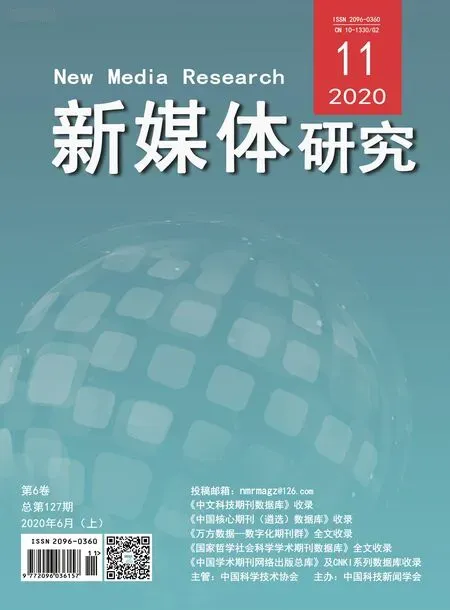模因論視域下周某齊梗的傳播機制研究
薛羽
關鍵詞 模因論;周某齊;傳播機制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11-0088-03
隨著媒介技術不斷進步,當代文化的生產與傳播方式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社會議題在新媒體中的廣泛傳播,使得網絡流行文化照搬進社會現實之中,社會議題娛樂化現象愈演愈烈,弱化了文化的傳承功能,影響著受眾的道德認知和價值觀形成。在這個過程中,網民成為施加這種文化暴力的主體,語言成為文化娛樂化的工具。
本文以周某齊事件為例,從語言模因工具及其進化視角出發,分析事件流行的動因,并指出模因娛樂化、低俗化發展的不良影響,旨在提醒人們在娛樂狂歡中應保持理性思考。
1 周某齊梗背景概述
2020年12月,南寧電動車偷竊慣犯周某齊出任廣西某電動車公司首席品牌官負責企業品牌形象建設,引發輿論熱議。他的首次走紅源于第二次偷盜被抓時接受媒體采訪所發表的言論“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不可能打工的”。周某齊第四次刑滿釋放當天,網紅經紀公司、直播平臺工作人員、熱心網友守在監獄門口迎接其出獄,聲勢浩大,轟動一時。30多家網紅公司找到周某齊哥哥尋求直播,提出300萬簽約金捧其做主播,將周某齊事件推向高潮。
網絡中圍繞周某齊的創作熱度持續升溫,有專屬貼吧、微博和抖音話題、印有他頭像及言論的周邊服飾和表情包等。“周某人”“那個男人”“偷電瓶養你”以及“精神領袖”等梗在社交媒體的大量復制與模仿,使周某齊成為集數梗于一身的“頂級流量王”。其中,微博“周某人”話題的閱讀量達969.2萬,B站以他為創作素材的視頻瀏覽量達1 353.1萬。模因論將這種存在模仿可能性的語言、觀念、行為視為一種文化基因即模因(meme),它通過復制得以生存,通過模仿得以進化。人們日常話語中的“梗”在傳播過程、表現形式和發生機制方面與模因十分一致,因此選擇模因理論來闡釋梗的傳播機制有助于挖掘其規律性。當前,圍繞周某齊的若干梗正在逐漸發展成模因群。
1976年英國生物學家道金斯首次提出模因概念,他認為生物進化是基于基因的復制,而文化進化則基于人類行為的復制,他取基因gene的諧音meme來命名這種文化進化的基因,國內譯為米姆、迷因、模因,也正是人們常說的“梗”。道金斯認為成功的模因必須同時具備長壽性、多產性、復制忠實性的特點,即模因復制在傳播模式中留存的時間越長,復制的數量就越多;模因的復制能力越強,傳播的頻率和速度也就越快;語言模因必須具備極高的保真性。模因信息模式具有寄生性,可以直接影響人的意識并改變個體的行為做出反應或者是重新加以復制,從而通過模仿、復制等手段來繁衍和傳播該類信息[1]。道金斯的學生布萊克摩爾在他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模因論,提出進化成為成功模因主要由兩個因素決定:作為模仿者和選擇者的人類本性與模因自身的特點。她還強調了模因進化的內在驅力——模仿,指出模因進化過程存在三個必要條件:遺傳(行為的形式和細節被復制)、變異(復制帶有誤差:改進及其他變化)和選擇(只有某些行為可以成功地被復制)。在她看來模因帶來的不僅是文化進化,也會驅動人類基因的進化,使得人類腦容量大幅度增加[2]。比利時學者海拉恩認為互聯網為模因傳播提供了全新的媒介,模因的進化和信息傳播要經過同化、記憶、表達和信息傳輸過程,其中那些接受并使用這些模因的人被稱為模因宿主。互聯網的高速發展賦予了模因論新的時代特征,全民性、交互性和數據海量性等特點使其成為模因模仿、復制和傳播的沃土。不同于以往模因的簡單復制,人類創造性思維活動在網絡上的高度互動和參與使得模因的傳播機制也發生了變化,經歷了解構與重構的過程,如今的模因傳播機制可以大致概括為同化—記憶—表達—解構與重構—傳播。
2 周某齊模因群傳播機制
2.1 同化:模因獲取與涵義認同
模因的獲取是邏輯起點。我國學者何自然認為語言模因的傳播具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模因宿主對信息的感悟和選擇,二是導致宿主做出選擇的環境因素[3]。宿主通過對事件、觀念和思想的感悟來提煉,從中選擇模因并加以復制。例如,周某齊“不可能打工”的模因提取實質上是來自于當地新聞媒體的把關。新聞媒體在周某齊事件報道中充當著第一宿主的角色,他們對周某齊的眾多話語進行提煉,最終選取了“不可能打工”這個梗。模因想要進入傳播渠道,還必須符合人們心理期待以達成觀念上的同化[4]。
2.2 記憶:喚醒與深化
模因具有長壽性的特點。模因的形成不是一個偶然的熱點瞬爆,而是具有較長生命力的,它建立在人們已有知識、信息獲得和情感積累基礎之上。周某齊在2012年因“不可能打工”言論走紅,2020年的“出獄風云”再次將他推向熱門話題,模因尤其是強勢模因喚醒了宿主心目中對周某齊已有的認知基模,并在原有基模上進行強化或修改,形成新的認知基模,從而深化宿主對于強勢模因的記憶,這類記憶將為周某齊下一次的流量高峰做準備,助推模因群不斷擴大。
2.3 表達:模仿與模因復制
塔爾德提出“模仿即社會”,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模仿,模仿是先天的,人們通過互相模仿來保持行為上的一致。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會在社會中尋找群體歸屬,當確認了自己的從屬群體就會自覺遵守群體規范并保持一致,以獲得社會交往和身份認同。模仿是遵守群體規范最有效的行為方式之一,模因正是通過模仿來進行自我復制。互聯網為宿主提供了海量的模因因子和社交互動平臺,宿主可以從中“偷獵”各類社會流行文本,創作并表現出這個群體本身的文化產品。周某齊的使用者就是這種文化產品的模因群體,他們在復制和模仿中賦予其新的意義。成員們使用“那個男人”等來表達情感訴求的過程便是一個自我身份的建構。高度自由的大規模復制和社會群體交往,使得模因的復制頻次和范圍加劇。
2.4 解構與重構:模因的競爭與進化
模因群中的模因為了得到復制相互之間會展開競爭,勝者將改變模因選擇的環境。宿主根據個人意圖對已有的模因進行解構,自然競爭將在模因之間展開,勝者成為強勢模因重新進入到模因群之中,達成模因群的重構。模因群體將模因源泉“電車偷盜慣犯周某齊”進行拆解并予以二次創作,衍生出“南寧車王”“今瓶沒”“當我出手時,你就可以走路回家了”等模因,又輔以表情包、電影海報、gif動圖等表現方式形成新的模因群。模因之間的競爭是一個過程,原有模因并不會在競爭失利后立刻從宿主認知中消失,而是由強勢模因轉化為弱勢模因,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被淘汰,模因就是在解構與重構中不斷地進化。
2.5 傳播:模因群的形成與到達
模因傳播需要借助媒介,從人際傳播到大眾傳播,不同媒介形成的模因群規模大小不同。模因源泉來源于大眾傳播媒介內部的把關,經由大眾傳播媒介編碼后流向大眾。在這一過程中,活躍在各類社交媒體的意見領袖在信息傳播和輿論形成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熟知媒介運行規律,意見領袖憑借自身優勢地位對興趣群體施加影響,引發群體的大規模模仿,這類模仿經過宿主自發的解構與重構環節,成功的表達宿主態度成為新的模因群,反哺到大眾傳播渠道之中。由此,模因群的傳播范圍不斷擴大,達到遍在的傳播效果。
3 流行動因
3.1 語言經濟性原則
美國學者齊夫提出人類語言的創造與運用存在著語言經濟性原則。人們在用一種語言表達個人觀念或思想的過程中會感受到兩個方向相反的力:單一化和形式多樣化的推動力。它們在人們講話時共同發生,一方面是希望盡可能的簡潔,另一方面又意圖便于讓人理解,使每個概念都能用一個對應的名詞或術語來表達,聆聽者理解起來毫不費力[5]。成功進化的模因擁有短小精悍、言必有中的語言特點。在語言模因上,一個模因往往可以表達一個完整的故事,即用最經濟的方式表達最復雜的含義。“南寧車王”可以簡單概括周某齊的心路歷程,從偷盜事件到全家走紅,從反叛領袖到悔不當初。人們在網絡上毫不費力甚至不假思索的使用模因,表達簡單的快樂。
3.2 審丑心理
隨著生活節奏加快,人們為了緩解生活壓力、宣泄情緒,會主動尋求精神刺激來追捧一種“丑文化”。審丑是一種獵奇、追求精神刺激和滿足的心理,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給人們精神上的畸形享受,是一種紓解壓力和情緒宣泄的方式。周某齊模因群正是滿足了審丑時代人們的心理爽點。
審美需要后天的培養,而審丑卻能在人們不假思索中出現。在注意力經濟時代,“丑”擁有毫不費力抓人眼球的特性,不斷地吸引注意力資源,尤其是當審丑進入了大眾傳播渠道,造成“全民審丑”態勢。主流文化長期以往造成的審美疲勞和逆反心理使得審丑時代加速到來。這時出現的一些低俗、奇葩的事物打破了當代主流文化傳播的高度同質性。諾依曼認為傳播媒介對人們的環境認知活動產生影響的因素有三個:共鳴、累積和遍在效應。當多數大眾傳播媒介的報道內容具有高度的類似性(共鳴)、同類信息的傳播在時間上具有持續性和重復性(累積),信息的抵達范圍具有廣泛性(遍在),丑文化便得以形成一種廣泛的認知環境。基于“丑”元素創作的話語、圖片、視頻等經過大眾傳播形成一定模因群,成為文化系統中的一部分。
3.3 模因的商品屬性
互聯網處處可見資本裹挾的影子,模因和現代營銷的結合是一種必然。基于模因強大感染力的特點,網紅經紀等商業公司瞅準它所能帶來的流量優勢加大了資金投入,使得模因具有一定的商品屬性[6]。在注意力經濟時代,模因和資本的結合是大勢所趨。資本的參與讓模因傳播更具有組織力和程序化,加速了模因進化。印有周某齊頭像服飾的售賣、親屬直播的背后都有資本的參與和操縱,但周某齊在資本面前只是工具人,資本售賣的是由他衍生的文化基因。
3.4 話語權的反抗
渴望表達卻缺乏主流話語權的年輕人和亞文化群體為尋求發聲,通過各種技術手段參與文化生產,使得網絡流行語、表情包、文創周邊盛行,為模因的傳播提供了豐厚的亞文化土壤[7]。伯明翰學派認為,亞文化出現的目的正是為了“抵抗社會”,這也能幫助解釋為什么負面意義的“偷車賊”卻能作為所謂的“精神領袖”得到公眾的廣泛矚目。需要警惕的是,在這場模因狂歡中青少年亞文化呈現出一種低俗化、泛娛樂化的發展趨勢,給主流話語帶來了一定的沖擊,表現出對“抵抗”的盲目崇拜。
4 結語
隨著5G技術的發展,模因復制與傳播的表現形式將會發生變化,不同于表情包、海報的平面制作,AR、MR技術的采用將增進人們感官的直接感受,成為新的表現形式和傳播載體。屆時強勢模因的效力將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模因的生命周期也將發生變化,弱勢模因生命周期更短,強勢模因生命更長。模因使人們的生活變得簡單有趣,但是人們也要警惕模因娛樂化、低俗化進化的現象。如今的模因更多表現為刻意的制作,而不是自然的選擇,這背后既有資本的誘因又有社會心理的參與。當“一切公眾話語都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8]。模因的過度娛樂化會麻痹大眾神經,使得人們更愿意選擇不經思考地、淺薄地對待社會事務,最終不再是人主導模因進化,而是模因主導人們的思想。周某齊的走紅展現了一種犯罪娛樂化趨勢,實質上傳遞的是一種扭曲的價值觀,消解了犯罪這個嚴肅的社會話題。
參考文獻
[1]曹進,靳琰.網絡強勢語言模因傳播力的學理闡釋[J].國際新聞界,2016(2):37-56.
[2]蕭俊明.摹媒與模仿:布萊克摩爾的摹媒理論述評[J].國外社會科學,2010(3):69-79.
[3]何自然.流行語流行的模因論解讀[J].山東外語教學,2014(2):7-13.
[4]吳華,楊剛.輿論引導:新媒體語境下模因傳播機理觀察[J].新媒體研究,2020(1):19-20.
[5]劉凱.語言發展中的省力原則[J].劍南文學,2012(1).73-74.
[6]常江,田浩.迷因理論視域下的短視頻文化:基于抖音的個案研究[J].新聞與寫作,2018(12):32-39.
[7]高雪.抵抗與收編:彈幕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關系研究[D].廣州:暨南大學,2015.
[8]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章艷,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