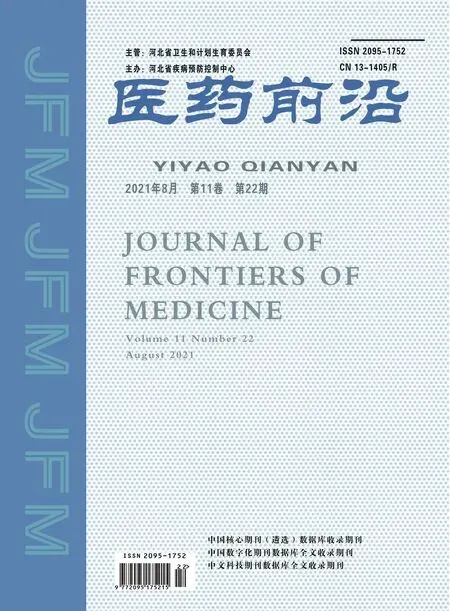肺腺癌中PD-L1的表達與EGFR及ALK基因突變狀態的相關性分析
高 敏,張世豪,周 嬋
(東莞人民醫院病理科 廣東 東莞523059)
在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治療中,近年來出現了兩種主要的治療模式: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前者依賴于基因改變的分層進行治療,如針對EGFR、ALK基因突變的靶向治療取得了顯著的治療效果。盡管如此,藥物耐受日益嚴重,此外,相當一部分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沒有靶向治療所針對的基因改變。新一代免疫療法的出現,改變了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模式,極大地改善了患者的預后。目前,以PD-1/PD-L1為代表的免疫抑制劑已成為非小細胞肺癌的重要治療手段之一。初步的研究已經提示PD-1/PD-L1通路與EGFR通路之間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探究肺腺癌中PD-L1表達情況與EGFR、ALK基因突變狀態的相關性是極其重要的。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1月—2017年12月我院病理科存檔的原發性肺腺癌石蠟標本94例,患者在術前均未進行任何治療;由至少兩位副高職稱病理診斷醫師對所選病例進行組織學分型、分期。
1.2方法
基因測序(Sanger法)技術檢測EGFR基因的突變狀態;熒光原位雜交技術(FISH)檢測ALK表達情況;IHC染色采用EnVision兩步法。參考Al-Shibli等[1]的標準判讀肺腺癌中PD-Ll的表達結果,陽性表達主要是鏡下在細胞質或細胞膜上出現黃至棕褐色顆粒。染色強度的劃分方法:無著色0分,淡黃色1分,棕黃色2分,棕褐色3分。陽性細胞數≤10%時1分,10%<陽性細胞數≤50%時2分,陽性細胞數>50%時3分。表達結果主要結合陽性細胞百分比和染色強度來綜合評定,即用染色強度×陽性細胞百分比得分,當該得分≥3分時判讀為陽性,<3分時判讀為陰性。
1.3統計學方法
使用SAS25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采用χ2檢驗和Fisher確切概率法進行PD-L1免疫表型的組間比較以及EGFR、ALK基因之間的比較;相關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關性檢驗;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PD-L1表達與肺腺癌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94例肺腺癌患者,其中男50例,女44例;年齡39~77歲,平均年齡61.3歲,其中<60歲的37例,≥60歲的57例;腺泡型47例,實性型18例,乳頭型7例,微乳頭型6例,附壁型16例;<3 cm的56例,≥3 cm的38例;TNM分期情況:Ⅰ期45例,Ⅱ期19例,Ⅲ期17例,Ⅳ期13例;有淋巴結轉移者38例,無淋巴結轉移者56例。PD-L1蛋白表達主要定位于腫瘤細胞的細胞膜和細胞質,其陽性率為39.4%(37/94),癌旁肺組織肺泡上皮細胞不表達PD-L1;PD-L1的表達與組織學分型、淋巴結轉移具有相關性(均P<0.05),見表1。

表1 肺腺癌中PD-L1蛋白表達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2.2 PD-L1與EGFR、ALK基因突變的相關性
94例肺腺癌患者,EGFR基因突變組51例,野生組43例;突變患者中,18例外顯子19位點缺失,23例外顯子21位點L858R突變,1例外顯子18位點G719A突變,7例外顯子20位點Q787Q同義突變,2例外顯子20位點插入突變。ALK融合基因陽性率為8.51%(8/94)。在51例EGFR基因突變型的肺腺癌中PD-L1的陽性率為51%(26/51),在43例EGFR基因野生型的肺腺癌中PD-L1的陽性率為25.6%(11/43);EGFR突變組PD-L1的陽性表達率高于EGFR野生組,兩組表達有統計學差異。PD-L1的表達與EGFR突變有關(P<0.05),未發現EGFR不同突變類型和PD-L1的表達存在相關性;PD-L1基因與ALK表達的相關性不具有統計學意義,其原因可能是EML4-ALK陽性率很低,病例數過少,見表2。

表2 肺腺癌中PD-L1蛋白表達與EGFR、ALK基因突變的關系
3.討論
程序性死亡受體-1(PD-1)是CD28家族成員之一,具有PD-L1及PD-L2兩個配體,其中PD-L1與PD-1的相互作用在抑制T細胞體內反應中起主導作用。PD-L1定位于人染色體9q24,屬于B7超家族成員,是由290個氨基酸組成的Ⅰ型跨膜蛋白[2]。通過阻斷PD-1/PD-L1信號軸,重新激活腫瘤微環境中的T細胞介導的抗腫瘤免疫效應,以達到治療多種類型腫瘤的目的。
結果表明EGFR突變組PD-L1的陽性表達率高于EGFR野生組,PD-L1的表達與EGFR突變有關(P<0.05)。這與文獻報道的EGFR通路的活化可以上調PD-L1的表達相一致。PD-L1表達的調控機制相對復雜,可受多種腫瘤信號通路的調控,如ALK/STAT3、PI3K及MEK/ERK/STAT1等[3],而上述通路中多個關鍵蛋白,如STAT3、PI3K等與EGFR、ALK基因激活的下游信號通路相關以及NSCLC的發生和發展具有密切關系。Chen等[4]研究發現,EGFR 19del突變和21L858R突變可以通過p-ERK1/2/p-c-Jun信號途徑介導PD-L1的表達,PD-L1高表達可通過PD-1/PD-L1途徑介導T細胞的凋亡。Ikeda等[5]發現,部分原發性非小細胞肺癌患者PDL1和JAK2基因同時擴增,JAK2是一種調節PD-L1表達的上游激酶,PD-L1蛋白表達通過PD-L1基因擴增和JAK2/STAT信號同步上調。Marzec等[6]觀察到NPM-ALK重排可以通過激活下游STAT3誘導間變性大細胞淋巴瘤中PD-L1的表達。此外,腫瘤微環境中干擾素-γ亦可調節PD-L1的表達,其利用IFN-γ/JAK/STAT1通路上調PDL1表達,減弱微環境中的免疫監視[7]。文獻中亦有報道PD-L1高表達與淋巴結轉移[8],組織學亞型有關[9]。大量證據表明,PD-L1表達水平與不良預后顯著相關[10],可能原因是在腫瘤發生過程中,這些致癌途徑、基因突變或炎癥因子等上調PD-L1,減弱免疫細胞的活性,使癌細胞逃避免疫刺激,提高其生存和轉移潛能。總之,PD-L1復雜的表達調控機制,可能影響PD-L1抑制劑的療效,有待今后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初步的研究已經提示PD-1/PD-L1通路與EGFR通路之間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探索EGFR、ALK基因突變等多種分子標志物的聯合評估,對腫瘤預后、免疫分子聯合治療以及靶向耐藥的替代治療均有重要的臨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