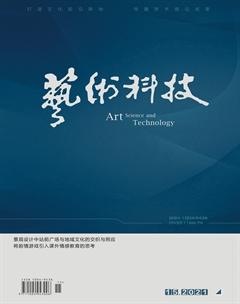重大歷史題材電視劇《覺醒年代》的隱喻機制探究
摘要:《覺醒年代》是一部講述新文化運動到建黨這一時期思想流變的重大歷史題材電視劇,如何用鏡頭展現思想的變化、精神的覺醒,是導演張永新認為的最大創作難點。本文通過分析《覺醒年代》中的隱喻機制,探究其價值觀傳達功能,從而為理解《覺醒年代》提供新的維度。
關鍵詞:《覺醒年代》;電視劇;重大歷史題材;隱喻機制;價值觀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15-00-02
1 影視語言中的隱喻理論
隱喻的本質就是通過另一種事物來理解和體驗當前的事物,隱喻機制包括換喻、提喻、替代、變形、并置等隱喻手法。《覺醒年代》中有大量有關社會背景、情感傾向、思想流變的內容需要被展現,這些抽象又宏大的鏡頭在電視劇的拍攝中具有局限性,而提喻可通過事物的一部分,或一個構成要素,乃至一個更為復雜的整體,給予同一事物“以小換大”的效果,因此《覺醒年代》借助提喻展現大環境,通過處理影像空間上的符號性提喻、時間軸線上的段落性提喻和角色塑造上的角色提喻,化抽象為具體,為理解人物活動進行生動鋪墊。隱喻中的替代則強調隱喻中的相關或對應關系,表現對象是分開的整體,用部分、原因、容器等符號替代整體、結果、容納物等的符號,通過替代雙方的隱性聯系,促使鏡頭內容產生新的含義;蒙太奇是指有意識地對鏡頭進行排列組合,從而含蓄形象地表達創作者的價值觀,鏡頭間相互聯系,具有強烈的隱喻功能。
《覺醒年代》以一刊、二人、三事和多元思潮為中心搭建全劇故事框架并塑造人物群像,講述了1915—1921年的覺醒年代中的社會風情與人生百態。一刊即《新青年》,二人即主角李大釗和陳獨秀,三事即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建黨,多元思潮即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皇派、復古派等多種思潮。不斷創新正劇表達形態是滿足受眾需求的重要手段[1],在藝術化的表現方式與創新性審美上,導演運用了大量隱喻,使這部劇整體表達有所突破[2],同時留出大量思考空間,引起觀眾情感上的共鳴[3]。
2 《覺醒年代》中的隱喻機制
2.1 提喻
2.1.1 符號性提喻
特雷弗·惠特克將提喻概括為“部分喻整體”,為了獲得明顯的提喻效果,影像文本可以充分利用各種修辭手法或表意策略。在影像空間處理上,可以使用特寫、光線、色彩、景別等,這個層面的提喻現象稱為符號性提喻,用影像的造型符號來隱喻文本主題,讓觀眾關注劇中符號的象征意義[4]。重大歷史題材電視劇離不開歷史,對歷史背景的掌握程度,決定著觀眾對劇中人物及事件的理解程度[5]。《覺醒年代》以版刻開頭,晃動的版刻紋路給人以斑駁與滄桑之感,整體顏色偏冷偏暗,呼嘯的風聲與沉重的旁白作為本劇歷史背景的符號性隱喻[6],營造了黃沙漫卷的蕭瑟凄涼的氛圍,這些符號被賦予了一定的現實指代和社會意義,在增強藝術美感的同時[7],也暗示著辛亥革命后被“三座大山”壓迫的社會的混沌,為后續講述國人“覺醒”運動,再現時代風云造勢。
2.1.2 段落性提喻
在時間軸線上,導演對時間元素進行刪減、擴容,甚至變換,這些元素包括時序、時頻、時長等。對實踐性元素進行設置導致影像段落產生,也就是用一個段落隱喻文本整體,這個層面的提喻現象被稱為段落性提喻。陳獨秀送別陳延年與陳喬年兩兄弟赴法國勤工儉學的片段中,導演將赴法與赴死兩段時間交織在一起,兩位少年赴法時意氣風發的腳步,與若干年后戴著腳鐐仍無所畏懼的步伐重疊,兄弟倆即將遠渡重洋的回眸與慷慨赴死的回眸交織。兩段時間上做減法的處理風格,帶來了空間及意義上的創新,兩個時間段的交織體現出了陳氏兄弟“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雄偉氣魄,同時這一段落也隱喻著影片整體,通過陳氏兄弟隱喻近代中國無數投身革命的志士仁人,他們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用碧血澆灌自由之花。
2.1.3 角色提喻
《覺醒年代》展現了不同形象的身份、年齡等差異,如魯迅出場的片段中,狐假虎威的砍頭士兵所代表的軍閥、要飯的乞丐、圍觀砍頭的農民、湊熱鬧的小孩和年輕人、冷眼旁觀的鄉紳、沒有悔意和羞恥感的盜賊、搶著要人血饅頭的無知百姓、穿著清朝服飾的女子與想要喚醒麻木無知民眾的知識分子,共同組成了當時的階層圖像,其中人物之間互為角色提喻,借助角色的差異側面塑造角色[8],將當時社會的愚昧與麻木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也暗示著中國先進分子和熱血青年建黨的艱辛,能引起受眾深層次的情感共鳴[9]。軍閥專制、文化復古主義、社會主義、保皇派、自由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在劇中皆有所展現,代表軍閥專制的北洋政府徐世昌總統,代表文化復古派的辜鴻銘、林紓、劉師培,代表社會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代表保皇派的張勛,代表自由主義的胡適,代表無政府主義的吳稚暉,在近代中國的舞臺上展開較量,各派代表之間的差異互為提喻,同派人物之間的差異也互為提喻,共同組成了相互異質、交融而又多元共生的社會群像,這給毛澤東、周恩來、陳氏兄弟、趙世炎等年輕的革命者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2.2 替代
替代由兩個系統組成,一個是作為喻體的源域,一個是作為本體的目標域,源域中的相關或對應的特性映射到目標域中,便會產生潛在的新意義,給予受眾較大的想象空間[10]。《覺醒年代》開頭出場的是沙漠中行走的駱駝,駱駝自古在我國象征著不畏懼艱險,將駱駝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特性映射到解說詞“國內政局混亂,人民痛苦不堪,內憂外患,再次將中國拋入風雨飄搖之中”所呈現的目標域中,觀眾便會產生中國早期覺醒的革命者如同駱駝一般不畏艱險、勇往直前,最終取得勝利的聯想。在展現總統府日薄西山的鏡頭中,天還是亮的,但總統府已經點起了燈,這一做法十分怪誕荒謬,這就是本組替代隱喻鏡頭所要表達的含義,運用隱喻意義的相關性,形象地表達出北洋政府是荒謬的抽象概念,引發受眾的認同及認知心理[11]。在這個片段中,總統府白天開燈的鏡頭是目標域,白天關燈、晚上開燈是觀眾意識中的基本常識,也是這個鏡頭的源域,將正常情況下白天關燈、晚上開燈的特性映射到總統府白天開燈的鏡頭上,就會產生矛盾,這時觀眾就會對這一個目標域鏡頭產生一個潛在的新含義,即荒謬。觀眾看到的鏡頭已經不是在表現白天不能開燈的意義了,而是在表現北洋政府的荒謬,這才是這組鏡頭真正要表達的含義。
2.3 蒙太奇
根據庫里肖夫效應,愛森斯坦將蒙太奇制造的修辭意義稱為隱喻,其具有“1+1>2”或“A+B>C”的功效,通過局部的對比造成整體的新的質。在劇中,青年毛澤東以冒雨逆人群奔跑的方式出場,該劇將毛澤東將帶領中國乘風破浪,使積貧積弱的中國舊貌換新顏這一內涵通過蒙太奇手法進行隱喻,達到了情感和意義共享的目的。首先,天下著大雨,在長沙擁擠混亂的街道上,行人撐傘行色匆匆,軍閥騎馬,布衣步行,都往一個方向奔去,接著導演將表現中國最底層的乞丐跪著吃地上的食物殘渣的鏡頭與資產階級小少爺坐在車中安然地吃著三明治的鏡頭進行對比,使底層百姓的可憐與上層資產階級的冷漠形成強烈反差。其次,是一頭黑色水牛被牽著鼻子走的鏡頭,水牛的犄角上掛著牽牛人的酒壇子,水牛映射著中國貧農,這些酒壇子映射著他們的耕地,水牛犄角上的酒壇子是牽牛人的,它只是麻木地享受著酒壇中散發出的酒香,隱喻著貧農耕種的土地是別人的,自己卻麻木于耕種。人高馬大的軍閥在狹窄逼仄的泥濘路上馳騁而過,隱喻著當時軍閥割據的局面,這使得混亂的中國更加狼藉。該劇將一頭水牛被牽著鼻子走的鏡頭與人高馬大的軍閥騎馬馳騁而過的鏡頭剪輯在一起,隱喻著軍閥對底層勞動人民的壓迫;將軍閥耀武揚威的鏡頭與一個賣魚的小販跌倒在地、車中的魚散落在泥水中的鏡頭剪輯在一起,顯示出魚販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在軍閥的統治下岌岌可危的境況,隱喻著軍閥對小資產階級的欺壓與剝削;將泥地上的混亂與閣樓中兩位女眷悠然的鏡頭剪輯在一起,隱喻著資產階級對當時社會的看客心態,延展了這段鏡頭的敘事空間[12]。這時鏡頭又從高降低,青年毛澤東將石塊中間的泥水一腳踏開,隱喻當時的中國正如這一灘泥水,需要一個能夠擔負使命、開天辟地的人掀起波瀾,使中國獲得新生。坐在車中吃三明治的小少爺的鏡頭與被賣的小女孩痛哭的鏡頭,隱喻著中國底層兒童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悲哀與中國上層兒童的冷漠,在這兩個鏡頭的對比中,看不到下一代人面對亂世、面對不公該有的反抗與斗爭,只能看到冷漠與妥協。緊接著是青年毛澤東逆雨奔跑過來的鏡頭,這三個鏡頭被組接在一起,隱喻著毛澤東將改變這一現狀,承擔起啟發民智、別開生面的歷史重擔。接下來是盲人拄著拐杖摸索前進和魚困于缸中這兩個鏡頭,前一個鏡頭隱喻著人們對革命道路的不斷探索,雖不知前路有何危險但仍然向前,困住金魚的缸就像魯迅先生筆下的鐵屋子,金魚看著外面的混亂卻安于自己的世界,隱喻著中國國民囿于現狀,對于屈辱的記憶如同金魚一樣轉瞬即忘。最后是一群鴨子走在街上的鏡頭,對應著“鴨子走路,左右搖擺”的歇后語,隱喻著中國社會時局動蕩,復辟與推翻的戲碼輪番上演的黑暗現狀。導演通過蒙太奇剪輯對畫外音進行了視覺呈現[13],通過蒙太奇手法將44個相關鏡頭組接在一起,從影像提供的構圖景觀角度來看[14],似乎只是街頭景觀,卻各有各的隱喻內涵,蘊含著大量的時代元素,導演用多畫面、慢動作、快節奏的剪輯方式[15],描繪了一個真實的民國,鏡頭內容以及鏡頭之間的對比、承接、并置,將中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華民族要覺醒著奮起反抗、尋求真理、救國救民的歷史任務展現在觀眾面前,增強了戲劇沖突,提升了觀賞性與思維性。
3 結語
《覺醒年代》作為一部講述思想流變的電視劇,需要傳達多種抽象的價值觀念,對劇中片段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隱喻鏡頭具有多種價值觀傳達功能。首先,隱喻鏡頭能將抽象概念具體化,通過隱喻表達導演的褒貶之意;其次,隱喻鏡頭能夠使畫面更加生動形象且具有強大的沖擊力;再次,隱喻鏡頭能夠對后續情節發展進行解釋說明;最后,隱喻鏡頭能夠與隱喻蒙太奇手法共同發揮作用,深刻表達主題思想。導演將隱喻鏡頭作為價值觀傳達方式,使畫面超越了其本身,具有更加強大且豐富的表現力,為影視語言與價值觀闡述開拓了更加廣闊的敘述空間。
參考文獻:
[1] 毛子鈺.情感觀察類真人秀節目的創新表達與價值構建[J].漢字文化,2020(11):50-52.
[2] 韓瀟瀟.國內綜藝節目“先導片”研究[J].新聞知識,2019(09):51-54.
[3] 張歡.對社會題材類電影引起情緒共振的思考——以《我不是藥神》為例[J].東南傳播,2019(02):43-45.
[4] 王汝源.新媒體視域下粉絲文化發展特點研究[J].漢字文化,2020(11):62-65.
[5] 吳一唯.《大明王朝1566》傳播失利的原因[J].藝海,2020(04):62-63.
[6] 陸春雨.懸疑推理類綜藝節目中的聲音運用[J].東南傳播,2019(08):140-142.
[7] 安曉燕.《一路書香》的敘事創新與問題審視[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9(11):103-105.
[8] 王思文.自然類紀錄片的故事化敘事研究[J].東南傳播,2020(08):138-140.
[9] 趙雅君.快餐文化下“慢綜藝”節目的發展路徑研究[J].今傳媒,2018(12):91-93.
[10] 姚穎鈺.淺論玄幻類IP的影視劇改編[J].戲劇之家,2019(03):81-82,92.
[11] 張祁.大眾傳播視域下抖音APP走紅原因的探析[J].東南傳播,2019(03):24-26.
[12] 安曉燕.類型融合背景下談話節目的敘事革新[J].中國電視,2017(5):56-59.
[13] 張祁.改革開放40年國內文化類綜藝節目的敘事嬗變[J].戲劇之家,2019(16):83-84,96.
[14] 梁明潔.新時代鄉村紀錄片的創新維度與反思[J].新媒體研究,2021(7):117-119.
[15] 安曉燕.淺論綜藝節目后期制作的角色功能轉變及其存在問題[J].中國電視,2019(7):21-25.
作者簡介:彭楠(2001—),女,江蘇蘇州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廣播電視。
指導老師:安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