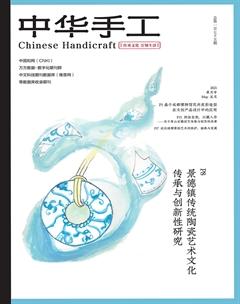師法自然 以藏入作
朱輝

摘 要: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在這里闡述的“自然”是一種不是人為造作的自然。壽山石本源于大自然的造化,天賦神韻鬼斧神工,其靈性在于出水芙蓉般的自然美,而雕刻師們的造化之功,皆取材于日月山川、人文景物、花鳥蟲魚、大千世界,“師法自然”的這一美學立場為我們工藝美術創作提供了方向。
關 鍵 詞: 壽山石雕;傳承與創作;美學
一、茶石亦道,師法自然
我們在藝術創作中所提倡與追求的自然,并不在于對形式美本身的刻板模仿,而是要將個體的意識、個體的痕跡融于自然,與自然共性和諧地相處,這種和諧更多體現的是與自然平等、親和并融為一體。福建人素愛品茗賞石,品茗賞石已經漸漸融入了福建人的日常盛會之中。殊不知,茶石亦道,師法自然。
福建是茶文化的發祥地。制茶講科學、品茶有文化這一獨特的人文特征,令福建這個歷史積淀悠久、文明承載深厚的特殊區域為世人所矚目。縱觀歷史上下,福建創制的茶類為世界之最,品茶的技藝可謂天下一絕。茶文化蘊含了茶道中的四字真諦:和、靜、怡、真,融生活哲學與藝術美學為一體。而福建壽山石雕刻藝人們在這品茗、論藝的日常中,以茶入道,以藝修心,開創了既契合于東方哲學思想的“外在儀式”,又符合儒釋道“內省修行”的茶石文化[1]。
中國人自古就有賞石、品石、藏石的愛好。文人墨客好寄情山水,徜徉自然,常以書畫抒懷表志,其壽山石印以獨特的靈氣成為凸顯山之風雅,寄寓文人情懷,彰顯個人性靈的載體。喜愛壽山石的文化名流中米芾、蘇軾、葉夢得、陸游等都是藏石賞石名家。其中,米芾“拜石”的典故已傳揚了千年。也因此使米芾在書法史上的“氣質”更顯獨特,影響自宋至今綿延不絕。而作為賞石大家的米芾,“在中國石文化中被尊為‘石圣”。賞石、藏石,看重的是奇石中所體現的拙樸、靈透、頑丑、俊逸等深刻內涵意韻,非常啟迪工藝美術的創作初衷。[2]壽山石的創作是自然美與藝術美的結合,以石代紙,根據石頭的變化無端的形狀、天然瑰麗的肌理和色彩,講究“因材施藝,因料取材”的原則,發揮每塊石材的特色。這恰恰與道教的天地與我共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尋覓“天道機趣圓融純美的意境”相一致。
二、以藏入作,傳承技藝
壽山石雕的蓬勃發展與文人階層的崛起,與書畫藝術的發達密不可分。作為一種地域性的民間傳統工藝,壽山石雕長期浸染于閩籍書畫的審美趣味,諸多閩籍近現代書畫大師也鐘情于壽山石雕刻研究,并將詩書畫印的精髓融會貫通。長期收集不同閩籍近現代書畫家的佳作,以期以藏入作吸取前人的文化積淀,借古開今不斷開拓藝術視野,提高審美文化涵養,力致跨越壽山石雕刻局限的視角,去體現表達人與自然之間的藝術感應,去感悟“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從而開創壽山石雕刻創作的新天地。
(一)以藏為養,以文化人
“胸中無書卷者,其畫絕不能佳。”閩籍著名畫家陳子奮非常注重對詩文修養的培養以及畫史畫論的研習。陳子奮著有《壽山石小志》《福建畫人傳》等書籍,這過程中資料收集、整理與輸出,有助于他日后取眾家之所長,借金石書法的筆意融入寫意畫作,投寫意天趣于篆刻之方寸,取長補短,為繪畫、書法、篆刻這三絕技藝打下堅實的基礎。當代著名的閩籍書法篆刻家潘主蘭的詩、書、畫、印嫻熟,成就卓然。其行書別具一格,若竹刀剜泥的獨特個性行筆,獨步于江湖。甲骨文法書,被公認具有“神風仙骨”,看他的字“如見八閩之魂”。金石印刻無巧無拙,渾古渾逸,恬淡平易,論及潘主蘭治印,有印詩“朝習操刀暮印人,乏金石氣腹終貧。不知款識為何物,多事牢騷議秦漢。”說明治印功在印外,不是一朝一夕便能成功的。胸中要有知識是很必要的,認為印要有書卷氣、金石氣,而最怕染上江湖氣,沾上江湖氣便不可醫了。
(二)以藏為鑒,隨心賦彩
色彩是壽山石其原本面貌最直觀的映現。色彩即可創造氣氛,展現作品獨立審美趣味,又能象征思想,表現個人情感。然則壽山石色彩萬千變化,因而一件壽山石雕作品對石色原本的屬性、面積及位置的處理和安排在不失本色的同時,如何錦上添花就值得壽山石雕創作者們不斷推敲。傳統認為,壽山石雕藝術講究“相石取巧”,根據石材、石色因勢造型,因材施藝,力致發揮壽山石的天生麗質。這與中國畫的用色準則“隨類賦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3]。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隨色象類,曲得其情”。隨色象類,可以解作彩色與所畫的物象相似。隨類即隨色象類之意,因此同于賦彩。畫壇巨擘鄭乃珖是20世紀中國畫復興運動中承前繼后的開宗創派者,對當代中國工筆花鳥畫領域的貢獻與成就,幾乎無人不提及。尤其是他對色彩的運用令人驚艷,他提出“ 隨心賦彩 ”,以表現對象為心使,為我用,為我表情,為我達意。壽山石色彩豐富,純潔干凈,一塊石頭未雕琢之時就盡顯靈氣,儼然如畫。因而在巧置色韻上與“以色貌色”“隨心賦彩”的工筆花鳥畫異曲同工。壽山石雕創作者們也正是借鑒了這種思想,掙脫表象的束縛,游刃于不同石色的形態之間,使之相關聯并更具靈性。
(三)以藏入雕,重質重工
無論是繪畫書法或者壽山石雕刻創作,都離不開對“線條”感悟。其區別在于使用工具的而不同而已。在中國畫中,用筆線條,線條的起承轉合,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表現形式,而是根植于畫者內心,外化于行的抽象審美。這種獨立于物象之外的審美,猶如道家莊子所說的“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的那種狀態,表現了畫家對中國傳統審美意境“物我齊一”的強烈追求。高超金石篆刻大家陳子奮,用筆如刀,通過篆刻切、行、頓、提、收等動作將金石碑文的渾厚老辣之氣融入白描花鳥創作中,線條的斷斷續續之巧妙暗含了生命不息的節奏韻律。
在壽山石文化生態起源和發展的潮流中,壽山石雕刻品類的選擇通常根據石材的體量和形態來確定其雕刻的樣式,其中印章是壽山石雕刻品類的上上之選,有著“印材重質,雕件重工”的說法[4]。壽山石性堅而韌,柔而易攻、石質溫潤是作為印章的優質石材,最負盛名的有印石三寶中的田黃石和芙蓉石,這也促成壽山石雕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故篆刻是壽山雕刻中的重要技法之一,這是一種在方寸間融會書法、章法與刀法一體、彰顯純熟線條功夫的傳統藝術,故篆刻素有“方寸之間見精神”之譽。傳統有言“先篆后刻,七分篆三分刻”,其中“篆”講究書法和章法的底蘊,“刻”強調刀法在印石的鑿與鑄,而能否自如與灑脫地游刃于方寸之間,使得一枚小小印章形意相生,是篆刻家和匠人的本質區別。
三、入世悟道,出世創新
當代工藝美術的創作是集大成之傳承、更是立于傳統之上的創新,現當代呈現世人面前的大部分優秀工藝美術作品,都承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工藝美術師們在尋求自我風格建構的過程中,由多樣渠道積累而成的文化積淀總能在創作構思上達成各個方向上的契合。福建具有層次豐富、底蘊深厚的文化生態,并開拓建立了繼承傳統又勇于革新的“閩學”文脈,工藝大師、書畫大家、文豪巨子盡顯,彪炳史冊。
在壽山石的創作過程中,筆者始終根植于閩地文化,博取眾家之所長,在壽山石的創作題材中,筆者認為金魚題材,是閩文化發展的一張重要的名片。首先,福州素有“世界金魚看中國,中國金魚看福州”的美譽,福州在金魚養殖上有著400多年的歷史,共有80多個品種,其中福州所特有的蘭壽品種金魚,因其優良的品質和雍容華貴的體態,被譽為“金魚之王”。而壽山石與金魚題材的碰撞,正可謂是天作之合,壽山石色澤豐富正好與五彩斑斕的金魚和其婀娜多變的體態相吻合,而金魚圓潤的身軀又正好符合壽山石的質感,金魚靈動的尾鰭又剛好與壽山石的晶瑩通透相契合,因此用壽山石來雕刻金魚可謂是上上之選。金魚也是筆者在壽山石創作中所鐘愛的表現題材,作品創作有《富貴有余》(見圖1)《金玉滿堂》(見圖2)《堆金積玉》《鶴頂當紅》等。作品中,筆者選取的是獅子頭或鶴頂紅等相類似的品種,此品種魚的特點是肉瘤發達高高隆起,體短肚圓,十分富態。在創作之初,需要反復地觀察金魚的游姿和體態,掌握不同品種金魚的生活習性,色彩特點和變異的過程,由此才可在雕刻中活靈活現地表現出金魚游弋與停駐之美。在這藝術化的處理過程中,對雕刻者的審美意識以及雕刻技藝的考驗是非常高的,金魚是世界上最有文化內涵的觀賞魚,在它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所具有的優雅、閑適、自由的生活韻味,更向世人展示著“悠”“美”“樂”“趣”的中華文化。
壽山石雕刻藝術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的傳承、文化內涵的保護是首當其沖、重中之重的問題。但是技藝的傳承并不是一味地模仿,而是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壽山石雕刻藝人在當下,與這個社會、生活、經濟、城市等所產生的聯系與問題,不斷深入思考和探究壽山石本身所承載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以及它所承載的社會意義。壽山石雕刻藝人必須在不斷學習雕刻技藝的基礎上,充分調動自身的情感與智慧,感悟生活與生命的真諦,深刻理解壽山石文化與眾多環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文化生態,才能真正地創作出優秀的壽山石雕作品。
參考文獻:
[1]楊國麗.論福州壽山石雕刻傳統技藝與傳承[D].福建師范大學,2015.
[2]張國治.“在地文化”與“創意生態”營造 ——文創產業視野下福州壽山石文化產業轉型策略[D].福建師范大學,2016.
[3]姜玲玉.師法自然 ——當代漆藝創作中的形式語言研究[D].浙江理工大學,2017.
[4]聶路,曾祥遠.閩都傳統造物的工藝文化精神[J]藝術教育.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