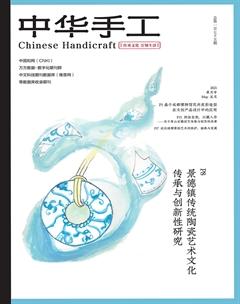董其昌行書藝術(shù)特色淺析
袁世龍
摘 要:董其昌的行書取法多元,早期宗師晉唐,取韻為上;中期轉(zhuǎn)入宋元,初顯風(fēng)貌;晚期博采眾長,獨(dú)具一格,形成了“淡”“秀”為主的行書風(fēng)格。董其昌在用筆上方圓并用,連帶牽絲;結(jié)字上勢從奇正,收放自然;章法上空靈疏朗,蕭散淡簡,影響了同一時(shí)期和清代初期的一大批書家,其中以查士標(biāo)、擔(dān)當(dāng)、沈荃等為主要代表人物。
關(guān) 鍵 詞: 董其昌;行書;藝術(shù)特色;影響
董其昌是明代書法繪畫藝術(shù)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中國書法史、繪畫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董其昌的行書更是在其書法領(lǐng)域占有突出的地位,同時(shí)也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書體,董氏開創(chuàng)了以蕭散、簡淡為主的書法風(fēng)貌,在中國書法史上形成了重要的影響。
一、董其昌行書的分期
(一)早期:宗師晉唐,取韻為上
董其昌少年時(shí)十分聰慧,其父董漢儒是一位鄉(xiāng)中塾師,在其父的影響和教導(dǎo)下,董其昌勤奮好學(xué)。隆慶五年(1571年),十七歲的董其昌參加了松江府會(huì)考,學(xué)問雖佳,卻因?yàn)樽謱懙貌睿蝗榈诙纱硕洳砰_始了他的翰墨情緣。董其昌初學(xué)顏真卿多寶塔,并受顏真卿影響頗深,持續(xù)久遠(yuǎn),后以唐書不如魏晉,故而上探魏晉,向鐘繇、王羲之的經(jīng)典法帖學(xué)習(xí),這不乏是對(duì)“取法乎上”的很好詮釋。董其昌曾在莫如忠的私塾讀書,并向莫如忠學(xué)習(xí)書法,莫氏對(duì)董其昌的學(xué)書歷程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因此,有了其“上探魏晉”的習(xí)書思想,為后來的書法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
(二)中期:轉(zhuǎn)入宋元,初顯風(fēng)貌
董其昌在二十歲至三十五歲期間,迫于生計(jì),流連于各地私塾任教,在此期間,結(jié)識(shí)了當(dāng)時(shí)有“第一收藏家”之稱的項(xiàng)元汴,得以盡覽眾多名家書作真跡,并進(jìn)行了大量的臨習(xí),對(duì)后來取法“宋元”奠定基礎(chǔ)。萬歷十七年(1589年),歷經(jīng)坎坷的董其昌終于高中,因此,開始了其仕途生涯。在京師為官期間,時(shí)常與當(dāng)朝名士切磋文藝,縱談劇論;正因?yàn)橛辛诉@些見識(shí)和交游,促成了董其昌廣闊的眼界和豐富的學(xué)養(yǎng)。中年后的董其昌書風(fēng)發(fā)生了轉(zhuǎn)變,開始將取法對(duì)象轉(zhuǎn)向宋元時(shí)期的書家。在其所著《畫禪室隨筆》中提道:“余十七歲學(xué)書……更二十年,學(xué)宋人,乃得其解處。”[1]由此可以看出,董其昌在其三十七歲的時(shí)候,迎來了其學(xué)書歷程的關(guān)鍵節(jié)點(diǎn),由于當(dāng)時(shí)晉人的書法真跡極為罕見,而宋元時(shí)期的墨跡作品傳世頗多,可以很大程度上還原古人的筆法、墨法,故而董其昌把重點(diǎn)放在了對(duì)宋元時(shí)期墨跡的學(xué)習(xí)上,其中主要向他終身崇拜的米芾學(xué)習(xí),通過大量的學(xué)習(xí),董其昌深得米芾神韻,并初顯自己風(fēng)貌。
(三)晚期:博采眾長,獨(dú)具一格
董其昌的學(xué)書經(jīng)歷,筆者認(rèn)為,應(yīng)以其三十七歲和五十歲作為兩個(gè)節(jié)點(diǎn),五十歲之后,董其昌的書法藝術(shù)進(jìn)入了成熟期,其鮮明的個(gè)人風(fēng)格和精煉熟絡(luò)的技法,開創(chuàng)了晚明書壇的新篇章。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時(shí)年五十一歲的董其昌,在擔(dān)任湖廣提學(xué)副使期間,得罪當(dāng)?shù)貏菁遥话档貞Z恿的生員搗毀學(xué)政公署;董其昌因不滿官場的現(xiàn)狀,決心不與同流合污,遂辭官歸鄉(xiāng),此后十五年內(nèi)都在江南鄉(xiāng)居賦閑。董氏或從事書畫藝術(shù)創(chuàng)作,或修禪論道,或行船訪友,過著悠游林泉、蕭閑疏曠的士大夫生活。在此期間,董其昌遍臨諸家墨跡經(jīng)典,博采眾長,在繼承與創(chuàng)新之間不斷切換,并將儒、道、禪三家的思想融入之書畫創(chuàng)作之中,展現(xiàn)出儒雅、靜謐的精神狀態(tài),最終形成了董氏自身獨(dú)特的書法風(fēng)貌。
二、董其昌行書的藝術(shù)特色
(一)用筆:方圓并用,連帶牽絲
董其昌的行書主要為圓轉(zhuǎn),方折為輔,兩者并用。圓轉(zhuǎn)之法,讓轉(zhuǎn)折處變得流暢自然,更加圓潤,棱角隨之弱化,線條愈顯生動(dòng)婉轉(zhuǎn);方筆之法,更添骨力,線條爽朗挺拔。[1]方圓結(jié)合讓董其昌行書的線條更加豐富,其行書呈現(xiàn)出圓勁秀潤、靈動(dòng)含蓄的面貌。董其昌行書另一個(gè)重要用筆則是連帶牽絲,這種用筆使得點(diǎn)畫之間聯(lián)系緊密、連綿不斷,在行書中有著起承轉(zhuǎn)合的重要作用,是行書貫通氣息、上下銜接的直接體現(xiàn)。董其昌行書中多用牽絲連帶,讓字與字組之間、線條與線條之間變化更加豐富。
(二)結(jié)字:勢從奇正,收放自然
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論用筆》中自述:“米海岳書……然須結(jié)字得勢,海岳自謂集古字,蓋于結(jié)字最留意。”[1]由此可以看出,董其昌結(jié)字對(duì)“得勢”最為重視,其行書結(jié)字也是將“得勢”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奇正變化和自然收放則是“結(jié)字得勢”的具體體現(xiàn)。董其昌對(duì)“米書”用功最多,其行書結(jié)體多以左低右高,其字勢則向右上方傾斜,以橫畫為最,豎畫也隨字勢稍作傾斜和變化,與米芾相較,董氏則略緩與米字,為其結(jié)字添加了一絲平正之感,與董氏“似奇反正”的結(jié)字思想十分符合。[2]結(jié)字的奇正為其行書添加了一股天真爛漫的自然意趣;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提道:“作書所最忌者,位置等勻。且如一字中,須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處……此皆言布置不當(dāng)平勻,當(dāng)長短錯(cuò)綜,疏密相間也。”[1]由此可以看出,在結(jié)字上,董其昌強(qiáng)調(diào)書法最忌諱等勻,少變單一,解決這一難題的最佳手段就是收放自然,長短交錯(cuò)。董其昌的行書很好地展現(xiàn)了收放關(guān)系的處理方案,行書之中更添一股神采。
(三)章法:空靈疏朗,蕭散淡簡
《畫禪室隨筆》中曾敘述道:“古人論書,以章法為一大事。”[1]由此可以看出,章法在書法的創(chuàng)作中占據(jù)很重要的位置,董其昌的行書章法呈現(xiàn)出空靈疏朗,蕭散淡簡獨(dú)特風(fēng)貌,而董氏章法最大的特征無異于字行距遠(yuǎn)、留白大黑。在眾多的古代法帖中,在章法上使董氏收獲最多的便是楊凝式的《韭花帖》,《韭花帖》的章法字行之間距離較大,留白較多,但其作品雖寬疏但不散離,空靈疏朗,蕭散簡淡。[3]楊凝式獨(dú)特的章法布局,對(duì)董其昌在章法上的處理產(chǎn)生了極大的啟發(fā)。董其昌的行書章法疏而不散,將疏密二者的關(guān)系處理得惟妙惟肖,將結(jié)字的美與字里行間的留白產(chǎn)生有與無的強(qiáng)烈對(duì)比,既營造出一種蕭散淡簡的獨(dú)特意趣,又增添了耐人尋味的極佳內(nèi)涵,這也正是董其昌在章法處理上的獨(dú)到之處,也是諸多書家鮮能達(dá)到的藝術(shù)境界。
三、董其昌行書的影響
(一)查士標(biāo)
查士標(biāo),明末秀才,清朝初期著名書法家、畫家、詩人。查士標(biāo)在明朝滅亡后,放棄舉子,潛心研究書法繪畫,書法宗董其昌,進(jìn)而由董窺探米芾,其書作蕭散俊逸,深得二者神韻,時(shí)稱“董、米在世”。[4]查士標(biāo)全面吸收了董其昌行書的精妙,與董氏相較,查士標(biāo)的用筆更加沉穩(wěn)扎實(shí),從容含蓄,少方折而多圓轉(zhuǎn)。結(jié)字上比之董氏,欹側(cè)稍顯不足,平正愈顯,字形更加方長。章法上仍是與董氏無二,空靈疏朗,蕭散淡簡。墨色上雖較濃潤,但對(duì)董其昌“淡簡”的韻味保留完好。查士標(biāo)的書法仿佛董氏書風(fēng)再現(xiàn),是明末清初時(shí)期的董氏書法神韻的重要的代表書家之一。
(二)擔(dān)當(dāng)
擔(dān)當(dāng),云南晉寧人氏。擔(dān)當(dāng)年輕時(shí)期,曾到京師應(yīng)試,得入太學(xué),而入仕內(nèi)廷,后因官場腐敗,對(duì)明朝不滿,便游歷各地,尋師訪友,使其眼界大開,詩、書、畫俱精進(jìn)。擔(dān)當(dāng)曾師事晚年的董其昌,其書法、繪畫均師宗董氏,以書法酷似,后在董氏書風(fēng)上變之,于行草書用功最甚,其勢清奇瘦勁,練達(dá)豪放。在董其昌眾多的追隨者中,只有很少人能夠真正抓住董氏書法的藝術(shù)的本質(zhì)特征,學(xué)得董其昌藝術(shù)的精髓,擔(dān)當(dāng)對(duì)于董其昌是衷心折服的,深受董氏書法理論和風(fēng)格之影響。擔(dān)當(dāng)并沒有受到明末清初那種墨守成規(guī)的影響,勇于創(chuàng)新,但由于其涉獵的名家名帖不夠廣泛,也造就了擔(dān)當(dāng)無法成為書法史上一流的大家。[5]
(三)沈荃
沈荃,清朝順治時(shí)期探花,官至禮部侍郎,謚曰文恪。書法尤有名。沈荃的父親沈紹曾是董其昌之婿,作為董氏外孫的沈荃,在少年就得到了董其昌親傳筆法,在如此優(yōu)渥的條件下,沈荃學(xué)習(xí)董氏書法造詣極高。沈荃繼承了董其昌“秀”“妍”書風(fēng),但其對(duì)于董氏書法中“骨”卻少得,由于對(duì)于骨感的缺失和遺憾,沈荃的書法較董其昌,顯得氣韻不足,神采稍遜。[6]但這并不影響沈荃在清初的書家群體內(nèi),以學(xué)董而名聲大振,成為清朝初期學(xué)習(xí)董其昌最有代表性的書法家之一。康熙皇帝對(duì)于董氏書法十分喜愛,而受到沈荃的影響,對(duì)董氏極為推崇重視,在清初時(shí)期形成了“以董為尚”的書法風(fēng)氣,對(duì)于董氏書風(fēng)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dòng)作用。
四、結(jié)語
董其昌的書法在晚明時(shí)期獨(dú)樹一幟,具有極強(qiáng)的個(gè)性,構(gòu)建出以自身為核心的云間書派,使蘇南地區(qū)的書風(fēng)得以重振,對(duì)后世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上文簡要分析了董其昌各時(shí)期行書的取法和創(chuàng)新,并對(duì)其用筆、結(jié)體和章法,以及對(duì)同一時(shí)期和清代初期乃取法董其昌的啟示和影響進(jìn)行總結(jié)。董其昌的行書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博采眾長,并形成自身獨(dú)特的風(fēng)貌,可謂是獨(dú)一無二。在董其昌之后的一大批書家中,都選擇由董氏入手,進(jìn)而上探宋元乃至?xí)x唐。他的書法,被視為千年文人流派書法史的縮影,也是對(duì)二王帖學(xué)的繼承與發(fā)展,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xiàn):
[1]孫小雯.董其昌行書技法對(duì)創(chuàng)作的啟示[D]:濟(jì)南:山東建筑大學(xué),2020.
[2]黃.中國書法史——元明卷[M].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09.
[3]吳耀明.董其昌的生平和家世論書[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2010.
[4]樊海濤.擔(dān)當(dāng)?shù)臅L(fēng)演變及作品鑒定淺談[J].中國書法報(bào),2021.
[5]梁驥.沈荃、王鴻緒、張照對(duì)董其昌筆法傳承考[J].中國書法,2019.
[6]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一)[M].杭州:浙江美術(shù)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