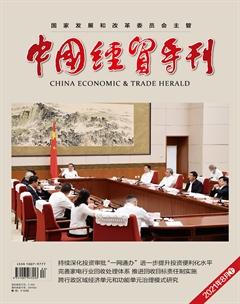加快氫能產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幾點建議
梁鵬
目前全國已有30多個省市(包括副省級市和地級市)發布氫能和燃料電池產業發展規劃及支持政策,所有項目加起來到2025年規劃車輛超過10萬輛、總產值規模超萬億。隨著我國氫能產業快速發展,依賴國外的一些關鍵元器件、零部件、原料和設備存在“斷供”風險。面對這種局勢,需要統籌國內國際資源、兼顧當前與長遠,發揮舉國體制優勢全面做好應對。
一、我國氫能產業面臨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挑戰
氫既可以通過燃料電池發電應用于汽車等交通工具或熱電聯產,又可以作為原料用于化工、冶金等行業。通過氫既可以實現可再生能源、核能和化石能源等的融合發展,又能實現能源與交通、化工、冶金等行業的互補升級。發展氫能技術,對保障我國能源安全,實現清潔低碳發展,推動能源技術革命和產業升級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國內初步形成氫能制備、儲運、應用等比較完整的產業鏈,制氫技術相對成熟且具備一定產業化基礎,但氫能儲運、加注、燃料電池等技術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例如質子交換膜、鉑催化劑、碳紙和膠粘劑等關鍵材料,以及氫氣循環泵、70兆帕(MP)加注卡口等核心零部件主要依賴進口。
二、氫能產業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主要原因
發展格局與實現創新引領發展的目標不相適應。某些地方政府簡單從新能源汽車或傳統動力變革角度看待氫能,存在“發展地方性產業的束縛”,社會上對氫是未來的技術還是現在就可以較大規模應用的技術看法不一。有的政府機構和企業在立足未來能源生產與消費革命的宏觀歷史視野認識和定位氫能方面還不深入全面,相應地,我國氫能產業創新體制、資源配置、政策體系還與“強起來”的要求不盡適應,整體上是“跟蹤追趕”。以燃料電池技術為例,國內骨干企業如廣東國鴻氫能科技有限公司、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先后以技術許可方式引進加拿大巴拉德動力系統公司生產線,有逐步形成對國外技術的路徑依賴傾向。
基礎科學源頭創新供給和支撐不足。基礎研究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在氫能科技領域,國內基礎研究較為薄弱,獨到創新不多。與氫儲運相關的抗氫脆氫腐蝕耐疲勞的金屬材料、耐低溫的密封材料、高效冷絕緣材料等材料科學,與燃料電池相關的電化學機理過程,與氫安全技術相關的泄露、燃爆等基礎理論研究不深。分布式發電、熱電聯供等氫能與其他一二次能源的交互技術鮮有研究,基本還處于空白狀態。
關鍵領域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我國進行氫能和燃料電池的研究開發已經有40多年的歷史,2006年發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對相關關鍵核心技術進行了前瞻的科研布局和政策引導,對項目研發攻關投入了一定資金和人才。但是在研發的樣品和樣機某些技術性能達標后,對后續高度復雜和困難的產業商用研發,缺乏長期堅持攻堅。以鉑催化劑為例,我國科研院所發表了很多論文也開發出了樣品,但在實際電堆上難以應用。
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尚需探索。相較于日本通過隸屬于經濟產業省(METI)的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的良好機制,組織產業鏈龍頭企業參與,匯聚政產學研用力量集中進行科研攻關,知識產權實行內部共享,快速實現技術突破。國內片面強調某一地區或幾個單位的“產業組合”自身的“全面掌握核心關鍵技術”,造成寶貴科技研發資源浪費。例如,不少涉氫央企、國企和民企各自都在瞄準燃料電池電堆技術進行研發,但基本上是各自為戰,技術路線各異、專業人才稀缺、圈內互相挖人現象突出。
三、加快氫能產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建議
關鍵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美西方在關鍵核心技術(如高端芯片、高水平光刻機、基礎軟件等)對我國的遏制及高強度打壓再次警告我們,關鍵核心技術既靠不住“朋友”又靠不住國際規則更靠不住商業利益。缺少“0到1”的重大突破,就無法有效解決“1到10”的升級和大規模先進技術的產業化廣泛應用,必須系統布局,打通氫能產業鏈國內大循環的堵點。
(一)結合實際國情定好科技創新路線
創新主體上,以水電、風電、光伏發電企業、氣體及特種裝備企業等為主體,布局建設氫能制儲運加產業鏈;以燃料電池發動機企業及相關配件、材料企業等為主體,布局建設燃料電池產業鏈;以汽車企業、空調企業、分布式能源企業等為主體,布局建設燃料電池汽車、分布式發電系統、熱電聯供系統等氫燃料電池應用裝置產業鏈。技術體系上,以燃料電池產業為戰略中樞,在上游設計好“綠氫”(可再生能源制氫)為主“灰氫”(工業副產氣制氫)短期過渡等產業技術協同發展;在下游設計好可再生能源規模化氫儲能及上網、微網氫電循環等產業技術銜接。
(二)擴大“0到1”基礎研究創新要素有效供給
對標美國氫能國家實驗室研發聯盟,以潔凈能源國家實驗室為龍頭,以涉氫國家重點實驗室為核心,相關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技術創新中心、高水準大學及一批骨干龍頭企業,與中國氫能源及燃料電池產業創新戰略聯盟(2018年由國家能源集團牽頭,國家電網、東方電氣、航天科技、中船重工、寶武鋼鐵、中國中車、三峽集團、中國一汽、東風汽車、中國鋼研等多家央企發起成立),共同打造戰略科技力量。氫能產業涉及能源、材料、裝備制造等多個領域,要整合優化科技部、工信部、能源局等部門現有的專項資金支持政策,面向關鍵材料等“卡脖子”環節實施攻尖工程,強化創新的物質技術基礎。
(三)激發創客在“1—10”產業創新中活力
在有氫能產業發展基礎的城市群探索建設多層次的氫能產業新型研發機構即產業創新中心,提供公益性實驗環境降低創新成本,使“重資產”特征明顯的氫能產業對創客不再高不可攀。通過“揭榜掛帥”方式,吸引中小微企業創業創新團隊到產業創新中心,實現理念到產品的轉換,提供常態化的知識產權產出流。新型研發機構不完全是企業性質,該實體在研發方面獨立運營,不受投資方、參與建設方以及政府干預,研發成果并非屬機構所有而是屬研究團隊,機構僅作為條件及資源提供者,參與研發成果轉化收益分配。
(四)優化國資在“10—N”應用創新中布局
企業層面,涉氫骨干國有企業要順應數字經濟時代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平臺化趨勢,逐步開放研發、廠房、設備、物資、渠道等優勢資源,推動制造能力平臺化,通過產業互聯網組織制造資源,打造開放的生態平臺,與民營企業做好產業鏈協同、技術協同、管理協同等,支持民營企業走好“專精特新”的路子,構建富有活力的產業互聯網創新生態。資本層面,氫能產業發展最大的問題是資金籌集困難大,國有企業要有擔當精神,在“專精特新”領域,先期以國資股權投資形式為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民企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后期在產業化發展步入正軌并保障國有資產適當增值收益前提下,可及時轉移控股權或者控制權,避免曾發生過的燃料電池領域明星企業上海新源動力有限公司因國資股權改革久拖不決,導致企業喪失創新活力事件再次發生。
(五)推進更高層次國際創新合作
要充分利用好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和率先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危機優勢,高質量推進離岸科創孵化器建設。依托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海南自由貿易港,制定氫能產業引才規劃和國別策略,按照“不求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原則,把人才智力引進更好地融入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全局,讓更多境外高端人才、數據信息、專業服務對接國內市場。同時,避免國內因中美博弈出現泛政治化傾向,繼續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增強對國際氫能領先企業的吸引力,支持其研發、生產落戶境內,更好發揮外資企業“外引內聯”的獨特優勢,逐漸形成“捆綁”格局,使相關公司不愿也不能與我“脫鉤”。
(作者單位:中國國際經濟中心信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