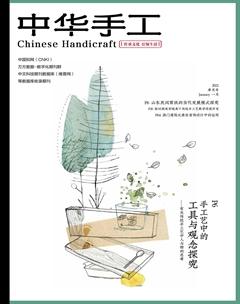從文化的角度探究中國木偶戲藝術與西方元素融合的演變
黃冉冉
摘 要: 中國木偶戲在現代是一種常見的戲劇藝術表演,其利用木偶來表演故事的戲劇形式深受大眾歡迎。但中國“木偶戲”的現代語義與古時相比,具有全然不同的含義。這其中的語義變化與西方木偶藝術元素的融入具有密切的關系,木偶戲在西方同樣作為一種大眾喜聞樂見的表演形式,其隨著時代的發展被傳入中國,在當代審美方式、文化理念、娛樂需求的多種因素促進下,其不斷影響著中國當代木偶戲形式的最終呈現,因此本文試圖從文化的角度探討中西方木偶戲在時代下不同元素的相互融合以及演變過程。
關 鍵 詞: 木偶戲;懸絲傀儡;中西方;儀式象征
一、中國木偶戲的文化背景及其歷史沿革
中國的木偶藝術源于漢代,興于唐宋,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是中國一門歷史悠久的戲劇藝術表演形式,其經過數百上千年的傳承,經久不衰。
早在漢代就已經有了關于木偶戲的歷史記載。《后漢書》載:“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儡,酒酣之后,續以挽歌。”[1]通過史料的記載,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經出現了表演形式完善的木偶戲。而后木偶戲依舊在不斷壯大發展,到了宋代則達到了興盛時期,并且木偶戲的劇目題材、表演種類也越來越豐富,木偶的制作技術也越來越高超,對木偶的神情刻畫達到了惟妙惟肖的境界。時至今日,中國的木偶藝術仍在不斷傳承,并且享譽海外。
木偶戲在全中國的不同地區都有各自的發展,而泉州木偶戲是中國木偶戲發展歷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泉州木偶戲古稱懸絲傀儡,1957年定名為線戲。關于懸絲傀儡戲傳入閩地的時間并無明確的歷史記載,但能夠確定閩地是木偶戲傳入較早的地區,時間范圍大概在漢晉時期,由于永嘉之亂致使中原地區動蕩不安,大批人口紛紛南下避亂,木偶戲隨著人口的流動而被帶到了閩地。就福建的懸絲傀儡戲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大致興于唐、盛于宋、繁衍于明清,轉換發展于現代[2]。由于福建地區相對和平的歷史環境,木偶戲在此得到了良好的發展與傳承。
中原地區作為古時經濟政治的中心,在戰亂的影響下,中原人口不斷向相對穩定的南方開始遷移,使得中原文化得以在南方傳播。因為藝術的形式發展與演變總是脫離不開經濟政治、宗教信仰以及文化思潮的影響,木偶戲在傳入南方地帶以后,同樣也發生了形式乃至語義上的轉變,其表演風格的最終呈現是不斷融入當地元素以及審美習慣的結果,并衍生出了各種新的表演形式以滿足當地人民的精神需求。
二、中國與西方木偶戲異同之比較
西方的木偶戲在世界范圍內同樣享有盛譽,這種藝術表演形式并非東方所獨有,全球五大洲幾十個國家,都有木偶戲演出的傳統。雖然中國的木偶戲發展歷史相較于西方更為悠久且源遠流長,但同樣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以及獨特的藝術價值。丁言昭在總結世界上木偶戲的共性后曾指出:“木偶戲是集劇本、導演、演員、舞美、人物造型、音樂、燈光為一體的綜合性表演藝術。”[3]當然,由于社會歷史、宗教信仰和文化風尚差異的影響,木偶戲在中西方呈現出全然不同的風格與形式,并且文化語義也不盡相同,各個地區都將木偶藝術內化為當地獨有精神內涵表達的一種方式。
首先是西方的木偶戲,它的發展源于基督教會的傳教活動。當時的基督教會將圣經教義和故事用木偶的方式編排成表演,以便讓不識字的平民能夠理解接受基督教思想。在重大的宗教節日,如圣誕節和復活節時,教堂往往會舉辦盛大演出來講述圣經故事。比如教堂往往會以七個木偶來演繹基督教義中的“七宗罪”[4]。之后木偶戲的表演不再僅滿足于基督教會的功能性需求,其受眾范圍不斷向民間擴大,逐漸成為西方社會喜聞樂見的一種戲劇表演形式。
其次,中國傳統木偶戲與西方木偶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通點的是,其最剛開始的衍生同樣是為了滿足于宗教需求。古代巫術中的偶人是木偶形象的起源,通常被用于祭祀活動之中。木偶在祭祀活動中常常作為一種“偶像”的替代,常常作為百姓溝通神靈的媒介,企圖通過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而達到目的。這種宗教式的儀式不僅存在于祭祀活動之中,尤其在閩南地區,傀儡戲同樣作為一種信仰崇拜,出現在賓宴喪喜儀式之中。而隨著歷史變遷和各種文化領域的交融,懸絲傀儡戲儀式的宗教巫術性逐漸褪去,進而更多地成為一種語義更為豐富的戲劇表演形式,從原本的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演變為歷史的再現、文化傳播以及娛樂大眾的藝術表演。
關于中西方的木偶藝術的區別的論述,首先可以將焦點聚集在受眾群體上。雖然中西方的木偶戲表演在最開始都是為了滿足宗教教義的需求,但兩者面向的群體卻全然不同。西方木偶不同于中國傳統木偶戲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其服務教育、服務兒童。但對于懸絲木偶這類作為地方儀式象征的表演形式,兒童從來不是懸絲木偶戲的優先觀眾,甚至他們在“加禮戲”演出場合存在諸多的參與禁忌[5]。
西方的木偶戲更像是面向大眾的藝術,其作為一種傳播宗教信仰并且將思想理念廣泛傳播的手段,其面向的群體通常都具有普遍性、普及性。而在泉州地方民眾對木偶戲的認知理解中,懸絲木偶戲并不是一種單純娛樂性的表演藝術。在閩地人民的觀念里,懸絲傀儡戲是一種神圣的象征,其觀眾通常都將自身的愿望依托于人偶之上,整個表演儀式只有將觀眾與人偶乃至操控人偶的表演者融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
三、中西方木偶戲元素融合的探討
通過前文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木偶戲在古代通常作為一種宗教儀式的“偶像”而被頻繁使用,并且在中國古代典籍的記載中,木偶的表演一般都被稱為“傀儡戲”,并沒有“木偶戲”這一詞語。但時至今日,“木偶戲”一詞幾乎已經成了“傀儡戲”的替代,成為了這一傳統的正式文本稱謂,并且木偶戲作為一種儀式象征的內涵卻不再被強調凸顯。
這種文化表演方式、文化語義的改變正是西方木偶文化元素影響下的結果。尤其在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世界各地的文化在各地之間相互傳播與影響,元素之間不斷碰撞與融合而發展出新的形式風貌。
據郭紅軍研究,在19世紀中后期,至少有三個西方木偶劇團來上海面對中外觀眾進行劇場演出[6] 。而到了1930年左右,一大批上海進步文人開始效仿西方木偶戲的表演形式來改革傳統木偶戲,就在這期間將木偶戲的受眾群體定焦為兒童,利用人偶來編排兒童喜歡的故事情節,這徹底打破了中國傳統懸絲木偶戲中的兒童禁忌。這種新型木偶戲其實就是用木偶來演話劇,所有的服飾、造型和劇情都是采用西方木偶戲的內容形式、不重視人物動作的性格刻畫,與我國傳統傀儡戲表演根本不同[7]。但從某種意義上講,其藝術形式的變革是一種成功的創新,中國木偶戲因在大眾中的普及而得到了持續的傳承。
上述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木偶戲在西方木偶戲的影響下改變了其表演形式針對的受眾群體,而受眾群體的改變也就意味著劇目表演的題材、表演形式以及藝術語言等元素都要進行相對應的變革,而這場變革之中又脫離不開以西方藝術為模板的借鑒。無論是劇目題材的選擇還是最終舞臺的呈現形式,都體現出了對西方木偶藝術的形式借鑒。
四、結語
總而言之,當今時代下中國的木偶戲已經不完全等同于中國傳統的傀儡戲,它在表演形式、技術效果、針對群體、象征意義上都受到了西方木偶戲元素的影響。在面臨這種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影響時,一方面可以認為這是追求現代性文化創新的延續,但另一方面這也是對中國本土傀儡戲藝人遺產運動的現代性挑戰。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中,懸絲傀儡戲受到各方面文化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除了要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創新意識之外,更重要的是應當恢復與保留傳統懸絲傀儡戲中蘊含的禮樂精神,因為禮樂精神作為中國古代思想的根基,對于社會的發展以及人民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指導作用,從古至今融匯于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因此,對于傀儡戲傳統文化傳承的保留與革新,應該做出深度的思考。
參考文獻:
[1](南朝宋)范曄著.后漢書[M].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06:3273.
[2]葉明生著.福建傀儡戲史論 [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
[3]丁言昭《談談中西木偶》[J].《戲劇藝術》,1996(1):60-69.
[4]瑪格麗特·索瑞森,朱凝.歐洲木偶劇淺談[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09,131(1):93-99,151-154.
[5]魏愛棠著.加禮的記憶泉州提線木偶戲的遺產認同研究 [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6]郭紅軍.近代西方木偶戲在上海演出考略——以《申報》廣告為中心[J].戲劇文學.2016,(6):142-147.
[7]虞哲光編著.木偶戲藝術[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