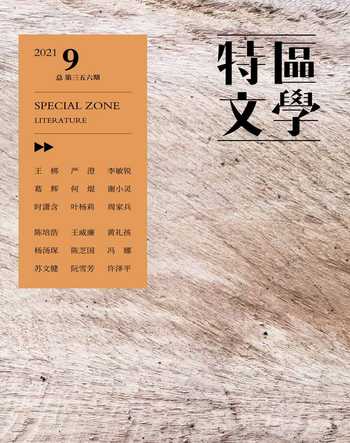以柔軟之心,抵達鋒芒之境
一
如果倒回頭去看1999年的澳門,雖然作為賭城的繁華并沒有因為即將到來的回歸而有絲毫的衰減,但一種內(nèi)在的文化認知早已悄然確立:這是一座中國的城。在談到澳門的文化屬性時,姚風曾有這樣的論斷:“盡管葡萄牙統(tǒng)治澳門逾四百年,但澳門的文化主體依舊是中國文化,葡萄牙語雖然是官方語言,但從來沒有普及到普羅大眾當中去。葡萄牙人帶來了自己的文化,也使之成為澳門文化的一部分,但澳門仍然較好地保持著中國文化的傳承,它仍然是澳門文化的主體,雖然葡萄牙在漫長的歷史中依靠政治和行政手段成為主導文化,但僅僅局限于精英階層和行政管理層面,它始終沒有能夠統(tǒng)御中國文化。”
姚風,1958年出生于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葡萄牙語專業(yè)畢業(yè),1988年后調(diào)往外交部,后在中國駐葡萄牙大使館工作,期間嘗試用葡萄牙文寫詩和翻譯。1992年,姚風移居澳門,在澳門大學葡文系任教,后又擔任澳門文化局副局長。在他的身上,疊加著外交官、詩人、翻譯家、學者、文化官員等多層身份,因此,姚風的視野非常開闊,他曾明確表示自己并不喜歡被定位為一個“澳門詩人”。澳門對姚風來說是一個居住地,一個生活、觀察和寫作的空間切入點,但并不是全部。姚風直接涉及澳門的詩歌很少,他主要面對的是一個文化的中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我的學習經(jīng)歷、知識結(jié)構(gòu)、曾經(jīng)的內(nèi)地生活、中國的歷史,都有關系。我的詩歌關心文化的中國、政治的中國、地理的中國、歷史的中國……漢語又是全球的,文化中國是屬于全球華人的,每個漢語詩人都帶著一個‘中國’。”
如果拋開澳門作為固定空間地域這一限制,這里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文化觀測地,中西文化在這里交匯,不同的歷史和觀念在這里碰撞,而姚風身上相對復雜的經(jīng)歷,能夠讓他更為冷靜地去觀察和體悟生活。因此,澳門這個小小的空間,反而成為了他觀察和思索的一個高地。實際上,正是在澳門(而不是其它地方),姚風成為了姚風,他的雙語背景和跨地域、跨族群的文化認知,使他成為了一個具備全球視野的漢語詩人—也即“華語詩人”。
二
在閱讀姚風著作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了姚風和他的不同分身之間構(gòu)成的豐富性和互文性,這些分身是:作為翻譯家的姚風,作為詩人的姚風,和作為學者的姚風。
作為翻譯家的姚風,以其對葡萄牙詩人安德拉德的精妙翻譯,至今在詩歌翻譯界享有著極高的聲譽。作為一個不懂葡文的普通讀者,我們對安德拉德的每一點想象,都來自于姚風優(yōu)美譯筆的重塑。換句話說,安德拉德正是通過姚風的譯筆鮮活地活在了漢語世界中,并對許多漢語詩人產(chǎn)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影響。
作為詩人的姚風,充滿著現(xiàn)實主義的冷峻,跟他譯筆下的安德拉德相當不同(至少在筆者看來是如此)。而作為學者的姚風,通過諸多的散文和隨筆,關心著中華文化的源流;思索著澳門的前世今生,對它的現(xiàn)狀時時流露出一種高屋建瓴的隱憂;辨析著詩歌的技藝和意義。學者的高度,反過來增進了他自己翻譯的嚴謹和詩歌創(chuàng)作的純粹。
而我更感興趣的是,作為翻譯家的姚風是如何影響到他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正因為他自己也寫詩歌,所以,詩歌翻譯在他這里就不僅僅是一種翻譯,而是一種“寫作—作為翻譯的寫作”。姚風的翻譯,重要的地方在于他致力于對原文的“重生”,他說:“翻譯詩歌,譯者必須對詩的語言表現(xiàn)出敏感,他所塑造的詩人,不應是在譯文中徹底死亡的人,而是要考慮如何使作者‘像一個詩人’繼續(xù)在譯文中生存,而不是急于宣判他的死亡和自己的‘誕生’。一首成功的翻譯詩歌,應該是作者、譯者、讀者三位一體達成的一個‘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契約。”又說:“譯者絕不是唯唯諾諾的奴仆,也不是假傳圣旨的太監(jiān),他在兩種語言中擰成的鋼索上行走,時刻都在保持平衡,以求盡量完美地抵達終點……譯者要尊重并服從語言的限定性,同時也要放眼語言的開放性。”
在被限定的語言空間中,以一種走鋼索式的平衡,姚風創(chuàng)造出了漢語詩歌中的“安德拉德”。這是安德拉德在漢語中的新生,也是姚風自己“作為翻譯的寫作”的重要成果。在我看來,這些優(yōu)秀的譯作,是作者和譯者共同創(chuàng)造的結(jié)果,這兩者的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成就這些優(yōu)美的文字,只有合力的再生,才使安德拉德的詩歌在另一種語言中開出了鮮艷的花朵。姚風的翻譯經(jīng)驗,應該在翻譯界特別是詩歌翻譯領域被廣泛借鑒,但現(xiàn)實是,擁有著詩人和翻譯家雙重視野和經(jīng)驗的人何其之少,這也是國內(nèi)詩歌翻譯界良莠不齊的一個原因。一個優(yōu)秀的詩歌翻譯家,除了在語言上過關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她)還得是一位詩人,再不濟,也應該具備某種詩人的眼光。
姚風在安德拉德的詩歌翻譯中肯定獲得了某種東西,但奇怪的是,在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安德拉德的影響卻顯得如此隱晦,至少,在他大部分的代表作中,安德拉德那種充滿著抒情意味的修辭方式,那種婉轉(zhuǎn)吟唱的詠嘆調(diào),在姚風詩歌中極難找到。如果把視野放得更大一點,除了安德拉德,姚風還翻譯過很多的詩人,包括但不僅限于拉莫斯·羅薩、庇山耶、卡西米洛·德·布里托、安東尼奧·西塞羅、胡安·赫爾曼、聶魯達。如果說這些之間有什么相似之處,我想,應該是追求翻譯的凝練與傳神,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信達雅”。在一個訪談中,姚風說自己的“語言精練到只剩骨頭不要脂肪”,這當然是某種“綜合因素”造成的,但“翻譯者追求語言簡潔的工作方式”是其中不應被忽略的部分。
我曾猜想過這樣的翻譯過程:作為詩人的姚風,在翻譯時不自覺地會以一個詩人對語言的敏感性要求著翻譯盡可能地達到“詩的盡美的高度”,而作為譯者的嚴謹則在另一方面不斷地提出問題和限制性的意見,在這樣反復地磨合中,譯詩以一種盡可能趨近完美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因此,翻譯的過程,不亞于是一場“帶著鐐銬的創(chuàng)作”。這種翻譯,一定會逐漸滲透進詩人的創(chuàng)作,“簡潔”因此可以看作是姚風從翻譯上獲得的某種來自于語言的饋贈。
三
“詞語/如同一塊水晶。/有些詞語,是一把匕首,/是一場大火。/有些詞語/僅是露珠而已”(安德拉德《詞語》)然而就算對待“露珠”,安德拉德也及其珍視:“即使蒼白/也讓人想起碧綠的天堂”。一個詩人應當是對世間的一切予以同等尊重的人。雖然他(她)會有不同的喜惡,但從不輕視事物內(nèi)在的火焰。
優(yōu)秀的詩人,每一個詞語都能在他的筆下找到相應的位置,但詩歌寫作不是詞語的游戲,而是一場事關內(nèi)心和靈魂的拷問。“以前寫詩,也迷信‘詩歌是語言的藝術(shù)’的說法,熱衷于詞語的煉金術(shù),寫下的詩句或許漂亮,但就像蝴蝶圍繞著花枝尖叫,僅僅是漂亮而已。而現(xiàn)在,我完全做了叛徒,背叛了以前的詩歌。我不再過多地考慮一首詩的語言或者形式,我認為那必須寫出的,只要飽滿和成熟,就會找到自己的皮肉。”通過他自己的表述,我們看到,姚風關注的,不再是詞語的表象,而是事物的內(nèi)核,并且希望借此企及某種人性的關懷:“人們熱衷討論‘如何寫’和‘寫什么’孰輕孰重的問題,但我更關心的,是如何讓我的寫作更加‘人性化’,關注生命,自己的生命和別人的生命。堅強有力的詩歌,應該是從內(nèi)心最柔軟的部位出發(fā)的。”
內(nèi)心的柔軟使姚風的詩歌在某些方面充滿了對生命的關懷和悲憫。這些關懷,并不僅僅局限于人類,而是在一種平等的視野中,把人與物,人與自然,人自身都納入了思考的范圍。
菜單上,寫滿動物器官的名字
濁浪翻騰,煙霧繚繞
模糊了彼此的面孔
我們一邊呷飲啤酒
一邊打撈片片煮熟的尸體
弱肉強食的法則之下
總要屠殺一些生命,維持另外的生命
總要切割一些身體,喂養(yǎng)另外的身體
我們食欲旺盛
談笑風生
絲毫沒有感受到生命的悲哀
—《火鍋店》
很多時候,作為高高在上的人類,總是認為我們對動物賦有生殺予奪的權(quán)力,完全沒有顧慮到它們也是活生生的生命。“我們食欲旺盛/談笑風生”,顯然,姚風并沒有讓自己置身事外,在悲憫的同時,也把批判指向自己。在另外一首廣為人知的《老馬》中,姚風進一步把人與物的天平,放到了一個更為平等的位置上:
我坐在縣城嘈雜的小酒館
望著你用盡力氣低下頭
把大車拉上斜坡
卻用你不懂的語言說一聲:
老馬,進來喝一杯吧
—《老馬》
比《火鍋店》更進一步的是,《老馬》把馬被奴役的悲慘描繪得更令人同情,馬(物)獲得了我們某種情感上的認同。因此,在詩歌最后,詩人把同情上升到人與物之間的平等:“進來喝一杯”。但是,反諷也恰恰在此刻出現(xiàn)了,一種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的“人與物”的不平等,加重了結(jié)尾的悲劇性。馬自然聽不懂人的語言(人的語言何嘗不是一種來自更高等動物的壓迫),詩人自然也就無法使人與物處在平等的對話環(huán)境中。悲憫自然轉(zhuǎn)化為了一種無奈和辛酸,這又反過來加重了詩人對馬(物)的命運的嘆惋,和讀者對于生命的感知和反思。
對于“物”的親近,一方面來自對生命尊重,一方面來自于詩人對內(nèi)在“純真”的追求。當一個人看清了現(xiàn)實的爾虞我詐,看慣了時代的喧鬧和庸常,就更愿意進入到一個人與物、人與自然相和諧的世界。在《喜歡一頭畜生》里,姚風寫了一匹自由吃草的馬,它“明亮的眼睛里沒有摻雜一絲雜質(zhì)”,這種無有思慮的純粹,使得詩人產(chǎn)生了一種羨慕和柔情,“在我孤獨的內(nèi)心,在這易變的塵世/喜歡一頭畜生/比喜歡一個人更加容易”。
除了追求人與物的平等,姚風還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像《趙四》《尹士存》《李文強》《庫比多》《盧先福》等詩歌,閃爍著人性之光,詩人與他筆下的人物是平等的,沒有居高臨下,只是平緩地敘述中呈現(xiàn)出人物的悲傷喜樂。姚風寫的雖然是個體的生命經(jīng)歷,卻讓人感到詩人是在對廣闊的“人的生存”作出自己的考察,在不動聲色中,表達了一種理解和同情。
在這其中,《李文強》一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詩歌中有一種時代的對比,“我”和同學在三里屯邊喝酒邊看街上性感的女子,我們放縱著自己的感官;而站在另一個時代(“改革開放”前)的語文老師李文強,卻因為一個不曾證實的“猥褻罪”,被當成“流氓抓走了”,“他目光憂郁,面孔總是一片黑夜/有人罵他是流氓,向他吐唾沫/他也一言不發(fā),像個啞巴/手拿一把錘子不停地敲打/后來,護城河發(fā)現(xiàn)李老師的尸體/已被河水泡得不再矮小”。在今昔比對中,詩人對李文強的死有一種深深的遺憾和悲哀,時代的過錯,仿佛也成為了詩人內(nèi)在的一個悲愴的傷口。因此,詩人對歷史、時間或某種宏大的總體感總保持著一種警惕,這也常常在他的詩歌中以某種反諷和批判的鋒芒呈現(xiàn)出來。
四
柔軟和鋒芒是一對有意思的詞,它們總是以一種看似相互悖反、實則殊途同歸的方式彼此依存。鋒芒是因為內(nèi)心有必須要守護的“柔軟之地”;柔軟是內(nèi)心葆有著現(xiàn)世邏輯里難以生存的“珍視之物”,為了這一“珍視之物”,不惜以全部的“鋒芒”來對抗現(xiàn)實的壓力。從“內(nèi)心最柔軟的部位”生發(fā)的姚風的詩歌,在我看來具備著不可忽略的“鋒芒”,這些鋒芒至少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現(xiàn)實、歷史和世界的介入和發(fā)言,這其中必然涉及到反思和批判;二是對自我的探尋、挖掘和展露,這是一種知識分子式的內(nèi)在觀照,把自我的弱點放在強光下聚焦,摧毀所有的面具而讓自己重新做一個“純真”之人。但需要提及的是,這兩者并非截然分離,外在的批判也是對自我的一種調(diào)整,而自我的審查也會在某些情景下轉(zhuǎn)化為對現(xiàn)實的凝視。
《為大平煤礦死難礦工而寫》一詩的批判性顯而易見,但這種批判根植于姚風對生命的敬畏和對底層苦難的感同身受。這首詩應該拆開來看,先是對事件的描述,生命在瞬間被毀滅,成為了冰冷的數(shù)字和物件:“一具尸體抬出來了/又一具尸體抬出來了/再抬出來的,還是一具尸體/烏黑,但堅硬,像劣質(zhì)的煤塊”;接下來是一種冷入骨髓的同情:“你們,即使在爆炸中/也沒有感到溫暖的你們/被送進了爐火熊熊的火葬場”,“溫暖”看似褒詞,但在這里反用,成了全詩的催化劑。一群礦工在沒有陽光的地底下冰冷地活著,生活給予他們的煎熬和苦難誰曾在意過?誰溫暖過他們?而反諷的是,在詩歌的結(jié)尾,在火葬場里轉(zhuǎn)化為煙霧的他們,“被納入了國家的供暖系統(tǒng)”,“溫暖”了千家萬戶。對生命易逝的悲涼,對生命難言的苦難,姚風有一種不甘之嘆。他結(jié)尾的反諷,何嘗不是對現(xiàn)實的一種批判?人們總是習慣在災難發(fā)生后去同情苦難中的個體,礦難(以及其他災難)時不時地發(fā)生,仿佛只有發(fā)生了,我們才意識到這個世界上還有那么多苦的人,但這是不對的,一個更有溫度的社會,應該是把對個體的關懷,納入到每一個普通的日常當中。
在其它一些詩歌中,姚風的現(xiàn)實憂慮甚至跨越了國界,“世界就是一個現(xiàn)場/爆炸、搶劫、強奸、拐賣、兇殺……/每一分鐘都在發(fā)生/監(jiān)視、抓捕、拷打、審判、坐監(jiān)……/無時不在進行//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嫌疑犯”(《絕句·49》),“轟炸機撕破晴朗的天空/身份模糊的民工被活活打死/只有病沒有錢的人被醫(yī)院拋在郊外/子彈把學校的孩子制成一具具尸體/蒼蠅厭惡了一張張饑餓的臉龐。”(《一個人的世界》)從這些句子不難看出姚風的現(xiàn)實主義傾向,他的道義感和擔當,早已超出了國界,而成為對世界文明的一種觀照和反思,這其中,作為人的生存處境,是他關注的焦點。諸多的外在世界的苦難,甚至常常成為他自身苦難的一部分(“和眾人一起/屬于這無邊的黑夜”《一個人的世界里》)。
當向外的鋒芒乃至批判不能分擔和消解現(xiàn)實的苦難時,一種內(nèi)在的視點必將油然生發(fā)。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姚風詩歌中同樣存在大量對自我探尋的詩作。孔子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改變外界是艱難的,但對自我的堅守,也是另一個向度的鋒芒。
而我不是河流,不是大地
甚至千瘡百孔的身體
不是一塊海綿
在水中,我只是一頭容易腐爛的動物
—《黃昏的雨》
姚風對自己有一種獨到的清醒,就算在向內(nèi)的觀照中,也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具備非凡能力的英雄。相反,他在更大限度上承認了自我的脆弱(“一頭容易腐爛的動物”), 努力保存著內(nèi)心最后的純真(“為了治愈那片天空/我漸漸代替了鳥兒的位置”《治愈》),并嘗試平衡與其他事物之間的平等關系(《大海真的不需要這些東西》)。
“我和你們一樣,臉上也囤積著/越來越多的時間/只有心中的鏡子越擦越亮/亮得一塵不染,/亮得只剩下一個物體”(《歡聚》)。在這里,“心中的鏡子”是存在于現(xiàn)實世界之外的“自我之地”,是一處可以反復“擦拭自我”,“重塑自我”的再生之地。在另一首詩中,他寫道:“我要找到你/我在黑暗中穿過鏡子/披了一身的破碎//我依然在鏡中/擁有鋒利的抽象與具象”(《鏡中》),“鏡子”就像是一個內(nèi)在的“異世界”,現(xiàn)實的“黑暗”與“破碎”,只能在這里得以消解,并使詩人再次獲得某種“鋒利的抽象與具象”,某種對現(xiàn)實描述和發(fā)言的鋒芒。就像他在《玻璃的內(nèi)心》中寫道的那樣:“玻璃的內(nèi)在/隱藏著鋒芒和喊叫。”
五
姚風的悲憫、道德感、擔當,以及某種歷史的反省意識,還集中地體現(xiàn)在《福爾馬林中的孩子》《植物人》《遺物》《默哀》《狗日的糧食》《南京》《景山》等作品中。而作為姚風標志式的幽默與反諷,則主要體現(xiàn)在《征服者》《詩人的午餐》《只有鮮花》《白夜》《狼來了》等作品中。在以往的研究中,姚風詩歌被視為一種“道德主義的,大丈夫的寫作”(朵漁),一種時代“可能的重”(東蕩子),以及一種“世界之詩、文明之詩”(沈浩波)。沈浩波的具體評價是這樣的:他是漢語詩歌中不多見的,在“文明”這一類主題上發(fā)力甚深,寫出過杰出的文明詩篇的詩人。他擅長寫世界之詩、文明之詩,對文明的親近與渴望,對反文明的質(zhì)疑和抗拒,是其詩歌中重要的主題。更重要的是,他以一個當代中國人的內(nèi)心去親近世界的文明,內(nèi)心常懷深刻的疼痛與悲傷。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姚風是當代漢語詩人中很少有的,能夠被稱為“文明之子”的那一種詩人。
沈浩波從漢語詩歌的角度去考察姚風存在的意義,這是很有意思的。在本文的開篇,我們其實已經(jīng)說到這個問題,姚風是一個“華語詩人”,他的影響并不應局限于國內(nèi),我們應該把他放置到一個更為廣闊的時空中去考察。他詩歌中的道義與擔當、幽默與凝重、悲憫與反諷、理性與感性,都是非常有價值的話題,他以個人之力,相當程度上推動著漢語詩歌參與世界文明的進程。他既關注著中國的問題,也關注著世界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最終都歸結(jié)到“人的生存處境之上”。在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被裹挾在“全球化、碎片化、后現(xiàn)代、大數(shù)據(jù)”的現(xiàn)實之中,個體的脆弱和時代的荒誕,成為一個必須要正視的問題,而對此,姚風是有清醒認識的,他說:“詩人作為個體面對現(xiàn)實甚至更為龐大的‘歷史’是不應該窒息喉嚨的。”又說,“時代呼喚著具有自覺意識的詩人,這樣的詩人應該對自己的內(nèi)心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只有吃得心苦,才能更真實地感受出人生和世界的復雜、荒謬、殘酷和苦難,其生命才會獲得重量和厚度,才不會僅僅在輕歌淺唱中把靈魂分解成一陣無謂的清風。”
說到底,姚風是有個追求的詩人,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甚至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魚化石》中,他寫道:“向著你淚水的海/多少人去了,帶著一把湯匙//我也去了/去做一條魚”,他的骨子里有詩人的浪漫、理想和追求。因此,他的詩歌中也不乏一種朝氣,一種朝著自我的使命奔跑的勇氣:“我們一起奔跑/在露水中奔跑,在果實中奔跑/我們跑得很快/在墜落之前,我們必須抵達”(《抵達》)。雖然有時候,在蒼白的現(xiàn)實面前,所有的努力顯得微不足道,但一種永不放棄,甚至自我獻祭的精神,正在他的血液里涌動,使他成為一個內(nèi)心柔軟的、具有鋒芒的,同時也是向著光的詩人:“經(jīng)過無數(shù)次的訓練/飛蛾/終于折斷了翅膀/它無法再飛/拖著夜色/像蝸牛/朝著光緩緩爬去。”(《朝著光》)
欄目責編:朱鐵軍
許澤平,青年評論家、詩人。廣東省作協(xié)會員,東莞市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理事,韓山師范學院詩歌創(chuàng)研中心理事。廣東省小學生詩歌節(jié)評委。出版詩集《在時光與落日之間》《獨腳站立的人》及評論專著《在時代的暗夜中穿行:80后詩歌考察》。曾獲“2013東莞年度文學傳媒大獎·詩歌獎”,入圍第五屆中國紅高粱詩歌獎、第二屆“詩探索·中國詩歌發(fā)現(xiàn)獎”等。
- 特區(qū)文學的其它文章
- 平行文化時空的聽風者
- 與廢墟對話(外一篇)
- 光與暗
- 心
- 如可贖
- 折疊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