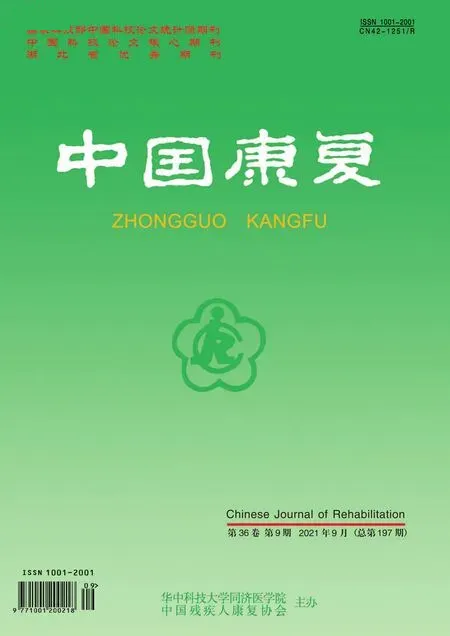圍手術期肺康復對肺癌術后患者不良情緒的影響
韓允,項潔,劉雯,胡小紅,徐偉文,王雨新
在全球范圍內,肺癌是對人類危害最大的惡性腫瘤之一。在中國,肺癌也是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惡性腫瘤[1]。有報道顯示,近年來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仍呈顯著上升趨勢,外科治療是其首選和主要的治療方式。目前圍手術期肺康復在加速康復外科中也被廣泛推崇。多項研究證明,對于肺癌患者,圍手術期肺康復利于肺部及支氣管炎癥的吸收和肺組織的修復;改善O2和CO2的排出;改善胸廓順應性等[2],從而改善患者肺功能,減少術后并發癥發生機率,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大家的廣泛認可[3-4],但精神疾病如抑郁、焦慮,作為癌癥的并發癥卻往往被忽視。研究顯示,高達40%的癌癥患者符合情緒障礙的標準,抑郁和焦慮分別影響20%和10%癌癥患者[5],其中重度抑郁、焦慮程度最高的是肺癌、婦科和血液系統腫瘤[6]。罕有文獻報道圍手術期肺康復對肺癌術后患者不良情緒的影響。本文通過對肺癌患者進行圍手術期肺康復,探討圍手術期肺康復對肺癌術后患者不良情緒、生活質量等的影響,為肺癌術后患者早期康復及盡早融入社會,提供方向和臨床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4月~2020年8月于徐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住院治療并進行胸腔鏡微創手術的肺癌患者73例。入選標準:通過病理結果確診為肺癌患者;年齡30~80歲;活動狀態Karnofsky評分≥60分;手術方式為胸腔鏡微創手術;認知功能正常,能夠配合康復訓練;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存在認知功能障礙或精神疾病不能配合康復訓練;存在肢體運動或認知功能障礙,不能配合及耐受訓練;存在嚴重軀體性疾病,不能耐受康復訓練的患者。本研究得到了徐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XYFY2020-KL009-01)。73例肺癌患者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38例和對照組35例,2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1.2 方法 觀察組:術前均接受圍手術期肺康復宣教,并同時于術前3d每天接受1次系統呼吸訓練,了解圍手術期肺康復的意義與重要性。從術后第1天起,在康復治療師指導下進行肺康復訓練,每次30~40min。出院后至術后2個月跟蹤指導病人進行康復訓練。圍手術期肺康復項目包括:①腹式呼吸和縮唇呼吸:根據患者病情,取坐式、臥式、站立等放松姿勢,盡可能減少肋間肌及輔助呼吸肌做功。以鼻深吸氣,緩緩膨出腹腔,吸入氣息量以感到腹部力量充實為宜,呼氣時將口型縮小似口哨狀呼出,吸與呼時間比為1∶2,每個呼吸時間包括屏息在內持續10~15s,連續進行20~30次(總時間約10~15min),每日2次[7]。②有效咳嗽訓練:根據患者病情,取坐式、臥式、站立等放松姿勢,患者盡可能深吸氣,吸氣后短暫閉氣,治療師在要咳嗽時給予手法幫助,向內、向上壓迫腹部,協助產生大的腹內壓力,進行強有力咳嗽,排除呼吸道阻塞物并保持肺部清潔,連續進行20~30次(總時間約10~15min),每日2次。進行該項訓練時,同時對放置胸腔引流管處進行保護[8]。③激勵式肺量計訓練:根據患者病情,取坐式、臥式、站立等放松姿勢,患者用肺量儀盡可能深吸氣,移開含嘴,仍采取縮唇方式緩慢呼氣,然后依次循環進行,連續進行15~20次(總時間約10~15min),每日2次。④有氧運動訓練:室內或者走廊內,選擇步行運動方式,術前每次約30min,術后從步行10min開始,逐漸增加至術前強度。若行走過程中出現明顯疲倦、氣促不適或或指尖血氧飽和度<85%,囑患者休息,待恢復后繼續進行,每日1次[9-10]。對照組:給予肺癌相關知識宣教,在心胸外科常規治療基礎上,未接受任何干預措施。
1.3 評定標準 ①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共20個條目,每個條目包含4個選項,標準分越高,癥狀越嚴重。一般來說,焦慮總分<50分者為正常;50~60分為輕度,61~70分是中度,>70分是重度焦慮[11]。②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共20個條目,將20個項目的各個得分相加,即得粗分。標準分等于粗分乘以1.25后的整數部分。SDS標準分的分界值為53分,其中53~62分為輕度抑郁,63~72分為中度抑郁,>73分為重度抑郁。 抑郁嚴重度=各條目累計分/8。結果:0.5以下者為無抑郁;0.5~0.59為輕微至輕度抑郁;0.6~0.69為中至重度;0.7以上為重度抑郁[12]。③SF-36生活質量評分量表(the Mos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包含生理機能、生理職能、軀體疼痛等8個領域。換算得分=(實際得分-該方面的可能最低得分)/該方面可能分數范圍×100%[13-14]。④住院費用及胸腔引流管放置時間:收集2組患者住院費用及胸腔引流管放置時間的數據。術后肺組織的缺失,很長一段時間明顯影響患者呼吸功能、情緒及生活質量。術后2個月,肺癌患者的心理-生理-社會結構逐漸趨于穩定狀態[15]。隨著時間延長,術后康復進入平臺期,且增大了其他因素對肺癌術后患者情緒和生活質量干擾的可能[16]。所以選擇術后2個月的時間對2組患者進行以上評定。

2 結果
2.1 2組患者干預前后SAS、SDS及SF-36評分比較 干預前,2組患者SAS、SDS及SF-36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干預后2個月,2組患者SAS和SDS評分較干預前均明顯降低(均P<0.01),且觀察組以上評分均明顯低于對照組(均P<0.01);2組患者SF-36評分較干預前均明顯提高(均P<0.01),且觀察組更高于對照組(P<0.01)。見表2~4。

表2 2組患者干預前后SAS評分比較 分,

表3 2組患者干預前后SDS評分比較 分,

表4 2組患者干預前后SF-36評分比較 分,
2.2 2組患者引流管放置時間及住院費用比較 觀察組住院費用(5.60±1.37)萬元明顯低于對照組(6.36±1.65)萬元,t=2.156,P=0.034。觀察組患者引流管放置時間[3.50(3.00,4.00)]d明顯低于對照組[5.00(4.00,7.00)]d,Z=-3.466,P=0.001。
3 討論
癌癥患者常常合并有慢性的、臨床上顯著的心理社會困擾綜合征,以抑郁情緒、焦慮和生活質量下降為核心特征[17-18],其中抑郁是癌癥患者早期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19]。有研究顯示,情緒壓力是癌癥的危險因素,可以促進腫瘤的生長與癌癥相關的侵襲基因的表達,另外免疫系統受到情緒壓力抑制,可能促進癌癥進展[20]。情緒壓力還可以引起多種應激激素的表達,如兒茶酚胺、糖皮質激素等,促進腫瘤細胞生長、遷移以及侵襲,同時誘導促血管生成細胞因子的產生來刺激和促進腫瘤細胞生長環境的發展[21]。另外惡性腫瘤患者的不良情緒可能影響其家屬、醫務人員及相關人群,即不良情緒傳染的第二,甚至第三、第四等環節,形成“踢貓效應”[22-23],導致個人生活質量下降,甚至也會對社會產生嚴重影響,包括肺癌病人在內的癌癥患者的心理健康應該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本項研究表明,接受圍手術期系統肺康復訓練的觀察組患者術后2個月SAS、SDS水平顯著低于對照組水平,術后2個月SF-36評分高于對照組水平,同時觀察組SAS、SDS得分降低量及SF-36得分增加量均明顯高于對照組。目前國內外很多研究者已達成共識:圍手術期肺康復可以改善肺功能,減少術后并發癥,縮短住院時間等[24]。圍手術期肺康復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疾病本身對患者生理上的影響,增強了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減少了不良情緒的產生,這可能是接受圍手術期肺康復干預措施的患者焦慮、抑郁減輕的主要原因;另外不良情緒對生活質量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接受圍手術期肺康復的患者生理機能改善,同時不良情緒緩解,兩者相互影響,形成良性循環,從生理機能、生理職能、一般健康狀況、心理健康等多個方面都提高了患者生活質量。同時該研究也表明圍手術期肺康復可縮短引流管放置時間,減少病人住院費用,促進病人恢復。
關于圍手術期肺康復,我們可根據病人情況,制定和調整個體化康復方案,安全性高,具有可行性,結合本項研究結果,圍手術期肺康復值得在臨床廣泛推廣應用。本研究存在不足:未排除陪侍家屬情緒因素的干擾,必須指出的是陪侍家屬情緒也是影響患者不良情緒及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25];另外樣本研究參與者多為早期肺癌患者,且手術方式不盡相同。若能進一步排除陪侍家屬情緒因素的影響、腫瘤分期擴展至中晚期肺癌,同時限定手術方式,該研究更具有嚴謹性,更利于臨床工作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