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維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王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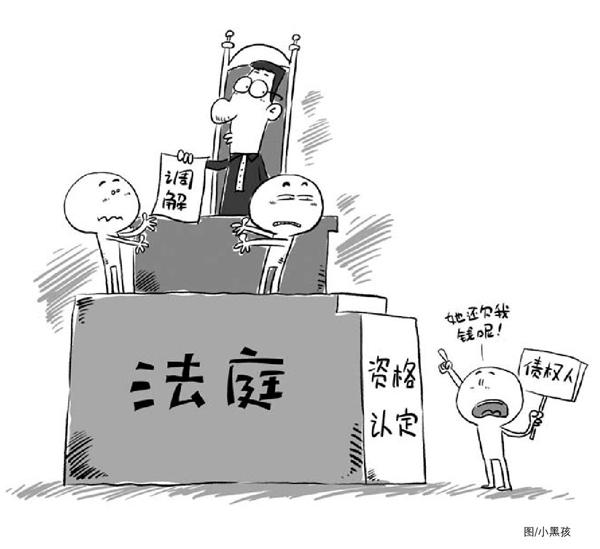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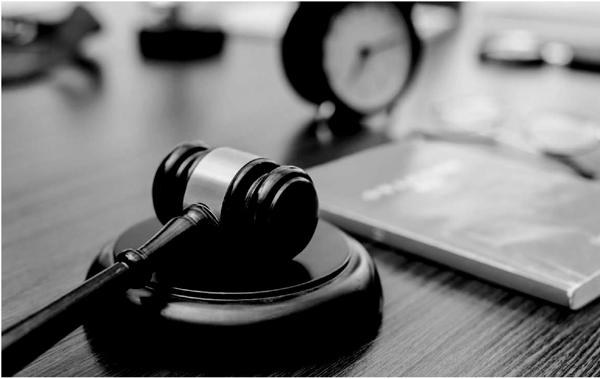
在我國當前進行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國應當逐步將既判力制度化,使第三人撤銷之訴發揮其應有的制度價值,切實維護現實經濟生活中案外人的合法權益。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法治建設的持續推進,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亦日益復雜,隨之而來的便是對社會關系予以規制的難度不斷攀升。如何調和經濟發展與法治建設之間的關系,是我國當前飛速發展背景下必須處理和面對的關鍵問題。在經濟生活中,人們基于本性趨利避害,而這也時常導致對他人合法權益的不當侵害。近年來,為了謀取經濟利益,不少人鋌而走險,采用惡意串通,甚至虛假訴訟的方式將原本用以維護民事主體合法權益的民事訴訟當作了謀取非法利益的手段。這樣的行為同時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和司法秩序,嚴重阻礙了我國社會的良性發展。為解決虛假訴訟問題,我國于2012年在《民事訴訟法》中新確立了第三人撤銷之訴制度,通過賦予案外人以提起訴訟的方式撤銷法院作出的確定判決的權利保障案外人的合法權益不受虛假訴訟的侵害。但是,第三人撤銷之訴的正確適用卻仍是我國需要不斷探索的重要命題。
我國第三人撤銷之訴自確立至今已有近10年之久,但圍繞其展開的討論卻從未停止過。在這些討論中,第三人撤銷之訴適格原告的問題是其中最具爭議、也是最為基本的一點。由于我國《民事訴訟法》明確將第三人撤銷之訴的適格原告限定為因不可歸責于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的第三人,而我國關于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以下簡稱“無獨三”)的規定本身又存在很大的不確定的空間,司法實踐中對于如何認定無獨三和第三人撤銷之訴的適格原告一直存在較大的困惑。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一批關于第三人撤銷之訴的指導案例。其中,152號指導案例(以下簡稱“本案”)就一般債權人能否依據其金錢債權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表達了觀點。但是,這一觀點究竟是否合理,尚需接受民事訴訟理論的檢驗。筆者認為,152號指導案例的裁判觀點(以下簡稱“觀點”)在理論上存在不能自洽之處,其為一般債權人鋪設的救濟路徑也不能給予一般債權人充分的救濟,甚至最終形成進退兩難的“司法困局”。
案例概述
本案歷時多年,所涉法律關系、法律主體較多。
本案所涉之當事人主要包括擔保中心、汪薇、魯金英三方。本案案情可簡單概括為:2010年4月,因先前的其他糾紛,擔保中心對汪薇享有金錢債權。2010年12月,汪薇與魯金英約定由汪薇向魯金英轉讓自己所有的養殖廠,轉讓價款為450萬元。2012年,擔保中心向法院起訴汪薇主張金錢債權并取得勝訴判決,隨后擔保中心據此對汪薇申請強制執行。2013年11月,因魯金英未依約支付養殖廠轉讓價款,汪薇基于買賣合同關系向法院起訴魯金英主張轉讓價款(以下簡稱“前訴”);此時,擔保中心對汪薇啟動的強制執行程序仍在進行中。隨后,汪薇取得前訴一審勝訴判決,該判決主文載明:(一)魯金英向汪薇返還養殖廠;(二)魯金英向汪薇支付違約金160余萬元。魯金英不服該一審判決,上訴至遼寧高院。二審過程中,汪薇與魯金英在遼寧高院主持下達成(2014)遼民二終字第00183號民事調解書(以下簡稱“前訴調解書”)。該調解書主文載明:(一)養殖廠歸魯金英所有;(二)魯金英再向汪薇支付150萬元轉讓款。后擔保中心得知該調解書,認為該調解書侵犯其合法權益,以汪薇、魯金英為被告向遼寧高院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請求撤銷該調解書。遼寧高院作出(2015)遼民撤字第00003號民事裁定書,認為擔保中心不具有第三人撤銷之訴的原告資格,裁定駁回擔保中心起訴。擔保中心不服,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終145號民事裁定書,指令遼寧高院對本案進行審理。遼寧高院經審理,作出(2016)遼民撤8號民事判決書,判決撤銷前訴調解書。魯金英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7)最高法民終626號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中觀點闡明了其認定擔保中心應為前訴無獨三,具備本案第三人撤銷之訴主體資格的理由,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一)擔保中心對汪薇享有債權,且在汪薇提起前訴時擔保中心已經基于該債權申請強制執行;(二)擔保中心認為汪薇與魯金英的行為符合其行使債權人撤銷權的條件,但由于前訴調解書的存在,擔保中心行使債權人撤銷權存在客觀障礙。
既判力主觀范圍
既判力指的是確定判決所具有的一種實質的確定力,即當事人不得再對確定判決就爭議事項所做之判斷再行爭議的效力。由于我國立法歷來排斥艱深的法律概念進入法律條文,既判力在我國至今尚未制度化。但既判力作為確定判決所具有的一種最基本的效力,卻早已成為我國民事訴訟中必須探討和面對的重要概念。
既判力的作用包括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兩個方面。既判力的消極作用具備十分豐富的內涵,即使是對于勝訴的一方當事人,既判力的消極作用也可能對其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如果僅僅是為了解決糾紛,那么就沒有必要對既判力的效力范圍進行限制,因為既判力的效力范圍越大,解決糾紛的效果就越明顯。而既判力的消極作用對為既判力所及者產生的這種不利影響之所以應當為所及者接受,正是因為所及者已經獲得了相應的程序保障。
我國實際上并不否認對既判力的效力范圍進行限制,現行司法解釋中關于“一事不再理”制度的規定就間接地體現了這一點。然而,在既判力尚未制度化的背景下,我國司法實踐亟需權威判例在如既判力主觀范圍這類爭議問題上統一認識。但是在本案中,觀點擴張前訴調解書的既判力主觀范圍,卻未對其正當性予以任何說明,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我國構建既判力具有相對性這一基本共識產生消極影響。
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識別
我國當前《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2款所規定的無獨三的概念,系自1991《民事訴訟法》沿用至今。多年以來,理論界對此概念的文字表述多有異議,認為其外延過于寬泛,不易于統一把握。本案中,觀點認定擔保中心具備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主體資格前的重要一步就是論述擔保中心與前訴處理結果具備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故擔保中心可以具備前訴無獨三的地位。
本案中,擔保中心作為一般債權人對汪薇僅享有金錢債權,而這種金錢債權與汪薇的其他訴訟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關聯性。具體而言,在本案情形下,擔保中心對汪薇的金錢債權與汪薇向其債務人魯金英主張債權的訴訟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性;而即使是在汪薇的其他訴訟確實可能使其責任財產受有不利益的情形下,這種不利益的結果與擔保中心債權能否實現之間的關聯性也不是必然的,而是還要取決于汪薇責任財產與擔保中心債權孰多孰少等其他因素,故擔保中心與該其他訴訟也僅能存在事實上的利害關系。同時,由于汪薇責任財產始終處于變化之中,法院在客觀上也不可能時刻查明汪薇責任財產的數量。
就一般債權人以無獨三身份介入債務人其他訴訟的正當性問題,筆者認為還可以通過將其與一般債權人依法以提起訴訟的方式行使債權人撤銷權進行對比說明。一般債權人行使債權人撤銷權,雖然也介入了債務人其他訴訟,但這種介入他人事務的方式是行使其權利,其正當性來源于債權人撤銷權行使的效力;而一般債權人僅以無獨三身份介入債務人其他訴訟,因一般債權人僅介入他人事務而未主張行使債權人撤銷權,故其正當性充其量僅來源于債權人撤銷權存在的效力。法律是一種平衡的藝術,既要維護一般債權人的債權,也要維護債務人其他訴訟不受一般債權人的肆意干涉。一般債權人僅依據其債權人撤銷權的存在主張介入債務人其他訴訟,而拒不行使其債權人撤銷權,本身就有濫用權利之嫌。一般債權人的這種行權方式因缺乏足夠的正當性而不為法律所允許。
第三人撤銷之訴的法律效果
本案最終的結果是擔保中心取得第三人撤銷之訴的勝訴判決,然而擔保中心的維權之路卻遠未結束,甚至擔保中心可能還要面臨竹籃打水一場空的結局。擔保中心的初心是希望行使債權人撤銷權,撤銷汪薇免除魯金英債務的不當法律行為。然而到了最后,似乎所有人都將注意力放在了擔保中心有無前訴無獨三地位這一問題上,而忘記了擔保中心的債權人撤銷權。至此,有必要探討第三人撤銷之訴的法律效果,闡明第三人撤銷之訴的能與不能。
第三人撤銷之訴屬于訴訟程序性形成之訴,是一種以變更訴訟法上的效果為目的的訴訟,與其同類的訴訟還有再審之訴、執行異議之訴等。
擔保中心原先是因為前訴調解書的既判力導致其債權人撤銷權失權,故而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歷時數年,第三人撤銷之訴終于塵埃落定,擔保中心取得了第三人撤銷之訴的勝訴判決并排除了前訴調解書的既判力。此時,導致擔保中心債權人撤銷權失權的既判力已經消滅了,但是擔保中心可能依然無法行使債權人撤銷權。依照《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釋之規定,債權人撤銷權適用長度為一年的,不可中止、中斷、延長的除斥期間。因而,在擔保中心撤銷前訴調解書后,其債權人撤銷權早已因除斥期間屆滿而徹底消滅。由此看來,擔保中心歷經千辛萬苦卻也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司法困局”如何破局
第三人撤銷之訴是廣泛適用于金融、破產、票據、房地產等領域的重要民事訴訟救濟制度,但其原告適格問題卻一直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巨大的爭議。152號指導案例的裁判觀點指出,在一般債權人已經就其債權申請強制執行的情況下,債務人與他人在另訴中達成調解書致使一般債權人無法行使債權人撤銷權的,一般債權人可以就調解書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這一裁判觀點違背了既判力相對性這一關于既判力主觀范圍的基本規則,更可能導致司法實踐中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認定泛化和第三人撤銷之訴的泛濫,同時也不能給予一般債權人充分的救濟。我國應盡快在司法領域確立既判力具有相對性這一基本共識,堅持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嚴格認定,明確第三人撤銷之訴的法律效果。
(作者系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律師)

